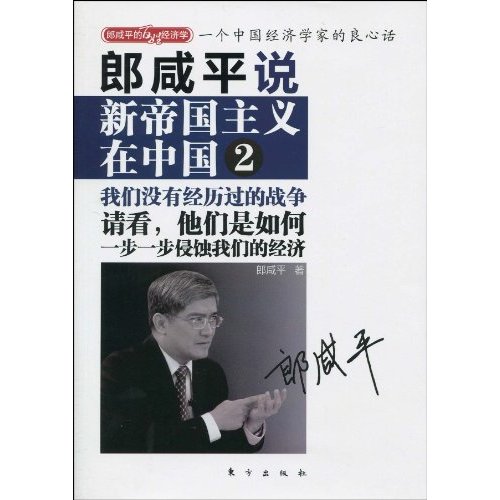悲观主义的花朵-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聪明,其实我也懒得见他们,可是不行。”
他拿出一副对待同龄人的态度把我送到门口,伸手帮我开门。
“下星期见。”
——要相信直觉,我的直觉告诉我,和陈天保持距离。
陈天有个坏名声,喜欢女人是许多艺术家的坏名声。这个坏名声证明他们是性情中人,证明他们情感炽烈,热爱美好的事物并且真挚忘我。我相信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对这个名声并不反感,像徐晨这样的作家还努力保持这个坏名声呢。(混际其中的下流胚除外,我从不谈论下流胚。)
不是道德禁忌,别跟一个喜欢拜伦的人提什么道德禁忌,对于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他们有自己的准则。我的问题是我已经说过我要远离风月情事,也就该远离那些情种,特别是那些还满不错的情种。
一个半月以后,我如期完成剧本,起名叫【小童的天空】,小童是那个爱上女老师的中学生。剧本交给陈天的时候,他很高兴,说很少有编剧提前完稿。除了这个,他没提什么意见,说等香港人看了再说。
写作是一件内耗的工作,让人身心疲惫,而放松身心的办法有人是喝酒作乐,而我是散步做爱。我每天散步,在散步不起作用的时候就做爱。我认为身体放松的时候大脑才能很好
地运转,当然,有个限制——做爱的时候只能用身体,不能用心,写剧本需要冷静。
那阵子,我和一个叫亚东的男孩有过一段交往。
亚东沉默寡言,有种处乱不惊的冷静,是我偏好的类型。这种人我一眼就能从人堆里拣出来。在一个酒吧不知为什么的莫名聚会里我们没说上两句话,但还是在离开前互相留了电话。两个星期以后我打电话给他,我们一起出去吃了饭,饭后去了一家台球厅,他手把手教了我两个小时的台球。
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不论长短,都会形成一种特定的方式,就像是计算机的默认值,一启动就是这个模式,大家都省事。我和亚东的默认值是——不谈论感情,不介入对方生活,由我打电话定约会,不一起过夜。
这种默认值使我在决定不和男人来往的时候,没有把亚东算在其中。
剧本快写完的时候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亚东约他见面,他犹豫了一下,问我什么时候。
傍晚时分,他如约来到我的小屋,迟到了四十分钟。他没解释,我也没问,我们像往常一样做爱。
天完全黑下来以后,我打开台灯,知道自己又可以安静地写上一阵子,心满意足地靠在床边看他穿衣服。
他背对我,忽然说:“刚才迟到了,下午我在做婚前检查。”
“你说什么?”我的脑袋已经不知道飞到哪去了,被他这句话拉了回来。
“我明天结婚。”
就算我一贯镇静如常,也还是愣了一下。
他转过身看着我,表情依然平淡,但我看得出他对他的话产生的效果很满意。
我知道我该说点什么:“你们看了那个他们说很恶心的成人毛片吗?下午?”
“没看,要不然还得晚。正好有一拨人看完出来,我们就假装已经看过了,盖了个章。”
“好运气。”我把衣服扣好,“那么,明天你是去登记?”
“上午登记,晚上请客。”
“那你有很多事要办吧,准备衣服,还得作头发?”我说着,发觉说的都是关于结婚最蠢的想法,只得作罢。“我不知道反正肯定得干点什么。”
他在床边坐下,吻我,深情的样子,久久不肯放开,让我惊讶。我想他是有意的,他要这样做,所以我其实用不着说什么,为耽误他而道歉就更可笑了。
“打电话给我,什么也不会改变。”临走的时候他说。
那天晚上,我只写了几行字就停了手,因为不对头。我一直在想亚东的事,想知道他到底出于何种理由要丢下他的新娘跑到我这儿来。为了给我留下一个深刻印象?不愿意拒绝我?他的婚姻是非他所愿的?我对他的私事一无所知,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不是出于爱,我们之间的一切与爱差着十万八千里呢。那么只有一个解释,他是为了向他自己证明他是不可改变的,为自己的生活制造一点戏剧性;要不他就是天性冷漠,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神圣,值得倾注心血的东西。那就可怕了,我喜欢冷静的人,但极端讨厌冷漠的人。
什么也不会改变,还是改变了,他不是我要的人,我要的是冷静面孔下燃烧的炽热灵魂。当然,是我太苛刻了,我并不了解他,他只是一个伙伴,应该说还是个不错的伙伴呢。算了吧,这个精挑细选的男友一样让我分神,与其关心他,还不如关心我的剧本呢。
我伸手想拨掉电话的时候电话响了,是爱眉,她有个好消息报告我,是关于我的金星的。
“你的金星与土星呈60度角 ,在星宫图里,这个分相最以表示艺术方面的卓越技巧,土星为金星唯美的审美观带来更坚毅固执的诠释,而你星座的主星就是土星,所以它们十分和谐,并无冲突”
“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剧本肯定没问题!”我马上把亚东忘到脑后去了。
星期三下午,我在陈天的办公室见到了刚下飞机的香港监制。他和陈天年纪相仿,保养得红光满面,一副商人派头,据说是香港最有钱的导演之一。
“剧本还不错,基本上可以说很好。”
看,我早知道,别忘了金星和土星的交角。
“只有一些小的地方需要修改,比如说小童的父母离婚这条线是不是太多了一点?小童的女同桌倒很有意思,可以多点笔墨,再浪漫一点,我这儿刚好有个很好的人选可以演。这些我们可以再细谈谈。”
好说,小菜一碟。
“这次真是多谢陈先生了!” 因为要考虑国语发音,香港人说话显得慢条丝理,“你们叫‘陈老师’?”
“人家写有我什么事儿。”
“多亏陈老师的指导。”我认真地表示。
“是。”香港人点头。
“拿我开心?”
对面的陈天居然红了脸,我可真有点喜欢他了。
晚上香港人在他下榻的昆仑饭店请客,陈天悠闲自得地靠在高背椅子里,还是那件皱皱巴巴,洗掉了色的外套,和周围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我不说话,只是吃,吃掉了一份北极贝,一份多春鱼,一份天妇罗,还要了一碗乌冬面。那年月,这东西贵得出奇,我基本上是照着吃大户的心理吃的。
陈天的特色是心情好的时候对人亲切无比,体贴入微,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冷嘲热讽爱搭不理。那天赶上陈天心情特别好,把那香港人糊弄得马上就想和他刹血为盟、结义金兰,直吃到晚上十点半一顿饭才算告终。
“我送你回去。”
饭后我跟着他走到停车场,没推辞就坐进了车里,他发动他那辆半旧的标致上了三环路。
“行了,搞妥了。”
“多谢。”
“谢我?”
我朝他笑笑,他也就没说什么,算是接受了。
“他们的意见不算什么意见。”
“对,两天就改好。”
“你刚才跟他说两个星期。”
“我当然要这么说,要不然他们会觉得钱花得不值。”
“一个比一个精。”他居然语带责备,“现在我可以说说我的意见了。”
他停顿了一下,很严肃,我等着他开口。
“太简单。比原来他们的那个故事当然强,但是还是简单,我说的不是情节,而是整个氛围,没有周围环境给他的压抑感,没有社会氛围,没有意在言外的伸展感,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它们的意味应该在有限中无限延伸。”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他说得对,所以我没吱声。
“你懂我的意思吗?”
“懂。”
他忽然侧头看了看我,怀疑地问道:“或者我们有代沟?你是故意这么写的?”
“不能说故意,但是我的确觉得这只是个简单的青春故事,肯定成不了《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所以不必我该怎么说?”
“还是代沟。”他断然地说。
我嘴角有了笑意,我们各有各的优势,他的优势是年长,我的优势是年轻。
“你看了《田园》吗?”他说的是他两年前曾经很招人议论的小说。
“没有。”
“嗯,那我就没法问你喜欢不喜欢了。”
“对。”
我可不急于恭维他。
“其实,我只看过你一部小说”
“别说了,肯定是那个最差的东西,广为人知。”
“对。很久以前看的,是你那个英国文学研究生借给我的。”
“噢。”
我抿着嘴忍着笑,他侧过头看看我。
“你以前不这样。”
“什么样?”
“伶牙俐齿。我记得那时候你不大爱说话,善于低头。”
“不是,我一直这样。”
他又看了我一眼,我认为那眼神不同寻常,但我懒的去想。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在他面前表演过少女脱衣秀,完全不知道。
车一直开到我们家楼下。
“就按你自己的主意改吧。”我下车的时候他说。
“不是按我的意思,是按香港人的意思。”
“说得对,我把这事忘了,算我没说。”
“哪里,受益非浅。”
“伶牙俐齿。”
“再见。”
“再见。”
我只有在两种情况下不大说话,善于低头,一种是心不在焉,一种是陷入了爱情。这两种情况还都没有发生。
过了一个星期陈天打电话来。
“喂,剧本改得怎么样了?”
“在改。”
“不是说两天就改好嘛?”
“看看能不能增加点社会氛围。”
“讽刺我?”
“没有,认真的。”
“明天晚上有个酒会,是我们公司的一个合作伙伴办的,你有空来吗?”
我沉吟了一下,公司的酒会,那么说是公事。
“来吧,可以拿一套新书看看,都是刚翻译过来的新书。”
“好。在哪?
“六点到公司来吧,我们一起去。
电话再响,是郭郭打来打听一个同学的电话,我想该问问她酒会的事。
“明天的酒会你去吗?
“酒会?
“陈天打电话说是你们公司的什么合作伙伴。
“啊,知道了,酒会没我的事儿,他叫你去你就去吧。那个女人,在追陈天呢!杜羽非。”
“什么?”
“那女的叫杜羽非,天天往公司跑,是个国外回来的什么女博士,要和公司合拍一个电视片,还要合出一套书,什么都想插一腿。”
“原来如此。”
“不过没戏,小沈的表姐说小沈在和陈天好着呢!”
“哦。”
“沈雪,你不认识?”
“噢,知道了。”沈雪是陈天的秘书,我见过几次,是个比我还小的女孩。
“小沈的表姐是个长舌妇,最爱传小话。”
郭郭提供的信息已经太多了,比我想知道的还多。
陈天的朋友,女的,杜羽非,矮个子,精力充沛,年轻的时候应该不难看,据说前夫是个著名的作曲。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