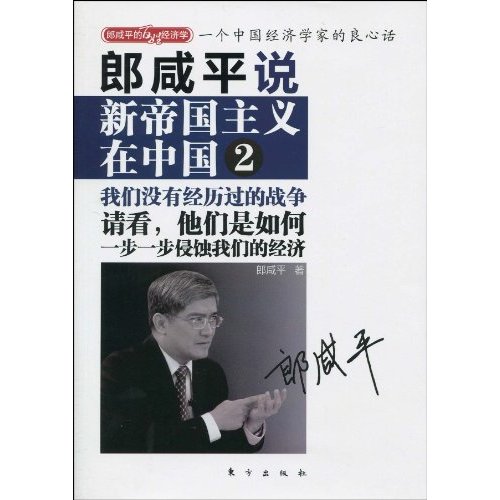悲观主义的花朵-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好。”
“同意了?那签个合同吧。”陈天起身招呼他的女秘书把合同送到了我眼前,“看看吧。”
我强装镇静地拿起合同,努力集中精力向下读,我没想到事情这么简单,管它呢,反正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没问题。”我努力使自己显得老练。
“那签字吧。”
他在边上看着我,我知道我的样子让他觉得有趣,有趣就有趣吧,他的优势明摆着,我不必计较。
我签了字,他也签了,合同交给了女秘书去盖章。
“好,这件事完了,还有一件事——这儿有个故事,你能在两个月之内写成剧本吗?”
我走出“天天向上”的时候,忽然有了另一个想法,对于“创造”我不敢说什么,但至少我可以追逐世俗的成功,这不会比“创造”更难吧。好吧,让我们来加入这争名逐利的人生洪流吧!谁打扰我我就把他一脚踢开,这才是魔羯座本色!
星期六我打电话请郭郭吃饭,郭郭说她下午要去看一个展览,问我要不要一起去,我说好啊,看完展览再吃饭。我们约了在官园见面一起坐车去。
郭郭是个巨能说的女孩,精力旺盛,对一切事充满兴趣,我们见面不到半个小时,我便对她这两年的生活以及感情经历了如指掌。她问我是否经常看美术展览?我就跟她说我从小就对美术深怀兴趣,小学画的水墨熊猫得奖就别提了,上中学的时候跟一个美院的学生学素
描,铅笔擦在粗糙白纸上的感觉让人愉快,一笔接一笔,连声音都十分悦耳。我不是个耐心的人,但画画的时候却心静如水,不厌其烦。那个美院的学生认为我画得不错,可也看不出什么不能埋没的才能,画了两年也就算了。后来唯一一次重拾这个乐趣,是和一个画画的男孩恋爱以后。我们曾经一起背了画箱去野外写生,我在他旁边支了个画框,有模有样地画着,引来不少过路的农民围观。从和那个男孩分手,我对美术的兴趣就只剩下看展览了。
我的谈话能力完全因对手而定,有了郭郭自然是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很是热闹,郭郭说到陈天,总的意思是觉得他不错,很有趣。
我们拿着请柬,边走边聊,颇费了些周折才找到位于东单附近的XX胡同23号,可那儿怎么看都是个大杂院,不知道展览在何处,门口也没有任何指示。我们在门口犹豫的时候,只见几个长头发大胡子的人朝这边走来,我知道对了,只要跟着他们就行,果然,他们熟门熟路地进了院子,三拐两拐地来到一个门前,不用说了,门口还站着好几个跟他们类似的人,原来是个私人画展。
进了门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房子倒是般般,但收拾得很有味道,花草门廊,错落有致,院子中间挂着七八个鸟笼,这些鸟笼可非同一般,上面长满了白色的胶皮奶嘴,密密麻麻,又是怪异又是好看。满院子的艺术青年和艺术中年就在这些奶嘴下面走来走去,交谈寒喧。如果你对现代艺术有点常识你肯定已经知道了,这些长奶嘴的鸟笼就是今天的展品之一。
在这种场合,没有比干站着更惨的了,展览十分钟就看完了,剩下的时间大家就拼命和别人交谈,显出和所有人都很熟的样子。郭郭肯定是没有问题,跟谁都能聊,这些人中间我也认识几个,于是也加入了奶嘴下晒太阳的行列,跟着大家点头寒喧,接受名片。
“阿波罗—赵。”我从名片上抬起头,看着眼前这个大脑袋的阿波罗,他除了脸盘子大,头发向外发射般地竖着这两点之外,看不出他和太阳神的关系。
“那边那位是我夫人。”他指着远处一个披着黑色披肩的女子。
“您夫人不会叫维纳斯吧。”
“你们认识?”
“还没这个荣幸。”
阿波罗赵又递给我一张名片,上面写着“维纳斯—孙”——居然不幸言中。
“你们一家把美、艺术、爱情全占了,我们怎么办啊?”我逗他。
阿波罗赵腼腆地笑了:“没什么,没什么。”
他这么坦然倒显得我小气了,爱眉这时进了院子。
“爱眉,爱眉!”我招呼她,把她介绍给郭郭,两人马上聊了起来。爱眉的父母都是画画的,都画国画。爱眉出于对家里堆得到处都是的笔墨纸砚的反抗,除国画之外的所有美术门类都感兴趣。
每次到这种场合我都会赞叹爱眉的社交才能,她跟谁都有的说,跟谁都说得来,而且全都轻松自如,我就僵硬多了,不是滔滔不绝,就是一言不发。
“当然了,我是双子座。”爱眉说。
“我明白你为什么不肯去乡下种菜了。”
“嗯,我需要活人。”
“活人,说得真恐怖,你不会吃他们吧。”
爱眉好脾气地笑:“反正不交谈我绝对受不了。”
郭郭是爱说话,爱眉是爱交谈,这两者之间有些差别。
我们都认识的一个画家周良神气地带着个外国女人向我们走了过来,他面色黝黑,脑后有辫,说话大舌头,但颇有活动能力。
“这是卡色琳,美国使馆文化处的。”
我们都向那个瘦小的黄毛女人点头。
“这是陶然,这是爱眉,她们是搞文学的,批评家。”
“我可不是。”我一点亏都不肯吃。
“今天有你的东西吗?”爱眉问。
“有啊,你们还没看呢?靠墙那七八副都是我的作品。”
我侧过头,墙边的确树着七八副大画,它们看起来全都一模一样,以致被我忽略了。
“你画的是什么?它们看起来像是——葫芦。”我指着画布上的一个个连环的圆圈问。
“你挺有艺术感觉的嘛。”
“不敢当。”
“——就是葫芦。”
“果然。你为什么画这么多葫芦?”我用手画着圆圈。
“这是我的新画风,葫芦代表中国哲学思想,体现了中国那种形而上的,飘的东西,是一种八卦,八卦风格。葫芦蕴涵了很深的哲学意义,它的弧形两个象征连在一起,这种连法代表的哲学,我们应该学习这种连法儿”
我很难告诉你周良到底说了什么,因为凭我的复述,这些话好像有了点逻辑关系,但是我敢保证,他说的时候绝对没有。
周良的阐述被一场行为艺术打断了。大家把一满脸粗糙、年龄不清的男人围在中间,他下身赤裸,软塌塌的生殖器上拴了一跟绳,绳子的另一端绑着一只小鸟,那可怜的小鸟肯定是受了惊吓,扑腾着翅膀上下左右飞窜,带着那裹着包皮的黑东西来回乱抖。
“题目是:‘我的小鸟一去无影踪’。”爱眉在念一份介绍,“小鸟不是在那儿呢吗?”
“没看见有人在边上拿了把剪子准备嘛?”郭郭提醒她。
“噢,看见了。你说他是要剪线,还是剪鸡巴?剪线就无聊了,剪那玩意还有点意思。”
“走吧,会让我对男人丧失兴趣的。”我拉爱眉。
我和郭郭爱眉出门以后,周良还在后面喊:“再呆会儿吧,一会儿艺术家们要出去吃饭。”
我们决定放弃和艺术家们一起吃饭的机会。
“你说,你倒说说,你认识的画画的人多,是不是我有偏见?他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利落——‘我们应该学习这种连法儿’!老天爷,这是什么话?!他有一次给我写过一张便签,说他晚上要去看话剧,知道是哪两个字吗?‘化剧’,‘化学’的‘化’,‘剧’字倒是写对了。有一些字是可以写错的,比如说‘兴高采烈’的‘采’,但是有一些字是不可能写错的,除非他是个白痴!你说他是不是个白痴?或者我有偏见,我有文化歧视。画画的人都这样吗?他们因为不会用语言和文字表达,所以才画画的?”
我在吃饭的桌子对面朝爱眉挥舞着筷子。
“是嘛?是嘛?他真的这么写的?”郭郭大叫。
“肯定不能这么说,画家中有学识善表达的人大有人在,多了,比如惠斯勒,你爱的王尔德还抄袭他呢。”
“我现在不像以前那么爱他了,他的俏皮话太多,真正谈得上观点的东西太少。不说他。”
“当然像周良这样的人也不在少数。有一种说法——最无学识,最没文化的人是最有天赋的艺术家”
“比如卢梭。”郭郭说。
“比如卢梭。”
“可是你说他是卢梭吗?他是真的有才能只是表达不出来,还是根本就是个白痴?”我说。
“这个有待时间的考验。”
“我看他多半是个白痴。”郭郭肯定地说。
“我小时候天天见的都是画画的人,后来我父母叫我学画,我死活不肯,因为很多人都像周良这样,我看不上,我喜欢用语言表达。不过后来我的确遇到过几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他们什么也说不清。”
“你认识许仙嘛?他就是这样的人!”
“好吧,那我们再看看吧。”我表示同意,但仍坚持说,“幸好我没学画画,每天和说蠢话的人在一起我会发疯的。”
“跟美术相比,你肯定更有语言才能。”
我打出租送爱眉回家的时候,她说。
“你敢说?”
“你自己不知道?”
“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步能算‘才能’。我的金星怎么样?”
“这得绘制星宫图,把你的九颗星星都放上去看它们的相位。”
“这么复杂?什么时候你有空,等你头不疼的时候,我想知道!”
“行。”
——有爱眉这样的朋友能解决多少人生的难题啊!
“要相信你的直觉,你有直觉能力。”爱眉下车的时候说。
如果我真有爱眉所说的直觉能力,我得说陈天给我的这个故事是个狗屎,一个中学生爱上了他的女老师,假模假式的性觉醒,矫揉造作,莫名其妙。还得避免过激的行为,避免实质性的接触,偷看女老师换衣服是肯定不行了,寄匿名情书还不知道能不能通过审查。
我把剧本大纲给陈天的时候,他沉吟着,我就把这些话跟他说了,当然没提“狗屎”。
“香港人,他们出钱拍这个电影。”他言简意赅,“编剧嘛,是个职业,你要不要写它?”
“要。”
我回答的这么干脆把他逗乐了:“我们当然可以弄自己喜欢的东西,女孩挽救作家呀什么的”他讽刺我,“不过你还年轻,锻炼锻炼,挣点钱也不是坏事。”
“多谢指点。”
“不过要用心写。”他挥了挥手里的大纲。
“我回去重写。把港式段落删掉,写一个青涩的初恋故事如何?”
“好,我看这个你在行。”
我忍住了不跟他斗嘴,很正经地说:“下星期给你。”
“跟我出去吃饭吗?我要去见两个人。”他抬头看看墙上的钟,轻描淡写地说。
我脑袋里的警铃颤动起来,一闪一闪地亮着红灯,我给了他两秒钟的犹豫,回答说:“不了,我回家。”
“聪明,其实我也懒得见他们,可是不行。”
他拿出一副对待同龄人的态度把我送到门口,伸手帮我开门。
“下星期见。”
——要相信直觉,我的直觉告诉我,和陈天保持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