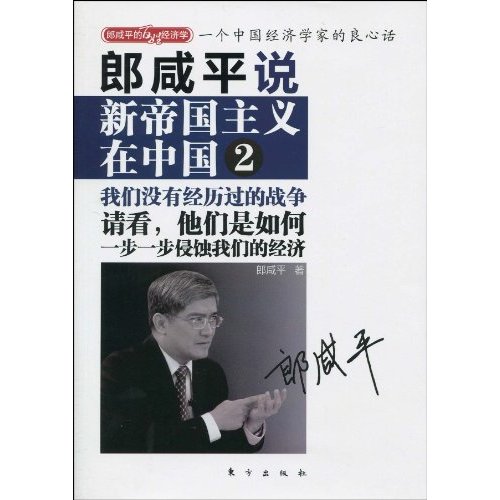悲观主义的花朵-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人向我打听他,这只能证明一件事——就是他不见了!我并不认为他的人身安全有什么问题,他只是从这个圈子里消失了。
他到底遇到了什么事,没有人知道。
爱眉认为大多数人都具有更多的感知世界的能力,只是它们被封闭了,没有开启。既然夏天炎热的空气使你烦躁,北欧的忧郁症患者远远高于热带,那么如此巨大复杂的行星运动不可能不对你产生影响。无论是占星,批八字,看相都是完全唯物的,你不相信,只能说明你目光短浅,如同一个视力好的人和一个视力差的人,看到的东西自然不同。
这就是爱眉,后面还会讲到她。
离开徐晨以后,我过过一段单纯的日子,因为疲倦,找了个温和优雅的男友,然后厌倦了,重新渴望与众不同的生活。
我把那段日子叫作“红舞鞋时期”,
“红舞鞋时期”的显著特点是没心没肺,肆意妄为,带来的显著特征是男友众多。
如果坎黛斯·布姝奈尔把这写入她的的专栏《Sex and the City》(中文翻译为《欲望城市》),她肯定会这么描述:“有一阵子这女孩选中三个男人,分一、三、五和他们上床,这样还剩下四天的时间无所事事。关于空闲的这四天时间她当时想出两种办法,一种是再找三个男友,或者一星期和他们每人上床两次,剩下的一天作为休息。这两种办法都不可行,前一种是因为她心不在焉常常叫错名字,记错约会。而后者,则需要他们对她有更大的吸引力。”
我在开头就说过了,人的欲望前后矛盾,瞬息万变,混乱不堪,牵着你的鼻子让你疲于奔命。对于人类来说,欲望和厌倦是两大支柱,交替出现支撑着我们的人生。一切选择都与这两样东西有关。但是吸血僵尸不是,他们只有欲望;从不厌倦,也就绝少背叛。他们是我喜欢的种类。
在那段日子里,我遇到过很多不错的人,当然也有很糟的。这都是我现在的想法,那时候他们的好坏我毫不在意,只要有一点吸引力就行,那可能是微笑时嘴角的皱纹,某种疲倦的神情,某个背身而去的孤单背影,什么都有可能。
李寿全有一首歌,那时候常常听的,歌名忘了,只记得第一句:“曾有一顿晚餐和一张床,在什么时间地点和哪个对象,我已经遗忘,我已经遗忘”
我就像那个穿上了红舞鞋的村姑,风一般地旋转而去,不为任何东西停下脚步,不为快乐,不为温暖,不为欣喜,也不为爱。
也许我错过了很多东西,谁知道呢。
很多年以后,在街头遇到一个“红舞鞋”男友,我们已经很久不见了,我对他的印象是不停地抽烟和一双修长漂亮的手,两三句寒喧之后,他突然说:“嫁给我吧。”说实话,我当时真想说:“好的。”就像在电影里一样,然后和他手拉手互相注视背身而去,在阳光的大道上越行越远,音乐起,推出“剧终”,好莱坞式的完美结局!它至少应该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一次!我当时一边这么想一边站在大街上傻笑来着。
但是红舞鞋终会变成一双难看的破鞋,为了摆脱它那可怜的女孩砍掉了自己的双脚!2002年初春,一个叫作Kneehigh Theatre的英国剧团来演过这出戏,屠夫拿了把锃亮的杀猪刀(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真刀,擦在地上正冒火星)对着女孩的脚比划来比划去,明知道他不会真砍,还是看得我心惊肉跳。
如果你不相信克制是通向幸福境界的门匙,放纵肯定更不是。
这是我的经验之谈。
再次见到陈天的时候,我刚刚跟所有的男友断绝了关系,把自己关在家里。
我整天不出门,不说话,只是关着门看书。我的一居室在父母隔壁,每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就来敲我的门,而我总是不吭声假装不在。
我戴着耳机反反复复听TEAR FOR FEARS的一首歌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不停地听:
“欢迎来到你的人生,
这是一条不归路。
大幕已经拉开,
你得扮演好你的角色”
我对一切都没有兴趣,悲观厌世。
当然,我一直是个悲观主义者,认为这个非我所愿而来,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个不折不扣的负担。只是凭着悲壮的热情和保持尊严的企图,我才背起了这个负担,同样出于尊严还要要求自己背得又稳又好。但那阵子我对这个工作失去了热情。
我试图寻找意义。
在这里我应该引用叔本华《悲观论集》的所有句子,但是还是算了吧。你一定已经读过,就算没读过,也可以找来读。
这种幽闭的生活过了两、三个月,唯一能够安慰我的便是看书,听歌和看碟——总之,看看别人是怎么想的。叔本华说的没错,对于人类来说最好的安慰剂就是知道你的痛苦并不特殊,有很多很多人,甚至许许多多杰出的人都像你一样忍受着同样的痛苦和不幸,忍受着这个充满虚无的人生。
就是在那时我认定艺术家的工作是有意义的,他们替不善表达的人说出了他们的感受,和善于表达的人取得了共鸣,而对于那些毫无知觉的人,应该恭喜他们,就让他们那样下去吧。
“欢迎来到你的人生,
这是一条不归路。
大幕已经拉开,
你得扮演好你的角色”
TEAR FOR FEARS悲怆的声音以无奈的调子这样唱着,到最后却仿佛自己也受了感动,歌声变得高亢起来,充满了金色的敬意和激情。
那年春天来到的时候,我对痛苦和沉思感到厌倦了,站在中午耀眼的阳光里眯起眼睛,我简直不能想像我会干出那样的事——深夜跑到结了冰的什刹海,整小时地躺在冰面上,试图让深夜的寒冰冷却我身体里燃烧的痛苦,那痛苦无影无形,却如影相随,不知道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后面去了哪儿。也许它是迷了路,偶然撞到了我身上,因为没有任何现实的原因,也就找不到任何解决的办法,这让它显得格外可怕。我敢说,我准是碰上了人们所说的“形而上的痛苦”。在这痛苦里我失去了所有的优雅作风,躺在冰面上大声喊叫,用了所有的力气大声喊叫,希望身体里的痛苦能够通过我的喊叫消散出去。
那天夜里四周寂静无声,没有任何人从黑暗中走出来打扰我或挽救我,任由我呻吟嗥叫——那时候的什刹海没有路灯,没有栅栏,也没有寒冬夜行人。
多年以后,当抑郁症席卷北京,身边的朋友纷纷倒下,饭桌上的谈话变成比较“罗拉”、“百忧解”和“圣约翰草”的药性时,我才想到那个冬天我可能得了忧郁症。那痛苦可能完全是形而下的而不是形而上的,但当时我们都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冬天结束,我把厚重的衣服收进柜子,花了很长时间在镜子前琢磨我的新衣。我那么专注于衣服颜色和样式的搭配,半天才发觉我竟然很有兴致!——也就是说它不见了!折磨了我一个冬天的痛苦不见了,我不知道它是走了,还是我已经对它习惯了。总之,我不再老想着它了!
好吧,既然我活着这件事已经不可改变,那么开始吧,大幕已经拉开,我得扮演好我的角色
没想到我的第一个观众是陈天。
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陈天坐在窗前的大桌子后面,从正看着的稿件上抬起头,笑了。
“长大了。”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一点都没变。”
“你可老了。”我向他微笑心里这么想。
我得先说我是去干什么的。
因为一个冬天的禁闭和思考,我基本得出了与浮士德博士相同的结论——人生唯一能带来充实感的事情就是创造,我既然要度过这个人生就得依赖这种充实感,这种“幸福的预感”,而我既无力“开拓疆土”,只会写作,只能写作,只有写作。于是我痛下决心,从此远离风月情事,远离情感纠缠,远离那些毫无意义的人间琐事,让写作凌驾于一切之上。
我当然知道创造除了需要决心之外,更需要的是“才能”,“才能”这件事说起来可跟你的努力,你的愿望都关系不大。想到此处我冷汗直冒,马上就想抄起电话打给爱眉,让她就我的金星相位谈谈我的艺术才能。可是如果她说我的相位不佳我可怎么办?我该怎么打发我的人生?
我的决心已经下了两个多月,每天对着自己的大堆手稿犹豫不决,不知道是该出去推销自己,还是该关在家里笔耕不止。写作对我是爱好,有人习惯手里夹一只烟,我喜欢手里拿一根笔,从小如此便成了自娱自乐。少年时代我曾断言徐晨是一个作家,对自己却缺少这种期望。我决定,从现在起再不把我的写作热情浪费在情书上了!如果这是我唯一会的东西,我也只好拿它闯荡世界了。
在我给杂志写专栏,给广告公司写策划,给影视公司写了几个有始无终的电影剧本的那段日子里,郭郭的电话找到了我。
“我们公司各种人都要!”她说,“下星期把你写的东西给我一些,我交给我们艺术总监看看。”
“好。”
郭郭是我大学的高班同学,在一家叫“天天向上”的文化公司里作策划,她的任务是为刚成立的公司找一群年轻写手,写什么的都要,因为“天天向上”的业务包括出书,办杂志,作剧本策划,制作电影、电视剧,也为作家作代理,你能想象出的事它都干,那两年,这种文化公司多如牛毛,所有有点声望的文化人都开了这么个公司。
“我们公司的艺术总监是陈天。”郭郭最后说。
星期一,我把一个电影剧本交给郭郭,那是我在出版社无所事事时写的。下一个星期一,郭郭打电话来,说他们的艺术总监明天约我去公司见面。
我如约前往。
《圆形棒糖》——我的剧本被陈天从一摞稿件中拽出来,拿着它坐到我旁边。
“真长大了,会写剧本了。”
他笑吟吟地看着我,我没吭声——以老卖老嘛!
“怎么想起写这么个故事?”
“没什么,瞎编的。”
“瞎编的?我还以为是自传呢。”
他不怀好意地笑着,我也笑了。
《圆形棒糖》是关于一个年轻女孩挽救一个酒鬼作家的故事,作家总是喝酒,而女孩总是叼着一根圆形的棒棒糖,在最后的日子里,年轻女孩因误杀一个纠缠她的坏男人被关进了监狱,而垂死的老作家还握着一根棒糖等待她的到来
“要拥有自己的语言是很难的事。”陈天收起脸上的笑容,正色道,“但是也很重要。”
他是说我缺乏自己的语言方式吗?他是这个意思。十足小说家的口气!剧本并不需要自己的语言方式,剧本寻求的是敏捷的表达,只有导演才看剧本,导演看的也不是你的语言方式,导演才需要自己的语言方式呢!
我像个乖女孩那样坐着,什么也没说。
“写得不错。”他最后总结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帮你代理,向别人推荐这个剧本,我们公司收20%代理费。怎么样?”
“好。”
“同意了?那签个合同吧。”陈天起身招呼他的女秘书把合同送到了我眼前,“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