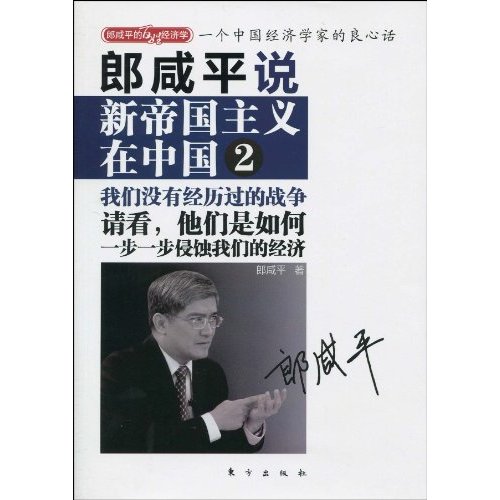悲观主义的花朵-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小童的天空】像其他的事一样被撂在半空,香港的制片方打电话给我,说已经拖延得太久,又找不到陈天,陈天的女秘书还跟他打官腔,让他找合拍部去。我还是只能听着。我不会为这事询问陈天,和他在一起的每一分钟对我都很宝贵,我不想说这种闲话。而且,这件事本来就是由他而起,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知道我已经完全违背了为自己制定的原则,这是必然的结果,我背离了第一个原则爱上陈天,以后就只能一发不可收拾。这有点像徐晨的理论——第一个誓言不遵守,以后也就都不必遵守了。我的人生已经毫无原则,唯一的剩下了一点逻辑也是陈天的逻辑。
杜羽非和陈天闹翻了。这个女人我在前面提到过,从陈天过去的闲谈里我知道她对他是多么好,他说过他们是好哥们,但她要求的一定不是好哥们。如老大经常说的:供求关系发生了问题。陈天对女人的那份好足以使人存有幻想,但是“好”既不是一贯的,也不是专一的,好就是好。陈天同意主编一套书是为了还杜羽非的人情,杜羽非不知怀疑他什么,半夜打电话问他:你老实跟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反正是已经不信任了,闹到这么不客气也足见他们过去多么亲密。女强人怎么肯受男人的怠慢和委屈?
那真是一个多事的冬天,对陈天最可怕的打击终于来了——他父亲去世了。
我有一阵子没有见到陈天了,他的声音完全哑了,因为牙疼整个脸都肿着。我非常想安慰他,但是我不行,我是他的另一个麻烦,我能作的只是躲开他,让他安静。
他不再每天打电话来,间隔的时间越来越长,但我还是每天在电话旁等待。
那个阴霾满天的冬日是陈天最委顿、沮丧的日子,他看起来判若两人,毫无生气,阴郁沉默,令人心酸,他说他听到纪念活动上大家对父亲的评价止不住地流眼泪,他说:我死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像父辈一样受到由衷的尊敬。他说他整夜在三环路上开车,他觉得他的创造力枯竭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时候狠不得冲着围栏撞过去
看见他的时候,他正在电脑前写作,我远远地坐下,没有说话。
他一直背对着我,不曾回头,那个背影让人满心凄凉,莫名难过,不知为什么忽然想起张楚的歌,那句歌词飞到我脑子里――“他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
他在那个冬天突然老了,他还要继续老下去,我不愿意他这么觉得!已经许久没有过这么深刻的怜惜之情,我无能为力,我的手不能扶平他的皱纹,不能给他安慰,也永远不可能责怪他。那个冬天我顾不上替自己难过,如果什么能让他快乐起来,我什么都愿意做。问题就是,我什么也做不了。
过了很久他才站起来,走到我面前,一声不出,忽然蹲了下去,抱住我的腿,头垂在我怀里
——我的心已经化成一滩水,那滩水酸酸的,要把我淹没了。
陈天不再去公司了,他的脑袋完全被别的事占据。对别人的不满他只说了这么一句话:“我好人也做过了,就做一次坏人也没关系。”
父亲的去世对陈天的影响非他人能够理解,他重新缩回他的小屋,思考他的创作。
“你的书是写给谁看的?”在那以前,我曾经很正经地问他。
“写给看书的人。”
“对,当然是看书的人,但是是什么人?”
“我不知道,也许是以后的人,还没出生的人。”
“这也算是一种答案,至少说明你对自己有信心。”
“其实我只是作我自己喜欢的事情罢了,我不是野心勃勃的小伙子了。你呢?你写给谁看?”
“电视剧嘛,自然写给老百姓看,他们看不看其实我无所谓。”
“你‘有所谓’的东西呢?”
“写给自己,写给跟自己同类的人,其他的人随便。”
“我知道你会这么想,很多年轻作家都这么想。”
“你呢?你怎么想?”
“我在美国的时候去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你知道那有多大?在那浩如烟海的图书中,你有必要再加上自己的一本吗?这一本有什么价值?有它独特的必要性吗?为了兴趣或者争名逐利写作我也理解,但这不是写作的终极目的。”
“会有什么终极目的吗?人生又有什么终极目的?”
“你搬出了虚无,一切问题就都不能谈论了。虚无可以颠覆一切,我们要谈论任何问题都必须预设一个对生命的肯定答案,否则就无法进行下去。”
“OK,假设我们的生存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偶然,不是被迫,不是自然随机的选择,美和善的原则的确是宇宙的原则之一。写作是为了什么?”
他笑了笑,以拍拍我的头代替了回答。
是的,要谈论任何问题都必须预设一个对生命的肯定答案,这样我们寻求意义的活动才能得到肯定和赞赏。但是我给不了自己这个肯定的答案,我想知道在一个否定的答案下,我该如何生存下去?我在其中找到的欣喜之事就是寻求美感。这一切都跟意义无关,所有的爱情,激动,感动,慰藉,欣喜,仓惶,痛苦,都不是意义,只是感官的盛宴。我想要的就是这样的盛宴。
我和徐晨也曾经为哪一种艺术更高超而争吵,也许我一直以平庸的态度爱着艺术,不过把它当成了逃避乏味人生的甘美草地。讲述和描绘可以使枯燥的生活显示出意义,我总是想拿起剪刀把那些岁月剪辑成一部精致的电影。如果有人兜售这样的人生,我想人们会倾其所有去购买。电视剧总是不能象电影一般精美,因为它象生活一样太过冗长,人们渴望日复一日的幸福,其实有了日复一日也就不再有幸福。
我和陈天对我们的工作谈论不多,后来就更少。我们俩的共同之处更多是在情感取向上,而不在艺术见解上。
陈天是个颇能自得其乐,享受生活的人。他对世俗生活有着一种我所不理解的浓厚兴趣。他非常贪玩,下棋,钓鱼,打麻将,玩电游,吃饭喝酒和女人调情,对名利一向不怎么上心。骨子里当然是骄傲的,许多事不屑一作,许多人不屑一理,对一些必须为成功付出的代价表示不以为然。他的这种世俗风格十分中国化,跟徐晨夜夜笙歌的颓废完全不同。
我和陈天相差二十岁,简直就是两个世界的人。四、五岁的时候,我妈开始教我背:“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青波。”到我可以自己选择书籍,我得说就没好好看过一本中国书。我所有的情感方式,价值判断,兴趣爱好都是西方式的,这“鹅鹅鹅”在我身体里到底占了多大部分,实在难说。
我的西方式的,极端的疯狂,撞在了陈天软棉棉的,不着力的善意里,完全销解了。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陈天不是我的吸血鬼,对我的奇谈怪论也不感兴趣。
我说过,陈天的文字像吹一支幽远绵长的笛子,不急不燥,娓娓道来,平实自然,体贴入微,细是细到了极处,像是什么也没说,却已经说了很多。
那笛子好是好,但终究是与我无关。
唉,我们到底是以何种名义相爱的?真是一头雾水。
在我最想念陈天的时候,有过各种念头。一定有某种办法,让他把他的梦境卖给我,那样我便拥有了他的夜晚,每夜等他熟睡之时,我们就可以相会。
我床头放着一本【哈扎尔辞典】,抓起来就能读,不管是哪一页。我对书中的阿捷赫公主着了迷,因为她擅长捕梦之术,能由一个人的梦进入另一个人的梦,在人们的梦中穿行,走了数千里的路,为了死在一个人的梦中。
我常常梦见陈天,醒来时便恍恍惚惚,或者是根本不肯醒来,打定主意用被子裹着头,闭着眼渴望睡去,再睡下去,让梦中的陈天继续说话,继续微笑,继续他的温存。
“你从不早起,就像这个姑娘。嫁到邻村后,她不得不早早起床,当她第一次看见田野里的晨霜时,她说:‘我们村里从来没这东西!’你的想法和她一样,你觉得世上不存在爱情,那是因为你起得不够早,无法遇上它,而它每天早晨都在,从不迟到。”
起床的时候已是傍晚,随手拿了包饼干吃,那本哈扎尔书在旁边,一翻便是这一段。
我一遍一遍地读它——你从不早起,就像这个姑娘,从不早起,因为你起得不够早,你无法遇上它。我们都起得不够早,就这样把爱情错过了,我们早早起来,却害怕外面的寒冷不愿出门,就这样把爱情错过了,我们在去田野的路上跌倒了不肯爬起,就这样把爱情错过了,我们早早起来来到田野,眼睛却已经瞎了,就这样把爱情错过了,就像这个姑娘!
令人绝望。
“刚刚写完,我先睡了。完了事你来吧,门我开着。”早晨八点,陈天打电话给我。
那天的整个上午我都戴着墨镜,一直戴着,谈事的时候也戴着。让世界在我眼里变得模糊一点吧,这个世界与我无关,唯一有关的是你,为了和你相会,我愿意一直睡着,睡着,在别人的办公室里睡,打电话的时候睡着,下楼的时候睡着,在出租车里睡着,付钱的时候睡着,直到见到你才醒来,你才是我真实的生活,其他都不是。
但是你,只有在你睡着的时候才能属于我。
我三言两语打发了一个制片人,打了车往他那儿赶,上午十点,这是我应该熟睡的时间。
我上到三楼,如他所说,房门没锁,一推就开了。房间里很暗,窗帘低垂——人造的夜晚。书房的门敞开着,很重的烟味,电脑屏幕保护的那缸热带鱼在黑暗中无声地游动。
他在床上,在熟睡,被子蒙住了头看不见脸。
我站在卧室门口,开始脱衣服,一件,一件,脱得一件不剩。
走到床前的时候,我突然感到恐惧,也许我进错了房间?也许上错了楼层?也许这个熟睡的人不是陈天?也许我马上就得夺门而逃!
而我一丝不挂地站在这儿!
房间里的钟嘀嗒作响,我不知所措地站着,觉得冷。
终于,被子里的人翻了个身,脸从被角露出来。
陈天甚至没睁眼睛,也没有人说话。我怀疑他会这样抱住随便哪个溜进他房间的女人,爱抚她们,和她们做爱。这个人造的夜晚蜜一般稠腻,它摹仿得如此之像,甚至让真正的夜晚无地自容。他开始在我耳畔轻声述说,含糊不清,如同梦呓,要想听清就得从这白日梦中醒来,但我醒不过来,就让他说吧,声音便是意义,他的话语不过是交欢时的颂歌,不必听清,也不必记住,让他说下去,说下去,作为超越尘寰永不醒来的咒语。
两个多小时以后,他又睡着了。我像进来时一样,悄无声息地溜下床,穿好衣服,溜出门去。但是,我把他的房门牢牢地锁好了,我可不希望另一个女人也这样溜进去
像我希望的那样,陈天把他的梦卖给我了。等他醒来,他会以为他只是作了个春梦。而我,像阿捷赫公主一样,能够把梦中的东西带进现实——他的亲吻还留在我的身体上,鲜红如血。
我几乎快乐地微笑了。
走到大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