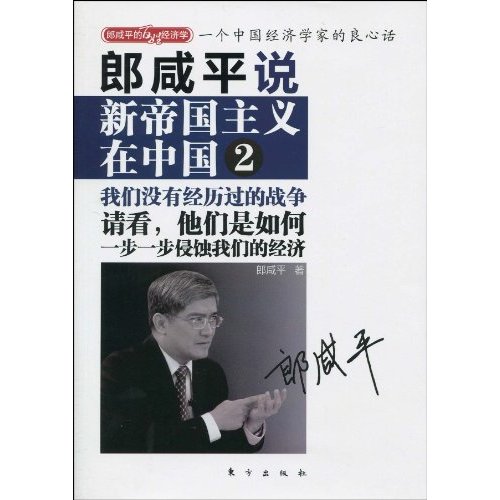悲观主义的花朵-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别愁眉苦脸的,这没什么。你不会以为我跟你上了床就非得嫁给你吧?”
他看了我一眼,显然并不觉得我的话可笑。
“也许有一天,我会强迫你嫁给我。”他这么说。
我没说话,——‘也许’,‘有一天’,‘强迫’,句子造得不错,也很感人,不错的情话,不过我们都不会把它当真是不是?我没想过要嫁给他,对应付任何世俗的烦扰也没有准备,我只是想跟他呆在一起,呆在一起,给我时间让和他呆在一起!
我看着窗外的车流,街道拥挤,芸芸众生都在赶着回到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安乐窝,如此忙乱而嘈杂,有几辆自行车几乎要倒在标致车的玻璃窗上,和我贴得如此之近!这车是我们的堡垒,遗世而独立的堡垒,只有在这儿我们是安全的,只有在这儿我们是不受干扰的,只有在这儿我们彼此相属。
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告诉他我爱他,这会让他轻松一点。
我看了看他,缺少了调皮的神情,他脸上的线条松懈下来,是个随处可见的中年男子。
确定陈天肯定没有时间见我的日子,我会约爱眉出去喝茶。这种时候不多,多数情况我会在家里随时等待他的召唤。
“我来一杯姜茶。”我对酒吧的男孩说。
“晚上不要吃姜,早晨吃姜如同人参,晚上就有害了。有这种说法。”
在这些问题上,我当然总是听爱眉的,她要了治失眠的紫罗兰,而我要了治焦虑的熏衣草。
爱眉显得心神不定,来回来去搅着那蓝色的紫罗兰茶,或者是我的错觉,是我在心神不宁?
“有什么事嘛?”我问她。
“我在想要不要结婚。”
“嗯。”如果我表现出了吃惊,那么就是说我并不是真的吃惊。但是这次我平淡地哼了一声。
“你有一次说过你今年有婚运。”
“对,所以如果我非不结婚,过了今年就不会结婚了。”
“永远?”
“十年之内。”
“那么?”
“其实结婚证明已经开了,但我在犹豫。”
“和谁?”我再沉得住气也不禁要问了,地下工作搞得也太好了,跟我相差无几了,哪象双子座啊。
“一个画画的,你不认识。年纪比我大。其实,是个很有名的画家,我说了你就会知道,但我不想说。”
“反正等你结了婚,你就非说不可了。”
“问题就是我可能不结了。”
“你决定了?”
“基本上。”停了一会儿,她补充说,“婚姻对我不合适。”
“得了吧,我看你就需要往家里弄进个丈夫,他会分散你很多注意力,强迫你注意很多具体的事情,你就不会想那么多事了。”
“我相处不好。我连跟父母都处不好,想想吧!”
“怎么可能?你对人哪有一点攻击性啊?”
“没有攻击性,可是要求很高,所有的不满最后只会作用到我自己头上,我只会跟自己叫劲儿,他们一点都看不出来。”
“你脾气多好啊,总比我柔和吧。”
“我们俩的星空图刚好相反,你是那种看起来很强的人”
“我?看起来很强?”——如此的小身板和温顺的脸?
“我说的是精神气质,只要不是太迟钝都能感觉到。”
“是,我是很强。”我认了。
“但这还是一个错觉。你的太阳在魔羯,但月亮在双鱼,海王星还在第一宫。双鱼是十二星座的最后一个,也是最弱,最消极的一个。”
“什么意思?”
“小事聪明,大事糊涂。”
“有这事儿?”
我不太想承认,爱眉以不庸质疑的表情挥了挥手,在这方面她极其主观,极端自信。
“我刚好相反,我对外界的具体事物完全没有控制能力,但是心意坚定。在关键问题上你能屈从于情感,或者别人的意志,我永远不行,我比你难缠多了!”
“大事清楚,小事糊涂?”
“不是糊涂,是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么咱俩谁更倒霉?”
“我。”
“都觉得自己最倒霉。”
“当然不是,想想,只要你知道了该做什么,你总有办法做到。但我永远都知道该做什么,但永远都做不到,你说谁倒楣?”
“你。”
“就是!不结婚并不是替对方考虑,是为我自己考虑。”
“你没有不安吗?有时候,希望有人在你旁边?”
“两个人的时候我更加不安。”
我的问题不是爱眉的问题。
“他是个双鱼座,双子座最受不了双鱼座的自以为是,目光短浅,还有不顾事实的狡辩。”
“说得好!不顾事实的狡辩!”我想起徐晨,拍案叫绝。
“所以,我肯定不行的。”爱眉下了结论。
“你再想想。想想他的好处。”
“好处,并不能改变本质的差异。”
爱眉终于没有结婚,凭着我对绘画界的粗浅知识,她不说,我也无法猜到那个双鱼画家是谁。
“这算是对抗命运吗?”过后我问她。
“命运只是给了你这个机会,要不要它,就是你自己的事了。”
我和陈天坐在二环路边的一处酒吧里,我们总是选择一些格调比较差,文化人不怎么爱去的地方见面,这种酒吧通常只有速溶咖啡,柠檬茶里的柠檬是皱皱巴巴的一小片,热巧克力的味道也很古怪,但是没办法。
我一本正经地拿着张传真,在给他讲香港人关于《小童的天空》拍摄前的最后修改意见。他靠在对面的扶手椅里,悠闲地把腿翘得老高。
“真怪,你看起来总是很安静,是因为你喜欢穿的这些衣服吗?”他忽然说。
我瞥了他一眼,继续念传真。
“知道嘛,你有好多小孩子的神态,看起来很小,也就十六岁,顶多十七。”他继续在对面打量我。
“你是作为监制这么说的,还是作为男友?”
“作为男友。”他笑。
“还要不要听?”
“你总是这么小,老了怎么办?又老又小,样子太吓人了。”
“放心吧,到那时候不让你看到就是。”
“肯定看不到,等你老了,我已经死了。”
“喂!”
“好吧,你接着说。”
他总是叫我“孩子”,从第一次见到我就叫我“孩子”,他说他对我有种偏爱,偏爱什么?他偏爱那些有着少女面庞的姑娘,清秀,安静,灵巧,永远不会成熟,不会长大,不会浓装艳抹,不会为人妻,为人母的少女。我没有什么特殊,我只是众多的,他喜欢过的有着少女面庞的女人中的一个。这个我早就知道。
我拿不准他会怎么想,喜欢还是不喜欢?在我们第一次做爱的时候,他不能置信地抚开我脸上的头发看着我--“还是你吗?”
后来,陈天有点不好意思地向我承认,他之所有不肯和我上床,还有一个不便言说的顾虑。
“我已经老了,我怕我不能满足你,你会不再喜欢我。”
他肯承认这个让我惊讶,这说明他不是那种认为男性权威不容侵犯的男人,足以使人理解他为什么吸引女人的爱情。他不是一个做爱机器,崭新的,马力强劲的做爱机器,一个人能不能满足你,要看他引起了你多么大的欲望,陈天从未满足过我,无论是肉体还是精神。
深刻的感情从来与满足无关,满足只能贬低情感,使情感堕入舒适,惬意和自我庆幸的泥潭。爱一个不爱你的人,一个登徒子,一个同性恋,那些无力满足你的人,这样你可以更加清晰地感受爱情的重创,没有虚荣心的愉悦,安全感的满足,甚至没有身体的舒适,只有爱情,令人身心疼痛的爱情。
――窒息你的自尊,抛弃通用的爱情准则,忘掉幸福的标准模式,剥掉这一层层使感官迟钝的世俗的老茧,赤裸裸的,脆弱柔软的,只剩下爱情了,要多疼有多疼,美丽得不可方物,改变天空的颜色,物体的形状,让每一次呼吸都带有质感,生命从此变得不同
陈天一定以为我是个热爱床笫之欢的女人,就象我这张安静的少女面庞造成的错觉一样,这是另一个错觉。那些冲动,颤抖,尖叫,撕咬,都不过是表征,我渴望、追逐的是另一种东西,它有个名字叫做“激情”。它是一切情感中最无影无形,难以把持,无从寻觅的,肉体的欲望与它相比平庸无聊。我无法描述我在他怀抱中感受到的激情,那哪怕最轻微的触摸带来的战栗,让我哭泣,我感动到哭泣。它来了,又走了。是同样的手臂,同样的身体,同样的嘴唇,激情藏在哪一处隐秘的角落,又被什么样的声音、抚摸、听觉或触觉所开启?永远无从知晓。
我想我最终也没能使他明白这个。
沉默不语。
我和陈天在奥林匹克饭店大堂的咖啡厅面对面坐了两个小时,最后是我要求离开的,因为这么沉默不语地对着他,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表现得像个傻瓜,却对自己毫无办法,我一声不出地坐在他面前,浑身因为充满着渴望而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这张弓除了微笑一无用处。我体会到了那种羞怯少女痛恨自己的感觉,我有无数的话要对他说,却不能开口,我
找不到恰当的方式和恰当的语言能表达对他的感受。越是这样我就越是难受,越是难受就越说不出,他送我回家的时候,我搂住他几乎要哭了,再有这样的一分钟,我的眼泪就真要落下来了。我这是怎么了?!
晚上和林木,狗子,老大,老大的女友花春,徐晨,徐晨的新女友(他老换,记不住名字),阿赵和阿赵的老婆一起吃饭,然后去了紫云轩喝茶,然后狗子说喝茶没意思,越喝越清醒,大家就移位去了旁边的酒吧。
林木在艺术研究院当差,每天跟这班闲人耗到半夜,第二天一早还去上班。他像那种老式的江南文人,热衷诗词歌赋、醇酒妇人。诗是真看,酒是真喝,妇人只是用来谈。我们都
给他介绍过姑娘,徐晨带给他的就更多,只看见他跟姑娘谈心,以后就再没别的下文。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我就不信哥们找不来!”
徐晨很是不服,当时凌晨一点,我们正在东四的永和豆浆吃鸡蛋饼。
“别回头,别回头,千万别回头!”老林的眼睛忽然直了,“就在你们身后,过一会儿再看,有两个姑娘!”
“你的梦中情人?”我闻到一阵香风,直着脖子问。
“差不多,差不多。”
“左边的还是右边的?”徐晨想回头。
“别回头!一会儿再回头,别让她们发现!”
“发现又怎么了?姑娘巴不得被人看呢!”
“是嘛?那好吧。”
等我和徐晨回头一看,几乎背过气去。——那是两个刚下夜班,或者没找着活儿准备回家的三陪!长得那个俗,穿得那个傻,脸像没洗干净似的,风尘扑面。
我和徐晨互望一眼,看看林木,这个白净书生有点紧张,不像是拿我们开心,我们恍然大悟。
“我说你怎么老找不着中意的!他身边都是女学生,白领,知识妇女,哪有这种人啊?咱们也不认识啊!”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