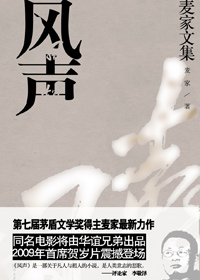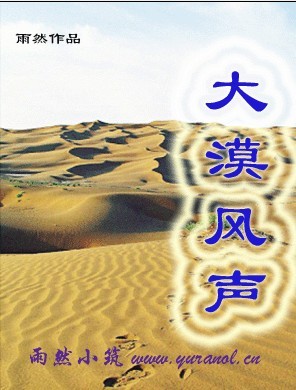风声鹤唳-第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噢,那不算什么。”
“你的东西呢?”
“我一分钟就可以弄好。”
“好吧!如果你坚持,就这么办。等到傍晚,我会带你去老彭家。事实上,我很希望你认识他。”
受了好奇心的驱使,那天下午博雅就过来坚持要梅玲告诉他过去的生涯。
“我从哪里说起呢?”
“从童年起,把一切都告诉我。”
“我们在路上有很多时间嘛。”
“但是现在告诉我吧,我会觉得和你亲近些。”
于是梅玲和他单独在一起,开始述说她的身世。她母亲是邻近上海产丝区湖州人。她离开丈夫后,就带着四岁的梅玲去上海。她在闸北区一所学校教书,每月薪水五十元。母亲带她上学,后来她转到一间男生中学去教书,只好把女儿留在家里。因此梅玲很小就学会了理家,让母亲安心上课,等她中午回家,午餐就弄好了。母亲对女儿期望很高,就在晚上教她。
梅玲是一个倔强的孩子,原先她跟母亲上学,和其他小孩子一起读书,大家都叫她“老师的孩子”。她常和同学热烈争吵,护卫母亲的湖州口音。当时各地已规定老师要用国语上课,但是梅玲的母亲和大多数的南方人一样,总是改不了家乡的口音,她老是漏掉“ㄣ”的尾音,所以“盘”字之类的声音总是念不准。她老说“牌”,而自以为说了“盘”字。梅玲知道母亲念错了,因为她自己念“盘”字就一点困难都没有,但是她总是坚持说她母亲念的是“盘”字,她发出一种介于“牌”和“盘”之间的声音,“ㄣ”音若隐若现,然后始终维护她的母亲。但是在家里她却告诉母亲念错了,想教她发出正确的“盘”音。母亲慈爱地说:“孩子,我的舌头又僵又笨。我知道那个读音,但是我读不出来,我一辈子都是这么说的。但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得教书维生哪。”第二天母亲听到梅玲故意在班上念出含有“ㄣ”音的“牌”字,以维护母亲,她很感动。
《风声鹤唳》伍(3)
当梅玲逐渐长大,不再上学,晚上就在她们唯一的客、餐、卧兼用的房间里书桌上,不仅埋头做功课,有时还翻阅母亲批改的学生笔记和作文。她观看上面批改的部分,藉以从母亲那儿学到超过学校学生的东西。她也自己查字典,寻找可疑音符的同音字。她看见母亲改到好文章时,脸上不觉一亮,两个人便一起欣赏其中的佳构。梅玲不久就有了丰富的文学知识,有一天她看到作文堆积在桌上,趁母亲不在时用毛笔批改了一部分,打上分数,还在末尾学母亲的字迹,加上批评的字眼。母亲回家,意外地发现作文批好了,因女儿的大胆而震怒。后来她检阅评语,不觉点头微笑。梅玲写得还不坏,只是不十分成熟而已。
“这个评语还不坏,你怎么做的?”
“噢,妈,”女儿回答,“很简单嘛。你常用的评语不会超过二十个字,只是常加以变化——譬如‘文笔流畅’啰,‘漫无条理’啰,‘虎头蛇尾’啰——我通通都知道。”
有一次母亲很累,特准梅玲替她改作文,但警告她不要删太多。梅玲对这任务非常自豪,非常尽力地做。母亲躺在床上看她工作。她看出梅玲很有兴趣,兴致勃勃为好句子画线或勾圈,有一次还在两篇杰出作品上打上三角记号。母亲览阅她批阅的成果,在需要的地方略微修改一番,学生都不知作文是一个和他们同年龄的女孩批改的,有些人注意到字体的不自然,母亲解释说她人不舒服,是在床上改的。
白天梅玲待在家,负责洗衣、煮饭、清洁工作。她们的房间在一条巷子里,是著名的“陋巷”,巷里挤满红砖房,谁都可看见十尺外对面房子的动静。她们的窗子正好面对一家棺材店。两端翘起,大框架的棺材在小孩子眼中是很丑的东西,不过就连这种东西看熟了也会产生轻蔑感。
不过她仍不能忍受看到小孩子的棺材,或者看见贫贱的妇人为孩子买棺材。“你知道,”她对博雅说,“连死都有贫富之分。丧亲的穷人比较哀痛得深。有时我看见有钱的弟兄穿着丝绸,来为母亲或父亲买贵重的棺材,和店东讨价还价,仿佛买家具似的。”
在这种环境中长大,梅玲自然惯于独来独往,上市场或店铺买东西,如此很早就学会管理她的钱财。闸北区的太太小姐们大都是来自小店主或小工厂工人的家庭,不像富家千金故作娴静。她们刷洗、聊天、敞开胸脯喂孩子、大声吵架,夏天夜晚就坐在竹凳上乘凉——一切都展现在街上行人的眼中,没有一个人比别人更有钱,人们很自然民主。工厂做工的太太小姐们自己每天有两三角的收入,可以不向人伸手,自己花钱打扮或散心。就在这样拥挤、吵闹、自由而民主的中下层社会中度过了少年时代,也因此培养了贫家女子的独立精神。巷子里的噪音很可怕,女人、孩子一吵闹,所有的人都听得到,巷子里一天也不沉闷。对一个过惯这般闹街生活的人而言,完全看不见邻居的僻静住所,似乎单调得难以忍受。
周末母亲没课时,梅玲常到国际住宅区的中心看表演,或者到北京路去看电影。在“大世界”,只要花两毛钱的入场费,就能消磨一天,看古装或时装的中国剧、杂耍、听人说书或者看一场民俗表演,常常一起去看。这是单口朗诵的节目,配着小鼓的韵律,运用高度优美而动人的语言,以固定的调子说出来,动人的段落则像一首歌曲。在专家手中,这种单口艺术可以用不同的节拍、腔调、手势和表情从头到尾把握住观众,既使故事已听过了一百回。这些简短旅途代表她们的假日,她们常常在小饭馆喝半斤水酒才回家,十分满意同时也很精疲力尽。
梅玲如果喜欢一样东西,就会全心全意。“我简直为大鼓疯狂了,尤其是刘宝全。”她承认说,“最后几年,我母亲健康不好,她不能再看表演,我就一个人去,我母亲不大赞成。但刘宝全表演,我硬是非去不可。”她说,听刘宝全这位最好的鼓手说书,完美的字句和音调似乎抚慰了她的感官,激励起她的情绪。她喜欢伯牙和钟子期故事中描写河上月光的段落,优美的音节仿佛由字音和字意描绘出河上静月的美景。
梅玲现在忆起伯牙——和她面前的男士姓名相像——的故事,两个人热烈的友情,伯牙的琴音只有子期能欣赏,所以子期死后,伯牙就不肯再弹琴了。
“钟子期若是女子,那就好了。”博雅说。
“那就变成文君的故事啦,这就是文君的故事长,子期的故事短的原因。”
“我可以背出整本故事。”梅玲说。
“背一点吧,让我听听。”
一阵迟疑,梅玲终于屈服了,开始敲桌当鼓。她的声音又低又柔,当她念到河上月光的那段,自己也完全沉醉在其中。她的小嘴微斜,很像月光下的波纹。博雅被吸引住了。突然她稚笑一声地打住。
在这一段打岔之后,她又继续述说整个故事。
母亲在世的时候,她过得很快乐。她母亲因为工作过度、营养不良,健康一天天衰退,但是学校工作还得做,作文也得改。梅玲天生乐观,总是展望事情光明面。她母亲花了三十元的巨款,几乎是一个月的薪水配了一副眼镜,但是似乎也不能减除头痛的毛病,而头痛又带来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等现象,梅玲常说母亲需要的只是休养一年,补充营养,症状就会消失的。她母亲只有四十岁,再过几年也许她嫁人,可以养活母亲,让她辛苦谋生多年之后好好休息一番。但是母亲的病情不断恶化,她没法休息,巷子里的噪音使她心烦。这时候梅玲才开始知道什么叫贫穷,也晓得金钱和幸福息息相关。
《风声鹤唳》伍(4)
结局来得太突然了,她母亲患了三天的流行性感冒,没有就医,便过世了。当母亲开始发高烧、胸口发疼,梅玲吓慌了。她叫来一个中国西医,但是治疗没有效。母亲猝死的震撼对梅玲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突然体会到自己孤零零一人,又没有谋生的方法。她甚至没有想过母亲会这么早就去世,现在她想养活她,陪她度过晚年的模糊梦境也化为乌有了。
梅玲只有十七岁。她还住原来的房间,因为一个月只要六块钱房租。靠学校朋友们的奠仪,她付完了丧葬费用,约还剩五十元。她对学校校长说,她很想教书,还把自己如何帮助母亲的经过告诉她,校长虽然同情,却告诉梅玲没有文凭是不可能的。她开始看广告应征秘书工作,但是许多工作都需中学毕业。她坦白说自己没上过学校,可是照样能把工作做好,但是每次有文凭的人就被录用。她一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
接着她在报上登广告,愿意当“家教”,这更难了。有一次她和一家人会面,对方要她教孩子们学校的功课,尤其是数学。她对数学、社会科学或物理一窍不通。她只会中国文学和作文。有人要她教国文和英文,她一个英文字都不懂。最后她总算找到了国文家教的工作。孩子们的母亲起初似乎很和善,但是三星期之后梅玲就失去了工作。次日她回去拿八本留在那儿的书本,无意间听到夫妻吵架。她一进门就听到丈夫生气地说:“她是个好老师。我知道问题出在哪,她唯一的缺点就是长得太美了。”既然已经丢了工作,她不管三七二十一走进去,拿了东西,说声“再见”便匆匆离去。
“我简直吓坏了,我的处境很严重。我一连几天满街去应征广告。为了省钱,只要不太远连电车都不坐。我看到有些广告征‘年轻貌美的小姐’当女推销员或医生助手。本来我不理这些,但是现在走投无路只好找些试试。一两次经验就够了。有一次我踏入一家单身公寓,除了一个年轻西式装扮的男士和模模糊糊的公司计划,没有一丝业务计划迹象。但是我仍充满希望,告诉自己情况再坏,去当小孩保姆总可以了吧。”
“就在这时候,”她继续说,“一些好运来临了。我曾经写过一千字左右的短篇小说,寄给当地一家报社的妇女版,结果被采用了。那个月月底,我收到通知,到报社去领五毛钱,但我得先刻一个印章,我花了一毛钱,坐黄包车要四毛,坐电车也要一毛左右。不过我若能写一千字,就能得更多。我开始提出其他有关妇女的问题,尤其是女人依附男性问题的文章。女编辑非常同情,她答应尽可能发表我的文章。”
“次月月底,我收到三元半的稿费凭单。口袋里装着自己的钱,我觉得格外骄傲和快乐。我到福州路一家饭店顶楼的戏院去,当时有一个叫张小云的年轻女伶正在那儿说书,门票两毛钱,我上了楼,经过二楼的茶室,看见一大堆人围桌喝茶。地方特别吵,你知道那地方若发生口角,都是由吵架双方的党派或村子里有头有脸的人出来调解。各阶层的观众都到屋顶戏院去,其中大多数是普通找乐子的人。”
“我独自坐在角落里的方凳上,听小云说书。每听到精彩段落的结尾,观众就大声叫‘好’,我太兴奋了,也随大家高声叫好,前面有个年轻人回头看我,后来他又找各种借口回头看我,我不知道什么吸引了他,因为我留着普普通通的短发,身穿一件南京路贫家女常穿的夏季薄衫。”
博雅打断了梅玲,“我知道,”他柔声说,“你眼中的光彩。你身上的温暖、纯真、清新的气质吸引了他的注意。”梅玲满脸通红,继续说下去,只说可不是头一次看到男人盯着她看她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