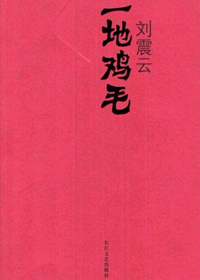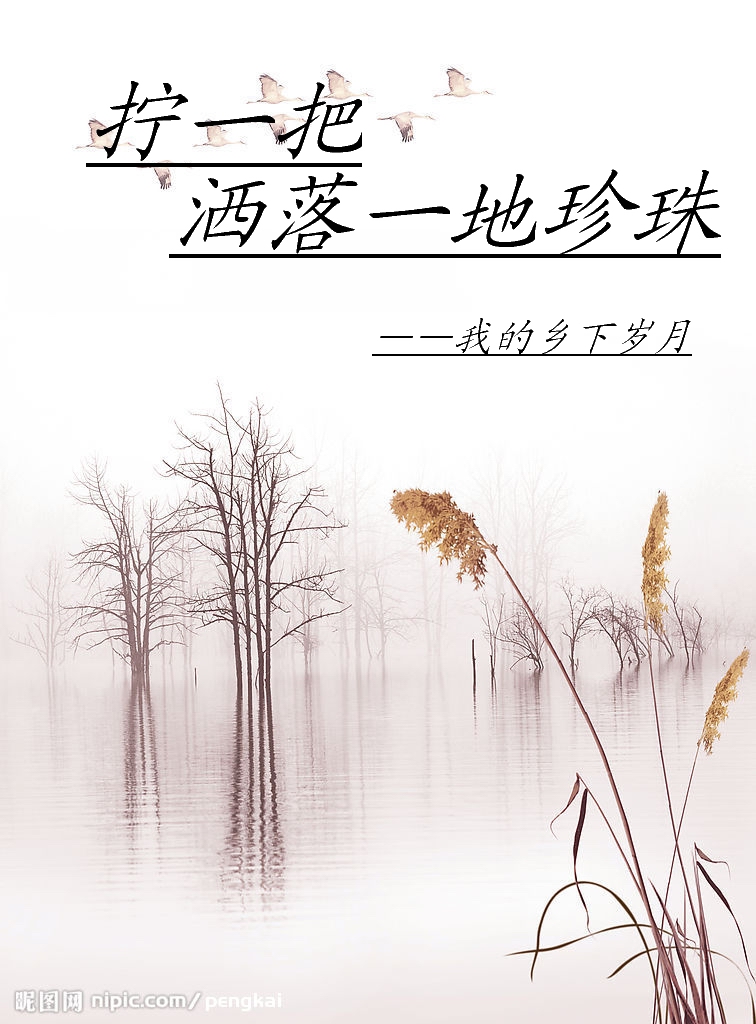一地烟灰-第2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辞。
“我说你架子够大啊,三请四催都不来,我们老两口得罪你还是怎么啦,啊?”部长硬朗甚至霸道的作风是全校有名的,但这么说我还是有些吃不消。阿姨看我面露难色,赶紧圆场道:“你凶什么凶啊?他是你的部下吗?他是我女婿!收起你那官僚作派!”部长一听赶紧打起哈哈来,看样子他也是个怕老婆的主儿。
我忙不迭解释道:“不好意思伯父、阿姨,上学期担任了骨干,实在是太忙,忙得连陪舒展的时间都没有。”
“我知道,听你们队长说你这排长当得不错,他准备这学期提拔你当连长呢。”
“啊?!”不止是我,连舒展都吓了一跳。“还是算了吧,我觉得以自己现在的能力还不能够胜任这个职务。”
“就是就是,你就别让他当什么破连长排长了,让人家安安心心当学员有什么不好。”
“没出息!”部长又骂了起来,“我知道你们俩打什么小算盘。工作忙了担子重了,就没有什么时间儿女情长了。你们年轻人啊,目光要放长远。还有你——”部长又指着舒展严肃道,“女孩子别老黏糊人,现在是奋斗阶段,以后有的是时间和机会卿卿我我?????”训得舒展舌头一伸一伸的大作无辜状。我唯唯诺诺地应着,心里却想,这一下就不止一个排而是一个连要骂我吃软饭傍泰山了。
因为“连长”有自己的房间,我搬出了和兄弟们一起住了两年半的“一排三班”宿舍,卷铺盖走人的时候,大伙都热情地过来帮把手,还说了一些诸如“好好干!”“以后就仰仗你了”的客套话,但气氛明显不如以前亲切。隔膜就这样在我离开宿舍的时候诞生了,我看着他们,无奈地摇摇头。
住进20平的“单间”,相比以前八个人挤的小宿舍自然空旷了许多。不知是睡生铺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眠。白天队长宣布“任命冯牧云同志为1连连长”的时候,周围的目光纷纷转过来齐刷刷地投向我——不是那种支持信任的目光,不是那种众望所归的目光,而是一种意外、惊诧甚至不服气的目光。每一束目光挟裹着一股热量,当他们不约而同射过来的时候,我的脸就在一瞬间被灼伤了,被烫得红彤彤的。
晚上,第一次集合全连。按惯例,要发表一篇“就职演说”,我给自己打足了气,跑步上前站在了三个排一百多号人面前。我是一连之长了,我是这一百多号人的头儿了。我的脑海里电光火石般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但刹那间我又反驳了自己:他们并不信任你,他们并不把你当头儿。
我定了定神,开始了我的就职演说:感谢同志们的支持,由我担任连长。话刚说完下面就有人笑了起来,:“谁支持你?你岳父吧?”声音虽然很轻但我听得真切。接下来,下面响起了嗡嗡的讲话声,声音依旧很小,似乎还很给我面子。我一边讲一边支起耳朵想听听别人怎么说,他们怎么评价我。我的思绪被完全打乱了,自认为很精彩的腹稿也忘得干净。我稀里糊涂讲了几句,结果发现自己都一头雾水不知所云,于是匆忙中来了两个字:“完毕!”下面百十号人一愣,随即赶紧“啪”地一下由“稍息”变为“立正”,把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大伙站在那里疑惑地看着我,话还没说完怎么就“完毕”了?刚才最后一句要写下来的话,后面连“句号”都不能接,最多能接个“逗号”。
百十号人戳在哪里看着他们新上任的连长,随即明白了,这连长连句话都不完整,接着又有人笑了起来,好像这笑声感染了其他人,在慢慢扩散、慢慢提高分贝。
“解散!”我使尽力气吼出了这句,一半是因为懊恼,一般是为了装得理直气壮一点,掩饰刚才的狼狈不堪。队伍“哄”地解散了,我一个人孤零零站在那里半天没动静,过了老半天才狠狠地骂了自己一句:“真他妈没出息!”
躺在床上,我越想越气愤,越想越窝火,我他妈招谁惹谁了,非得受这窝囊气?!不就是一破连长嘛,有什么了不起,爱谁谁啊。我打开窗户,冷风灌进来打在脸上,打在我穿着单衣的身上,吹灭了心中腾腾的怒火。我冷静下来开始仔细思考下一步该干点啥,毕竟鸭子都赶上架了。
第二天一早出完操我便拉着几个排长开了个短会,根据上学期的经历我知道排长是整个管理环节中最关键的一环,我谦虚而诚恳地和他们交流了意见并且简单地布置了接下来的几项工作。因为几个人都是上学期一起共事的骨干,彼此关系都比较熟络,虽然这次我抢了他们的位置有些不服,但看我“装得挺孙子”,也就积极配合起来。
紧接着我请老马牵头拉了几个从部队考上来的“班长”们吃了顿饭,这伙人军龄长、能力强、经验丰富、在学员中威信很高,即使他们不当骨干依旧是学员们的“精神领袖”,他们要造反绝对一呼百应,反过来说他们要顶你,这位子就保管坐得稳稳当当的。
我“班长班长”地叫着挨个给他们敬酒,把他们哄得乐颠颠的。最后的祝酒词都成了“坚决支持连长”、“坚决拥护连长”。
剩下的工作便是“三把火”了,第一把我重申和细化了一些规定和要求,并且适当放宽和修改了以前让学员比较反感的制度,同是明确了惩罚措施;第二把是逮了几个爱出头的“兵油子”,由于知道这些人都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主儿,我决定不再对他们进行一些“隔靴搔痒”式的惩罚,而是让所在班排“代他受过”,这样一来,几个人、几十个人同他一起受罚,脸皮再厚的人也扛不住。所以没等第三把火烧起来,全连基本上“井井有条”了。
我诚心实意要请老马喝个酒,因为不管是我当连长还是排长,在背后为我出谋划策当参谋的都是他,可以说要不是他我早在去年就让人轰下去了。老马说:“咱就算了,要不班里聚一聚吧,你没住宿舍了平常也忙得过不来,趁着这机会好好聊聊,免得兄弟几个生分了。”我说好。
依旧是“芬芳苑”。他们几个进来后明显有些拘谨,其中耗子竟喊了一句“连长!”把我噎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老马一瞪眼,说:“瞧你那德行,叫的啥玩意?现在是班里聚餐,哪里有什么**破连长,都按以前的来!”我看了老马一眼。接住了他的话。“哥儿几个,你们的冯子才几天不待在班里就被大伙儿这么生分啦,这也忒伤人心了。”大伙面面相觑,邱爷解释说:“其实大伙儿也没这意思,主要是考虑要给你树立威信啊,毕竟你现在是在这个位置上。”大家都跟着点头。“毬!”我啐了一口,“公共场合着么叫我不介意,关起门了你们还拿老子当外人,就是瞧不起我,”我开始上纲上线,“兄弟们都知道,我这个人好自由,不喜欢别人管,更不喜欢管别人,可人家非得把我赶出咱们班,我有什么办法?”弟兄们都沉默了。我鼻子酸酸的,开始把积了好多天的苦水往外倒,“兄弟们都知道,别人兜我‘吃软饭’说我‘傍泰山’,可我冯牧云是那样的人吗?我能怎么办?难道就因为这个和舒展分手?她又有什么错?”
“冯子,兄弟都理解你,”猪头拍拍我肩膀,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以后再听哪个孙子嘴巴不干净,咱就抽他妈的。”
“对,抽他妈的!”大伙紧紧地狠狠地跟上一句,我笑着说:“算了,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我再熬一学期,下学期,坚决洗手不干了!”我强调一句,“谁反悔谁孙子!”“好!那个下铺还给你留着!”“好!喝一个!”
“干!”
大伙都举起杯子很爽快地亮了底,接着又是一阵久违的没心没肺的笑声。
当上连长后特别忙,人在忙起来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一不小心又到了大三的尾巴上,下一步就是暑假实习了。部长把我叫到他办公室,问我喜欢学校哪个单位。“嗯?”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不是说实习下部队吗?怎么呆在学校?”“你小子脑子怎么不开窍?”部长拍拍我的头一副横铁不成钢的样子,“明年这时候就毕业了,你先在机关熟悉熟悉业务,到时候直接留下来啊。”留校?对于P大毕业生来说留校意味着最美的结局和最高的,一般来说,只有特别优秀的和特别有来头的才有可能留下来。
“对啊,怎么样?”部长殷切地看着我,他似乎在等待着我惊喜和感激的表情。
“可是,我还是想下基层锻炼锻炼,”我低下头去把每一个字吐得十分清晰。
“什么?”部长很明显被我的回答震了一下,他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重新问了一遍,我又原原本本把刚说的重复了一遍。
“哼,”他的鼻息骤然粗重起来,片刻之后他又像给自己找台阶一样来了一句,“也好,下去了解了解基层也不错,回来可以更好地适应学校的工作。”
“伯父,没事我就先走了。”我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继续下去,因为很明显我和他的想法相悖。
“走吧,”他随手拿起一份文件看着,头也不抬地招呼道,要换平时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他会放下文件笑着骂道:“滚吧臭小子!”或者一瞪眼,“急啥?咱爷儿俩好好唠一会儿。”然后就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成长史,他的从军史甚至他的恋爱史,完了还不忘神神秘秘交代一句:“注意保密,别跟我闺女说啊。”
我轻轻带上门走了。
第1卷 第十四根 “冯排副”
大三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我们所有04级学员都呼呼啦啦地奔向学校指定的实习单位,广西、吉林、青海、福建??????一夜之间P大学员就遍布大江南北。我也想远远地离开西安,最好是去一个边陲省份,感受一下不一般的生活,遗憾的是我却被分到了河南某基地的一个作战旅——距西安才几个小时车程。
大轿车把我们送到部队大院的时候已经是子夜,让我们意外的是一进门就听见铿锵的锣鼓声。我们把头扭向窗外,看见旅里的干部战士整齐地列队在马路两侧,他们后面打着红底黄字的标语:热烈欢迎P大学员来基层实习。这让我们这帮“红牌”多少有些受宠若惊。
休息了几个小时,第二天一早旅长和一些干部为我们举行了“欢迎会”,会后象征性地问我们想去什么样的单位,做什么样的工作。学员们都偷偷笑了,一个旅里能有什么样的单位,一个红牌能做什么样的工作。于是大伙异口同声回答得响亮干脆:坚决服从分配。旅长眯眯笑着不住地夸P大的学员素质就是高、作风就是硬。
接下来十多个营长前来领人。每个营分三个,还有两个旅部机关实习的名额,需要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和组织协调能力。大家都把目光投向我,似乎这位置就是专门为我留的一般。我头低下去迟迟不肯举手,在所有人看来呆在机关简直就是肥差——约束少待遇好还能学到更多东西,但我更情愿呆在班排里正儿八经体验一下基层生活,一步一个脚印把路走踏实。
最后一个会搞黑板报的和一个懂电脑的留了下来,我和另外三名学员让吉普车拉到了离大院十几公里外的郊区。
“前面就到了。”营长坐在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