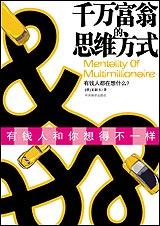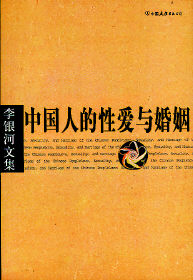性爱的思辨 作者:杨东明-第3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钥匙串叮叮当当地响着,守库的驼背老头走过来了。“芝麻,开门——”,那扇大门訇然而开。
那里面装着于潮白夫妇最珍贵的财宝,他们俩相挽着,迫不及待地走了进去。
“佑生,爸爸来了!”于潮白说。
“佑生,妈妈来了!”陆洁说。
冰柜的抽屉缓缓地拉开,儿子就静静地躺在抽屉里。小小的身体,穿着小小的新衣,宛如一个小小的的玩具。
儿子的玩具都是放在抽屉里的,儿子喜欢给他的玩具布熊、布狗、瓷猫、塑料娃娃穿衣服。儿子总是反反复复地将它们的衣服脱下来,再穿上。穿上了,再脱下来。脱下外衣之后的那些玩具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它们变成了不真实的冒充者。
儿子就反复地审视它们,观察它们,然后再把外衣给它们穿好,让它们重新变成熟悉的朋友。
儿子总是把这些熟悉的朋友放在一个大抽屉里,即使坏了,儿子也从不把它们丢弃。
抽屉是玩具们的世界,是玩具们的家。
可是此刻,象阴云一般凝重的铁抽屉已经拉开,躺在里边的大玩具,他们夫妇合力制作的这个玩具,必须从抽屉里取出来了。
“佑生,跟爸爸走——”
于潮白的声音亲切而轻柔。当初儿子蹒跚学步时,于潮白就是用这种语调念叨着,把一条长围巾系在儿子的腰间,半提半拉地牵着儿子走。
“佑生,跟妈妈走——”
陆洁的声音犹如香甜的诱铒,在一条小鱼的眼前颤动着,处心积虑地要把它钓起来。儿子见不得商厦的食品柜台,只要到了那些柜台前,他就会依偎着柜台里的五光十色,做着徒劳无望的坚守。每逢遇到这种情形,做母亲的陆洁就会用这种声音,发出不容改变的劝哄。
四岁的玩具走了,他直挺挺地躺着,绷紧了小嘴,一言不发。于潮白在前面托着他的头,另外几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分抬在架床的四周。这个可怜的小人儿,就这样不情愿地做着成人强加给他的最后一次出行。这个小人儿,仅仅用四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有百天贺席的开始,也有殡仪馆的结束,成人们给了他一个象成人一样的完整。
成人们的哀乐在殡仪馆的厅堂里徜徉,脚步犹如成人一样平稳、持重。蹦蹦跳跳的小人儿呢,雀儿一样轻巧毛躁的小人儿呢,此刻正安静地躺在那些有血有肉的鲜花和无血无肉的假花丛中。他那描画过的眉眼格外鲜明,面颊也被涂出两团红晕,望上去愈发酷似成人制作的一个小偶。
陆洁和于潮白失神地接受着亲友的唁慰,人人都看到了这对夫妻异乎寻常的悲伤,但是没有人知悉隐在悲伤深层的,是他们那无以名状的自责。
最后的程序是到后院看烟囱。烟囱竖在蓝天里,那么细那么长。天呢,天没有走,天在等着它,等着它靠上来。天是个怪物,你永远琢磨不透天。你说它是蓝的,它却发灰,你说它灰了它却又白。它似乎是透明的,然而你却无法将它望穿。它高的时候,你觉得它正在离开你、甩下你,自顾自地远去、远去,远得几乎要消失了。
近的时候呢,它就贴在你的头顶,用厚重的黑云压着你,好象要用一顶大帽子捂头盖脸地将你扣住。
烟囱是靠在天的边沿上的,天是救生的船,烟囱就象搭上舷沿的长梯。化为轻烟的生命一波连着一波,攀着那长梯接踵而去,犹如新生的虾群,汹涌着登上了彼岸。
陆洁仰着头眯着眼,久久地凝视着烟囱与蓝天相接相连的地方,那模样象是在虔诚地祈祷。一团一团的烟们推着拥着挤着跳着笑着闹着,哪一团是儿子佑生呢?
看,看那一个。那一个是圆脑袋,圆肩膀,这些部位都长得象陆洁,都有着柔和的曲线。瞧,身子拉长了,细长细长的,象于潮白了。窄腰长腿,犹如一只孤独的鹭鸶
一个男人,一个孤零零的生命个体,他只是他自己,那是属于他自己的细胞排列与组合,他与别的个体没有生命意义上的联系。同样,一个女人,一个孤独的生命,她用皮肤圈围起自己的疆域,以此守定了生物意义上的独立。变化是由游离出男体的那个细胞引发的,那是一个不安份的旅游者,它携着三十万对遗传基因,进入了女人的身体。不久,这个好动的旅游者就遇上了女人的那个细胞,那个也带着三十万对遗传基因的娴静的细胞。不知道是前者蛮横地攻入了后者,抑或是后者宽容地接纳了前者,总之,两个细胞汇融了,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
新生命寄生在后者的体内,不断地成长、成长在这个世界上,每个生命都注定是孤独的,那新生命也不例外。它最终从母体脱离而出,于是,世上就多了一个独立的生命个体。
这就是男人、女人和他们的孩子。
他们的孩子,这个新的生命个体带着属于男人和女人的遗传基因,因此,这孩子才象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
因了这个带着双方基因的孩子的存在,原本毫不相干的两个生命才有了生命体意义上的联系。
可是如今,于潮白与陆洁生命的合作之物已经化烟化灰,他们重新又成为毫不相干的两个生命个体了。
毫不相干!——想到这一点,陆洁竟浑身颤栗起来。她不由自主地靠向身边的于潮白,探探摸摸的,把手伸了过去。那动作好象是一只胆怯的兔子,委委缩缩地出了洞门。于潮白的大手掌张开来,把那兔子紧紧地攫住了。那是个毫不生分的动作,热乎乎的掌心,传递着夫妻的体贴和亲密。
然而,陆洁仍旧无法停止身体的颤栗。皮肤与皮肤的接触,更使她感到生命疆界的存在,那是一种基于生命本体的隔断,一种与生俱来的疏离。
那天晚上,当他们夫妻俩躺在那套被称为“家”的房子里,他们才真正感受到儿子的离去给他们留下的空白。那情形就象是有一张看熟了的画,上面画着猫狗,画着草虫,画着鲤鱼打挺,公鸡斗架。忽然之间,画空了,猫狗草虫鲤鱼公鸡全都不知所向,只留下茫茫然一片空白。这种变化,是让人难以接受,也让人难以置信的。
今夜,他们夫妻却偏偏与这难以置信做着残酷的面对,他们看不到那个有形有体有声有色的小人儿了!
视觉的无能和苍白,愈益显出了感觉的丰富和敏锐。他们感觉到了空气中那个人形的游走,就象在黛色的水底潜行的鱼,那摇荡的动,那回旋的搅,都是在感觉中实现的。
声音的存在也与耳膜无涉,他们感觉到了声音。那声音稚嫩得犹如春风里带雨初绽的茶芽,尖尖小小,鹅黄粉白,还生着透明的茸毛。
孩子的气味呢,他们怎么能感觉不到那气味?丝丝缕缕,如抽如扯,鲜奶一般的温馨中,混着些许带有可爱的臊味儿的汗香
然而,佑生这孩子确确实实地一去不归了。
在却不在,不在却在!——那是同属于他们俩,并且让他们俩永远也咀嚼不尽的人生的大悲哀。
躺在黑暗里,每个房间的灯都闭着。陆洁喃喃地说,“儿子的小房间,今后别动了,就那样留着它。”
“不,不行。我看不得儿子留下来的东西,我真看不得啊!——”
于潮白的胸膛里发出了一种异样的声音,那声音犹如一棵不堪负重的老树,在呻吟着,摇晃着,然后吱吱嘎嘎地裂开
“潮白,我还会生!真的,还会生——”陆洁满脸都是濡湿的泪,她近于绝望和狂乱地在于潮白的耳边哭着。
于潮白转过身,万分痛切地抱紧了她。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夫妻同房,陆洁都表现得格外努力。相形之下,于潮白却有些难如人意,每每显得力不从心。那情形,有点儿象打表演赛的一对网球手,一方提着精神长抽短吊,拼命扣杀,另一方却勉为其难,穷于应付。日子一天天过去,却丝毫也看不到新生命被孕育的迹象。于是,陆洁就变得越来越焦躁,越来越绝望。
陆洁心里明白,这多半是因为土地已经沙漠化了。沙漠化了的土地是很难生出什么果树,结出什么果实的。陆洁所患的慢性妇科炎症,已非一时治疗所能奏效。
除此之外,于潮白上场时每每表现出来的不良状态,更使陆洁心忧。虽然于潮白从来不说什么,可是他的身体在说,人的身体是会说话的。于潮白的身体在向陆洁说着拒绝,说着冷落。于潮白每一次的性无能,都在向陆洁言说着无可挽回的破裂和最终的离去
冷静的时候,陆洁也想到过和于潮白的分手。此前,陆洁甚至主动提出过离婚的事。理智和自尊都在向陆洁提出要求,离开他,离开了这个男人你照样能在世上好好地活着。然而,陆洁的肉体却在做着抗辩,它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它觉得那种情形是不能忍受的。
陆洁观察过自己的肉体,它发现肉体是有记忆力的。陆洁的肉体珍藏着许多对于潮白的记忆,到了床上,一接触于潮白,那些记忆就自动地苏醒,按部就班地将对方曾经访问过的地址一一打开。如果是短暂的分别,如果她和他的肉体没有机会接触,那么陆洁的肉体就会在独处的时候,默默地将那些记忆一一反刍。
那情形,颇象一只温情的牛,在静静的时候,在静静的角落,独自不声不响地反刍着它的拥有。循来回往,反反复复,那滋味让它咀嚼不尽
有时候陆洁忽发奇想,会认真地思索可有什么药物能够将这一切改变。欲使药物产生作用,需要找到能够发生作用的链条,这样溯源逐本,陆洁就不能不面对肉体记忆产生的最初原因。
陆洁发现,女性的这种肉体记忆是被最初进入她肉体的那个男性装填进去的,那是一种神秘的不可思议的现象。在此之前,一个女性的身体是一个孤悬的天体,它只属于它自己,而不与任何外界发生联系。那之后,一个男性靠上来了,他用他膨胀出来的身体的那一部份进入了女性。
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进入,随着这进入的发生,女性就不再是她自己。她的肉体会感到已经与那进入者合为了一体,于是便无可更改地对那外来之物生出了同一感、统一感、依附感、归属感。
一次次地进入,使得这种同一感、统一感、依附感、归属感一次次地加深,就象马臀上打了火烙一样,成为无可更改的印记。
因此,女性才会对那男性说,我是你的人了——性交合的作用,如此地精妙,如此地让人不可思议。
所以,陆洁才殚精竭虑,要重建她和于潮白之间的肉体关系。
尽管在此之前,陆洁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要和于潮白离婚。其实陆洁明白,那类话只是出于负气,无论如何,陆洁都离不开他。从精神到肉体,都难以与他分离!
她无法忍受分离,与其分,毋宁死。
凭窗而立的陆洁借着月光,翻来复去地察看着手中轻薄锋利的刀片,那神态和举止,俨然是在做着一场手术前最后的准备。
月光给那刀片淬着火,幽蓝和哑白在锋刃上蹦跳不已。
耳边仿佛有个病人在恳求,医生,拜托你了,请你下手时利索点儿。
陆洁苦笑着自语,我会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