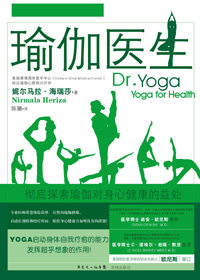赤脚医生万泉和-第3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涂医生惊慌失措,张着嘴,眼睛往下挂,语无伦次地说:“是胆道蛔虫啊!谁说是胃痛?谁说是胃痛?”自问了两遍,发现自己的思路不对,赶紧说:“快去弄船,要机帆船,马上上县医院!”万水根愣了片刻,把万小弟交给万月珍,自己转身奔了出去。万月珍已经开始哭了,她几乎抱不动万小弟了,我的两条腿也软得迈不开步子,只会傻站着。涂医生骂道:“万泉和,你站着等死?”我赶紧接过万小弟抱紧,涂医生到医疗站取了些急救的用品,一起出来,万水根已经喊来两个壮劳力,船也已经到了。大家上了船,万水根拼命加大马力,马达声震得安静的夜都抖动起来。这时候我们都希望万小弟能像刚才一样又哭又闹,可万小弟一点声息也没有,涂医生给他打了针强心针,针打下去大约一两分钟后,万小弟吐出一口气,张开了嘴,对着我喊了一声:“妈妈,哇哇。”头一软,歪到一边,万小弟就这样去了。我看到有两条蛔虫从他的鼻子里钻了出来。万月珍一看,“嗷”了一声,就晕过去了。
万小弟死了,船也不用再往县城开了,但也没有转回头。马达熄火了,船就这样漂浮在河面上,既不向前也不后退。没有一个人说话,万水根的手仍然扶着舵,他的眼睛低垂着,看着我手上的万小弟,过了好半天,他扔开了舵,“呜”的一声抱着自己的头蹲了下去。
如果换了一个强悍的农民,他这时候也许会打我,打涂医生,如果他打我,或者打涂医生,我们都会觉得好受些,可万水根是个老实人,他不会打人,也不会骂人,甚至都不会满怀仇恨地瞪着我们。他只是抱着头“呜呜”地哭,像一条被人欺负了的狗,有说不出的哀怨。
涂医生虽然也惊慌,但到底比我镇定一点,他先掐了万月珍的人中,把万月珍弄醒过来,然后说:“回吧。”队里请来帮忙的两个劳动力,都听涂医生的话,把船头调转了。万月珍从我手里抱过万小弟,低低地抽泣着,一切竟都是那么的安静。
回到队里,万水根夫妇把死去的万小弟抱回去了,我和涂医生回合作医疗,涂医生一头扎进了自己屋里,关紧了门,一点声音也没有。我流着眼泪,跑到我爹床前,我爹一如既往地闭着眼,他晚上总是闭眼睡觉,似乎再大的事情也打扰不了他。我坐在他的床边,哭诉着说:“爹,爹,你醒醒吧,你起来吧,还是你做医生吧。”我爹不理我,我就继续说着,可我爹仍然不理我,始终不理我。我说到最后,嗓子又干又痛,我借着微弱的灯光,看到我爹的眼角,滴下一滴水来,我说:“爹,你哭了。”
天还没有亮,敲门声又响起来了,我去开院子门,是万水根来了。我先是吓了一跳,以为他来算账了,我往后退了退,心里在想,你要是算账,就找我算账,我本来也不是当医生的料,借这件事情我就不当了,就不要让涂医生受过了。但是万水根两眼无光,好像没有看见我,他直直地走到马同志家门前,怦怦地敲马同志家的门。马同志一家被吵醒了,爬起来问什么事,万水根“呜呜”地哭着说:“马同志,黎同志,弟弟死了,问你们讨几个洋钉钉小棺材。”马同志拿出一包洋钉交给万水根,万水根谢过马同志,又哭着走了。我听到黎同志在和马同志说:“他的意思,是想告诉我们,赤脚医生误事了,他还会到别人家借东西的。”
黎同志的话是有道理的,到了天亮的时候,二小队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不过他们并没有到合作医疗站来说什么,他们只是挨个地跑到万水根家去看躺在那里穿上了新衣服的万小弟。女人陪着万月珍哭一通,男人陪着万水根抽掉一根大铁桥烟,然后离开,然后又来一些人,再离开,再来,离得比较近的其他几个小队也有人来看。
两天以后,万小弟就葬掉了。葬掉了万小弟,事情也就慢慢地过去了。过了些日子,听说万月珍有喜了,他们要再生一个孩子,来替代万小弟,如果能够再生个儿子,那就更好了,万小弟的阴影总会渐渐消去的。大队合作医疗也没有因为万小弟的事情就变得门庭冷落,大家该看病的还是来看病,只是回避着万小弟的话题。但是万小弟的影子在我心里却拿不掉,我老是在半夜里惊醒过来,因为万小弟老是出现在我的梦里,对着我喊:“妈妈,哇哇。”我惊醒过来,出了一身冷汗,我去找涂医生,我站在他的窗口说:“涂医生,万小弟老是来找我。”涂医生也没有睡着,他气鼓鼓地说:“他不光找你,也来找我。”我说:“那怎么办?”涂医生说:“我还想问你怎么办呢。”
其实那时候农村里生病死人也是常有的事,但万小弟的事件把我和涂医生都吓着了,我们变得草木皆兵,一点小病,明明有把握看的,也让人家到公社卫生院去,到县医院去,甚至要叫他们到城市里的大医院去。开头几次,把病人吓得不轻,后来他们渐渐发现,是我们两个赤脚医生被吓着了,小心为妙。只是这样一来,他们麻烦了很多,浪费了他们的钱,还耽误他们挣工分。不过农民虽然有想法却不敢说出来,他们只是希望赤脚医生渐渐地忘掉万小弟,恢复正常的工作,因为还有更多的病人等着他们呢。
下放干部马同志也是老胃病,痛得止不住的时候就打阿托品。平时都是涂医生替他控制药量的,但现在涂医生胆小如鼠,不敢自己开药,我们一起把马同志送到了公社卫生院。结果却因为公社的医生不了解情况,把药量弄大了,造成马同志药物中毒,出现幻觉,他弯腰站在医院的病床上不间断地做着插秧的动作。马莉和马开放学后赶来,马同志正在床上插秧呢。马莉到底还小,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看见平时严肃拘谨的父亲在床上这样折腾,不由哈哈大笑起来。马开比马莉懂事多了,他骂马莉说:“你还笑得出来,爸爸要死了。”马莉说:“呸,你才要死呢,有万泉和在,谁也死不了。”马开跟她争,说:“万泉和是个屁,万泉和把万小弟都看死了。”马莉说:“你才放屁,万小弟是涂三江看死的,跟万泉和没关系。”
涂医生在一边听了脸上青一阵红一阵,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马莉和马开在病房里吵成一团,最后被赶了出去,我追出来想劝劝他们,马开却很瞧不起我,理不都理我,一甩手就走了。马莉对我说:“万泉和,你把本事弄好了,再不要看死人了。”我想跟她说我学不好本事,但是看着马莉瞪大的眼睛,我都不敢这么说,我感觉到马莉身上有一种气势,让人害怕,我赶紧咽了一口唾沫,没有再说话。我们又回到病房,马同志的病情经过治疗稳定下来了,不再插秧,躺平了,但情绪还是有点激动,打了睡觉的针也不想睡,嘴里说:“我去罱河泥,我去罱河泥。”两只手就做罱泥的动作,一夹,又一夹,又一夹。最后药性到了,他才睡过去。
马同志的病虽然把我和涂医生都吓了一下,但回去的路上,我却意外地发现涂医生的情绪很高涨,我不知所以地看了看他,他兴奋地说:“万泉和,你看见惠医生了吗?他坐在门诊室里了。”我不知道谁是惠医生,涂医生又说:“惠医生是内科的,当初也是跟我同一批下放的,现在他已经回来了,在坐门诊了。”我把涂医生的话想了又想,也想不明白惠医生回来坐门诊跟涂医生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这么高兴。
我们到家的时候,万小三子正在院子里和马莉说什么,裘奋英守在一边,像个忠诚的卫士。看到我们回来,马莉对万小三子挥了挥手,说:“行了行了,别啰嗦了,走吧。”万小三子很听话,乖乖地走了,裘奋英也跟了出去。她现在是半步不离万小三子,也许是跟万小三子跟习惯了,离开了万小三子,她心里就不踏实。马莉跟着我们到医疗站,但她并没有进来,只是站在门槛上,朝里边看着,说:“万泉和,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帮你喂你爹吃饭的。”我这才猛地想起了我爹。因为万小弟的死,害得我总是提心吊胆,神魂不定,一有病人来,就怕他死去。送马同志去公社卫生院的时候,一路上心里就念叨着,你不要死啊,你不要死啊,竟把我爹给忘记了,要不是马莉,马同志活过来,我爹倒要饿死了。我赶紧拍马莉的马屁,我说:“马莉,你要红蝴蝶结吗,下次货郎担来了,我买了送给你。”马莉说:“你才要红蝴蝶结呢。”我说:“你不要红蝴蝶结,那你要什么?”马莉说:“我要,我要——”刚才还一脸凶巴巴的,说了两遍“我要”,她的脸一下子红了,撒腿就跑,连跑边说:“我偏不告诉你,我偏不告诉你。”
我纳闷了一会儿也就算了,小孩子的事情你不能跟她认真的。我赶紧进屋看我爹,我爹眼皮眨巴得很厉害,我知道我爹想听我说马同志的事情,我就说了。说到马同志阿托品中毒在床上插秧,我爹的嘴角流下了一缕口水,我替他擦了,继续说:“后来,后来给他打了安眠针,他还罱河泥呢。”我爹继续眨巴眼睛,我跟我爹说:“爹,吓死我了,阿托品中毒会这样子的啊?”我爹还是拼命眨巴眼睛,我说:“不过爹,这次不能怪我,不是我打的针,也不能怪涂医生,是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打的。”我爹仍然不满意,我又说:“爹,我知道,你是怪我们没有向公社卫生院的医生提供情况。”我爹这才停止了眨巴眼睛。
自从马同志生病、涂医生送了马同志去公社卫生院、再回来,这一去一来以后,涂医生的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每天一早就开门迎接病人,甚至还知道把自己和自己的屋子打扫得干净一点,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总之,我看得出来,涂医生的工作热情又回来了。我虽然不知道涂医生的变化因何而生,从何而来,但看到涂医生高兴,我也高兴,涂医生工作积极性高,我的工作积极性也高,我们的合作医疗站又开始呈现新气象。不过在我的感觉中,这种新气象和早先的辉煌似乎有些不同的味道,不同在哪里,我说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涂医生的工作比过去更加认真负责,凡是病人需要去公社卫生院拍片、化验或者做其他什么检查,他都亲自陪着去。这样涂医生三天两头就跑公社卫生院,病人很不过意,老是觉得欠涂医生太多,涂医生却乐此不疲。有几次我也觉得涂医生来来往往太辛苦,我提出来由我送病人去,涂医生坚决拒绝,不要我去。
这天下晚,病人都走了,我坐在合作医疗站门口,目光穿过我们院子的大门看到有一个人在路上奔过来了,渐渐地近了,我才看出来是涂医生。他一路狂奔着进来,最后差不多跌进院子来了,还没站定就气喘吁吁大声说:“万泉和,万泉和,马同志上调了。”我没听清楚,吓得心乱跳,我以为马同志上吊自杀呢,赶紧问:“在哪里,在哪里?”涂医生说:“在县委,听说安排在县委办公室。”我这才知道马同志是上调而不是上吊,松了一口气。我也感到高兴,但我没有涂医生高兴得那么厉害,涂医生简直有点手舞足蹈,我不知道涂医生兴奋的哪回事,就像上回他看到他从前的同事惠医生又坐在门诊里那样,我觉得他的兴奋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很长时间里涂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