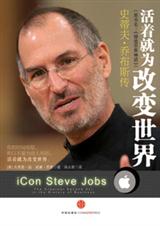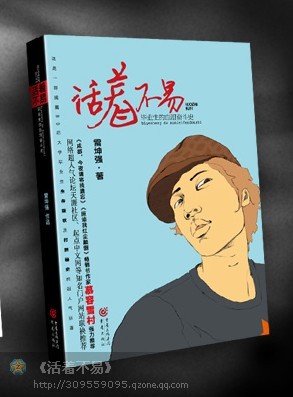活着活着就老了-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守望者》的塞林格,我想要和你睡觉。”小波也算是海龟派鼻祖,八十年代就回国了,他不搞互联网公司圈钱,不进外企当洋买办,他只在北京街头浑身脏兮兮地晃悠。他写得最好的一篇杂文是《我为什么写作》,在那篇文章里,他从热力学熵定律的角度,阐述了做人的道理:有所不为,有所必为。
今年4月11日,是王小波逝世五年祭。小波生前寂寞潦倒,死后嘈杂热闹。这些年,这些天,报纸杂志互联网拚命吹捧,小波的照片像影视名人商贾政要似的上了《三联周刊》的封面,一帮人还成立了“王小波门下走狗联盟”。我这个本来喜欢小波的人,开始产生疑问:小波到底有多么伟大?
小波的不足显而易见。
第一,文字寒碜。即使被人打闷棍,这一点我必须指明,否则标准混淆了,后代文艺爱好者无所适从。小波的文字,读上去,往好了说,象维多利亚时期的私小说,往老实说,象小学生作文或是手抄本。文字这件事,仿佛京戏或杂技或女性长乳房,需要幼功,少年时缺少熏陶和发展,长大再用功也没多大用。那些狂夸王小波文字好的,不知是无知还是别有用心。小波是个说真话的人,我们应该说真话,比如我们可以夸《北京故事》真情泣鬼神,但是不能夸它文字好。我们伟大的汉语完全可以更质感,更丰腴,更灵动。
第二,结构臃肿。即使是小波最好的小说《黄金时代》,结构也是异常臃肿。到了后来,无谓的重复已经显现作者精神错乱的先兆。就象小波自己说的,他早早就开始写小说,但是经常是写得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小波式的重复好象街道协管治安的大妈、酷喜议论邻居房事的大嫂,和《诗经》的比兴手法没有任何联系。要不是小波意象奇特有趣,文章又不长,实在无法竟读。几十年后,如果我拿出小波的书给我的后代看,说这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杰作,我会感觉惭愧。
第三,流于趣味。小波成于趣味,也止于趣味。他在《红拂夜奔》的前言里说:“我认为有趣像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这是小波的一厢情愿。除了趣味,小波没剩太多。除了《黄金时代》和《绿毛水怪》偶尔真情流露,没有见到大师应有的悲天悯人。至于思想,小波和他崇拜的人物,罗素、福柯、卡尔维诺等等,还有水平上的差距。缺少份量,小波只有三、四本书遗世,而且多为中篇。虽然数量不等于伟大,但是数量反映力量。发现小波之后,我很快就不看了。三万字的中篇,只够搞定一个陈清扬,我还是喜欢看有七个老婆的韦小宝。
总之,小波的出现是个奇迹,他在文学史上完全可以备一品,但是还谈不上伟大。这一点,不应该因为小波的早逝而改变。我们不能形成一种恶俗的定式,如果想要嘈杂热闹,女作家一定要靠裸露下半身,男作家一定要一死了之。我们已经红了卫慧红了九丹,我们已经死了小波死了海子,这四件事,没一件是好事。
现代汉语文学才刚刚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开始,小波就是这个好得不得了的开始。
2002/4/11
永远的劳伦斯
冯唐
英文书念得多些的中国人难免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中文和英文哪个更优越。我个人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数量问题。数量少,二、三十字以下,中文占绝对优势。有时候,中文一个字就是一种意境,比如“家”字,一片屋檐,一口肥猪,睡有屋食有肉就是家。乱翻词谱,有时候,中文三个字的一个词牌就是一种感觉,“醉花阴”,丁香正好,春阳正艳,他枕在你的膝上,有没有借酒说过让你脸红的话?“点绛唇”,唇膏涂过,唇线描过,你最后照一下镜子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的眼睛?五言绝句,有时候,二十字就是一个世界,比如柳宗元的《江雪》,有天地人禽,有千古幽情。数量多些,比如两、三千字,中、英文持平。三袁张岱的小品同兰姆、普里斯特利的散文一样耐读。数量再多些,比如二、三十万字,英文占绝对优势,中文长篇几乎无一不可批为庞杂冗长,而不少英文长篇充满力量。
这种力量感,最强烈地来自劳伦斯的文字。
劳伦斯生于一八八五年九月十一日,一九三零年三月二日死于肺痨,终年四十四岁,是本世纪文学史上重要得不能再重要的人物。他上接狄更斯、哈代,下启詹姆斯、福克纳,是近、现代文学的连接人。最重要的作品有:《儿子和情人》,《虹》,《恋爱中的妇女》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儿子和情人》是劳伦斯的成名之作,小说旧瓶子装新酒,篇章结构不出维多利亚小说窠臼,但是社会背景已经不再重要,人物心理开始唱主角。小说写尽恋母情节,有些男人天生是女人的儿子,同妈妈的联系绝对不止是一条脐带,一把剪刀不可能剪断。没有情人,他们不能长大,情人的作用是让他们意识到他们离不开妈妈。美国现代图书馆的二十世纪百部小说排名上,《儿子和情人》远远比劳伦斯其他入选小说靠前,看来酒还是比瓶子更重要,老实作文比故弄玄虚更有效。没准百年后念中文的人偶然记起琼瑶,只是因为《窗外》。《虹》,《恋爱中的妇女》和《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松散的三步曲。记得第一次读《虹》的时候窗外雨疏风骤,几十页书念得我心惊肉跳,我忽然发现有些人闲了,可以想出这么多事情。这些小说中的女人,让我想起交配后要杀死雄性伴侣的雌性昆虫。
劳伦斯是能于无声处听见惊雷的人(昆德拉是另一个)。人最大的悲剧不在外部世界,不是地震,不是海啸,而在他的内心。劳伦斯临死前将自己的一生概括为:A savage enough pilgrimage(残酷的朝圣之旅)。或许就是这种苦难,这种对自己的心灵绝不放过的苛求,造就了文字的力量。中国文人最吃不得的是心苦,讲究的是寄情诗酒,内庄外儒,心态平和最重要。或许,文章的区别,中文和英文的区别,说到最后还是人的区别。但是我没有道理地相信,任何一种文字,不吃苦,体会不到苦难,写不出苦涩,一个作家永远成为不了大师。
谈劳伦斯,不能不提他的最后,也是最遭非议的一部小说《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小说遭非议是因为性爱描写,但是它成名篇并不仅因为它。小说主题重大:人,性,自然,工业,异化。结构精巧:以性交为故事骨架,九次性交,由初相见到高潮迭起,由地升天,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如果勉强算,李渔的《肉蒲团》也能算是以性交为主线)。
“她完全沉浸在一种温柔的喜悦中,象春天森林中的飒飒清风,迷蒙地、欢快地从含苞待放的花蕾中飘出在她千丝万缕互相交汇的身体里,欲望的小鸟正做着美好的梦。”
屈原要是读到这样的文字,一定会想起那些穿兰蕙佩香草和他关系暧昧的女祭祀们。但是,现在是二十世纪,不少人已经觉得劳伦斯假道学,充满基督式说教。要是亨利?米勒写人格异化和自然之间的冲突,上面的一段文字就会被一句化代替:“当你烦躁迷茫的时候,操。”(《北回归线》“When you feel confused; fuck。”)
1995/6/7
难能的是当一辈子“流氓”
冯唐
亨利米勒是我了解的文化人物中,元气最足的。
从古到今,有力气的人不少,比如早些写《人间喜剧》的巴尔扎克,晚些写《追忆似水年华》的普罗斯特,中国的写170万字《上海的早晨》的周而复和写200万字《故乡面和花朵》的刘震云。这些人突出的特点是体力好,屁大股沉,坐得住,打字快,没有肩周炎困扰,椎间盘不突出。他们的作用和写实绘画、照相机、录像机、录音机差不多,记录时代的环境和人心,有史料价值。
从古到今,偶尔也有元气的人,他们的元气可能比亨利米勒更充沛,但是由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留下的痕迹太少,我无法全面了解。比如孔丘,抛开各种注解对《论语》做纯文本阅读,感觉应该是个俗气扑鼻倔强不屈的可爱老头,一定是个爱唠叨的。但是,当时没有纸笔,如果当时让孔丘直抒胸臆,现在大熊猫一定是没有竹子吃了,长跑运动员一定是没有王八汤喝了。耶稣对做事的热情大过对论述的热情,不写血书,只让自己的血在钉子进入自己肉体的过程中流干净。佛祖可能在文字身上吃过比在女人身上还大的亏,感觉文字妖孽浓重,贬低其作用:如果真理是明月,文字还不如指向明月的手指,剁掉也罢。晚些的某些科学家,想来也是元气充沛的人,比如爱因斯坦,热爱妇女,写的散文清澈明丽。可能是受到的数学训练太强悍,成为某种束缚,他最终没能放松些,多写些。
亨利米勒是思想家。亨利米勒的小说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成形的人物,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有主题,没有悬念,有的是浓得化不开的思想和长满翅膀和手臂的想象。真正的思想者,不讲姿势,没有这些故事、悬念、人物像血肉骨骼一般的支撑,元气慓悍,依然赫然成型。既然不依俗理,没有系统,亨利米勒的书可以从任何一页读起,任何一页都是杂花生树,群英乱飞,好像“陌上花开,君可徐徐归”。在一些支持者眼里,亨利米勒的每一页小说,甚至每十个句子,都能成为一部《追忆似水流年》重量级的小说的主题。外国酒店的床头柜里有放一本《圣经》的习惯,旅途奔波一天的人,冲个热水澡,读两三页,可以意定神闲。亨利米勒的支持者说,那本《圣经》可以被任何一本亨利米勒的代表作替代,起到的作用没有任何变化。别的思想家,是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站在巨人们的肩膀上,添加真正属于自己一层砖瓦,然后号称构建了自己的体系。亨利米勒不需要外力。一个小石子,落在别人的心境池塘里,智识多的,涟漪大些,想法多些,智识少的,就小些,少些。亨利米勒自己扔给自己一个石子,然后火山爆发了,暴风雨来了,火灾了,地震了。古希腊的著名混子们辩论哲学和法学,南北朝的名士们斗机锋,都有说死的例子,如果把那些场景记录下来,可能和亨利米勒的犀利澎湃约略相似吧。
亨利米勒是文学大师。崇拜者说,美国文学始于亨利米勒,终于亨利米勒。他一旦开始唠叨,千瓶香槟酒同时开启,元气横扫千军。亨利米勒是唯一让我感觉像是个运动员的小说家,他没头没尾的小说读到最后一页,感觉就像听到他气喘吁吁地说:“标枪扔干净了,铁饼也扔干净了,铅球也扔干净了。我喝口水,马上就回来。”
我记得第一次阅读亨利米勒的文字,天下着雨,我倒了杯茶,亨利米勒就已经坐在我对面了,他的文字在瞬间和我没有间隔。我在一秒钟的时间里知道了他文字里所有的大智慧和小心思,这对于我毫无困难。他的魂魄,透过文字,在瞬间穿越千年时间和万里空间,在他绝不知晓的一个北京市朝阳区的一个小屋子里,纠缠我的魂魄,让我心如刀绞,然后胸中肿胀。第一次阅读这样的文字对我的重要性无与伦比,他的文字像是一碗豆汁儿和刀削面一样有实在的温度和味道,摆在我面前,伸手可及。这第一次阅读,甚至比我的初恋更重要,比我第一次抓住我的小弟弟反复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