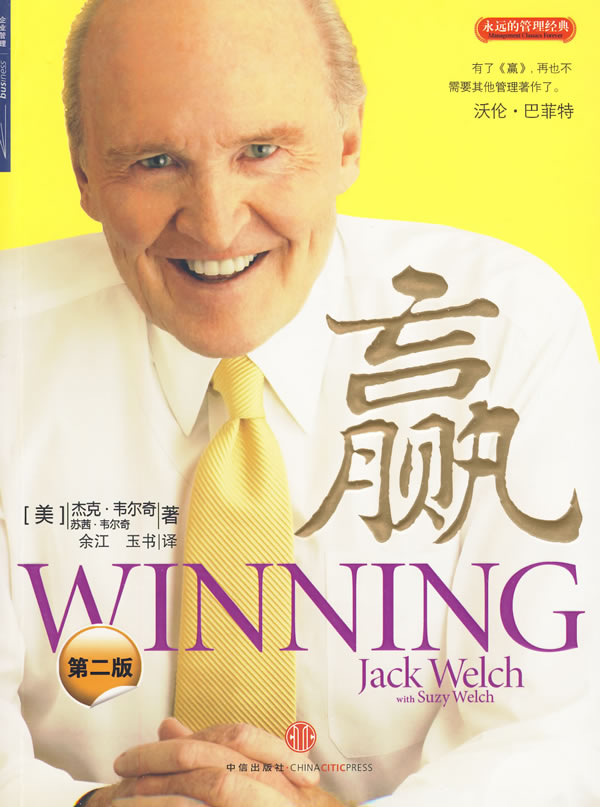邪魔女巫-杰弗里·亨廷顿-第2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知道她是个夜间飞行的力量。她有和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一样的力量,所以,我们拧成一股劲儿制服她是有道理的。”“不只是我们拧成一股劲儿。”西比拉对他说,“你看,伊泽贝尔从她和魔鬼打交道中学会了某种技能。她学会了一种作用于某类夜间飞行的力量特别的力量。”她停下来,回头看着自己的丈夫。“就是女夜间飞行的力量。”
阿日努尔夫只是低声哼着。
“你见过她,”威格拉夫对得汶说,“她很美,对不对?”
“她是个女妖,”得汶说,“是不是?”
西比拉点点头,“她是。一个夜间飞行的力量的女妖,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对她迷人的美丽动心,都想获取她的芳心。她已从村子里很多妻子手里夺走了她们的男人,作为夜间飞行的力量,也没有更多的免疫力。”
“首先我们是男人,”阿日努尔夫仍盯着火,发着牢骚,“除了我们的力量,其他的和常人都没什么不同,都太人性化了。”
得汶完全理解他说的。“可她要被打败了,”他坚持说,“看,我不只是从另一个地方来,我来自另一个时代,未来。夜间飞行的力量的历史显示,伊泽贝尔将被烧死在火刑柱上———那将会是女夜间飞行的力量们征服她的。”
“那么我们会成功的。”阿日努尔夫高兴地说,“我们不用怕了,那么,我们得做些什么。”
“这孩子不是来这儿灌输自满的,”威格拉夫警惕地说,“他是来树立自信的,你们也会失败,阿日努尔夫,然后整个历史过程将被改变。你每次必须像命运中描述的那样扮演你的角色。”
他们决定为将要到来的时刻休息一下,有人给得汶把一捆稻草铺在有火的地方附近。他安置好,放好这些带有刺激性的稻草,想找个舒服的姿势。威格拉夫已经在椅子上发出鼾声了,盖瑟丽和她父母不见了,她们去了房子的另一边。
“如果我在这儿中圈套了怎么办?”得汶又一次想。“如果这是我的命运怎么办?在这个时候,给那些要打败伊泽贝尔的人带来信心?”
他估计不会有这么悲惨的命运。的确,他已经不得不习惯没有电视、汽车、计算机、电影、冰淇淋和比萨了———可他有骑士、城堡、魔法师的发明和随时可以饮用的啤酒代替它们。的确,他得习惯街上没人清理下水道的臭水沟,室内没有暖气。可他在一个夜间飞行的力量家族长大,甚至能参加威格拉夫任教的夜间飞行的力量学校,那一定比对付吃力的老魏斯白先生更好。事实上,他和这些与塞西莉、罗夫、格兰德欧夫人十分相像的人在一起已经感到很舒服了。甚至还有伯爵恩———如果他能被人们从伊泽贝尔手里救出来,得汶知道他会的,因为从现算起的五百年后,他还活得好好的。
可如果得汶留在这儿,谁会在二十一世纪征服伊泽贝尔呢?谁会在她的进攻下拯救乌鸦绝壁的人呢?他父亲给他看的情景会成真吗?甚至他不用到那儿打开地狱,如果他不能阻止伊泽贝尔,他能听见对他的责备,塞西莉和他其他的朋友会死在血泊中吗?亚历山大得活到作为一个臭鼬逃走的那一天吗?罗夫怎么样?罗克珊娜能从伊泽贝尔的符咒中救他吗?或者伊泽贝尔先统治了乌鸦绝壁,然后是整个世界,他会变成她永远的奴隶吗?
“休息了吗,得汶·马驰?”
他抬头看了看,盖瑟丽穿衣睡衣,手中向上举着一只蜡烛。
“哦,这的确不像我在乌鸦绝壁的床。”
她坐在他边。“给我讲讲你的床,给我讲讲未来,我想知道。”
他叹口气。“有很多事物值得介绍:你会走得更快,因为我们有汽车和飞机———”
“飞机?”
“是的,像船一样,只是飞机从天上飞过去。”
“这是夜间飞行的力量的魔法吗?”
“不,只是正常的,不是万无一失的技术。”
“技术?”
她点点头,似乎领明白了他的意思,“未来的女人是怎么样的?”
“哦,你还真挺像塞西莉的,似乎完全一样,或者无论如何差不多。女人能做她们想做的,可能成为她们想做的人。”
盖瑟丽笑了。“哦,那很好,我同情现在的一般女人。她们在所有的关系上,都是她们父亲和丈夫的附庸。当然,她们夜间飞行的力量就不同了。可我们在和正常人打交道的日常行为中我们必须假装服从,”她做了个鬼脸,“我很烦这么做。”“我能理解。”
她用含有爱意的眼睛望着他,烛光照亮了她的脸。得汶看着。他也看见了塞西莉。
“像未来一样美妙,得汶·马驰,”盖瑟丽乞求说,“别离开我回那儿去。”
他冲她露出一丝苦笑,“我都不确定我能回去了。”
“你会慢慢接受你现在的时代的,你会成为这里伟大的魔法师。我知道的。”
回房间之前,她过去轻轻地吻了吻得汶的脸。得汶又在稻草上伸展开四肢。他几乎一晚上都没睡着,女巫还在她的梦里,尽她狡猾之能,尽她引诱之能。“我会抵制你的。”他说道。可她只是冲他放声笑笑,寒冷恐惧压倒了他,他比害怕女巫还害怕自己的恐惧。“那会打败你的,”在梦里,他脑子里的声音还是告诉他。
早晨,计划要付诸行动了。得汶跟着阿日努尔夫和西比拉穿过街道,避开前天的能记住他的城里人的眼睛。“这个秘密的会议在哪儿举行?”得汶问威格拉夫。
“现在我要是知道了,那还会是秘密吗?”
“哦,阿日努尔夫一定知道。”
“我们在这儿停下。”阿日努尔夫突然说。
他们站在村庄尽头的黄花地里,那是一片摇曳着黄色、延伸到地平线的花的海洋,这又一次提醒着得汶时间怎样变得非线性,当他离开二十一世纪时还是严寒的冬天,这却是夏末了,又闷又热。
可是,他没法理解为什么他们单单停在了黄花地的中间,“聚会在外面举行吗?”得汶问道,“那是多么精明啊!”
“这是我们举行会议的地方。”阿日努尔夫解释说。
得汶注意到其他人现在也正往地里走来,他认为他们是其他的夜间飞行的力量,可他看他们时,他们一个个似乎被猛烈的光反射得看不见了,然后他感觉到自己在发光,他的同伴们也是。“怎么了?”
没人有功夫回答他,因为下一刻得汶看见他们不再在田地了而是在一个石头建筑物里面。他们现在一个大厅的地面上,抬头看着一个红蓝星星镶嵌的花式在他们头顶上形成一个雄壮的圆顶。这地方充满了夜间飞行的力量———上百的夜间飞行的力量。得汶知道他们是夜间飞行的力量,因为他们胳膊上的汗毛都立着,就像他在乌鸦绝壁地下密室中的那些书里看到的一样。最后被其他和他一样的人包围了,他突然感到脸色绯红,呼吸困难。
“这是举办盎格鲁-撒克逊会议的地方吗?“得汶问。
“是的,孩子,”威格拉夫对他说,“尽管官方聚会今晚半夜才开始。我们现在聚在一起只为了一个目的:打败女巫。”
“我要求这个聚会要有秩序。”一个巨大的老人在前面的大厅里,突然大声地敲着小锤,用低沉、爽朗的声音说。“那是塞莱道哥·埃皮·格鲁菲德,不列颠最有力量的魔法师。”威格拉夫对他说。
塞莱道哥看上去挺凶的:长长的头发,深陷的黑眼睛,鹰钩鼻子,巨大的手抓住教堂的讲经台,似乎要把它弄成两半。他站起来将近有七尺多高,肩膀大约有四尺宽。“他是个好家伙,我确信。”得汶说。
“是的,”威格拉夫说,“很好,可让人畏惧。”
夜间飞行的力量分成两排,男人、女人、孩子都说自己的语言:英语,法语、丹麦语、德语、芬兰语、瑞典语、俄语、比利时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土耳其语、汉语,他们皮肤的颜色反映着夜间飞行的力量来自范围广阔的地域,从白色到闪着亮光的黑色。
得汶从盖瑟丽旁边溜进一排座位,东张西望地看着他能看到的。
“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尊贵的国王亨利的密使,”塞莱道哥对他们说,“苏福克公爵。”
“那是国王的嫂子,”得汶对盖瑟丽低声说,他很兴奋地想起了从魏斯白的课上知道的一些事情。
尽管站在塞莱道哥旁边的公爵显得又瘦又小,可他还是个大男人,他戴着一顶皮帽子,和得汶的是一样的,可他的上面镶着红宝石和绿宝石,“我听见我们中那个伟大的魔法师说话很长时间了。”公爵向人群致意,“可直到现在我才真的相信这一切。”
他对面前的聚会很敬畏,得汶能够理解:毕竟是他亲眼见到成百上千的人出现在这个大厅里。
公爵说,“我的君主想求你们帮忙消除这个国家的灾难———一个女人要推翻到他的君主,用英格兰的力量使魔鬼荣耀!”
夜间飞行的力量低声说,他们同意。“可当她用美貌去引诱一个男人———甚至就是你们中的一个———进入一个恐惧和欲望的泥坑时,我们能怎么做呢?”
人群中激起一阵笑声,西比拉站起来时得汶吃了一惊。“我的上帝,这个聚会中将近一半的人无法抵制女巫的魔法,因此击败她的策略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可你只是个女人。”公爵说。人们又发出一阵笑声。
“因为她,你和你的国王对这灾难如此恐惧。”西比拉坐下来说。
塞莱道哥·埃皮·格鲁菲德又挪回讲经台。“西比拉是对的,我们必须依靠我们的夜间飞行的力量中的姐妹们征服女巫。”
现在轮到威格拉夫站起来了,“伟大的塞莱道哥,能不能让我说句话?”
“当然可以,威格拉夫。你是我们监护人中最伟大的,你想补充点什么?”
威格拉夫用胳膊肘顶了顶得汶,示意他站起来,“尊贵的夜间飞行的力量,如果可以的话,我向你们介绍一位拜访我们时代的年轻人———”。“威格拉夫,你要干什么?”得汶的脸刷地红了,他小声地从牙缝里挤着字———“为什么你———”。
“他的名字叫得汶·马驰。”威格拉夫不理他继续说道,“他带着侯雷特·穆尔的保佑来的。”
得汶觉得似乎要融化在座位里了。几百张夜间飞行的力量的脸都转过来看他。他,从纽约的考斯—詹克森出来只有几个月,他好像有许多关于他们的知识、经验和他们对夜间飞行的力量历史和传统的理解———”
“你进过地狱又活着回来了。”脑子里的声音提醒他。
“噢,”塞莱道哥说,“侯雷特·穆尔,我们未来的时光旅行者,我们的后代。告诉我们你带来什么新闻了,得汶·马驰?”
得汶站起来,希望没有人———尤其是盖瑟丽———会注意到他的膝盖在发抖,“哦,嗯,”得汶盯着威格拉夫结结巴巴地说。
“给参会的人讲讲看见女巫的事儿。”他的监护人说。
“哦,好的,我是见过她,女巫伊泽贝尔。”他低头看着盖瑟丽,我们———盖瑟丽和我———跟踪土地神,伯爵恩·弗克比亚德———”
“你们做了什么?”塞莱道哥突然大声说。他的脸突然在不易察觉的愤怒中扭曲了,人群中引起了义愤,人们低声嘀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