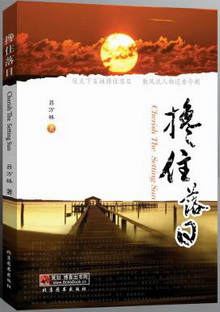搀住落日-第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爷爷在新房子里未能住上几年就离我们而去了。他其实死在他心甘情愿的奉献岗位上。南河那边的姑婆婆家砌屋,尚未恢复元气的爷爷住在那儿帮忙“放树”、做砖,累倒了,自个儿拖着苍老疲惫的身躯,翻山越岭过河而归,半路上有老熟人轻叫:“跟我回去吧!”爷爷恍忽觉得此人早年得“痨病”死了的,回家后高热寒颤,一病不起,不足两月即艰难而依恋地咽下他那最后一口气。唯一在场与爷爷诀别给爷爷送终的我,痴望着爷爷亲手粉泥的凸凹不平的墙壁,轻抚着盖着爷爷那瘦小身躯的蓝家织布被子,感慨万端,悲叹良久。
我跳出“农门”后,老家经历了“分田到户”、“棉改梨”、“梨改桔”、“水果又改回棉花”的风风雨雨,当年的新房顺理成章地变成旧屋,如今又不可抗拒地变成老屋,当年的“硬扎劳力”父母如今已极不情愿地变成年逾古稀的老人。六个子女六枝丫,没一枝枝丫能守家。两老相依为伴,相濡以沫,尽管父亲性急而犟,母亲性温而不乏刚,然而两老经过将近一生的磨合已能互谅互让,平和相处。这方面我放心,两老也从不给我添丁点麻烦。令我最不放心的是两老的身体。人老了,内部零件都老化了,加上他们一生辛劳,小时没吃甚么好的没喝什么好的,长身体之时营养奇缺,成年以后劳累过度,年老之后还独自撑持自食其力,心脑肾、肝胆脾、手足臂腿怎生抵御岁月的磨蚀和经年劳作的消耗?两老都患有高血压,每次回老家,或者两老每次来我这儿,总是叮嘱他俩按时吃药,常到村卫生室量血压、戒激动,叮嘱父亲少喝点酒、不喝酒精勾兑的酒。本来还要劝他少吃大荤和动物内杂,然一想到他已这么一大把年纪,何况还经常挑一两百斤重的担子,便没劝。我住在这县城,最骇怕的是半夜三更来电话或大声急喊“开门!”。1991年的腊月十九,有人夜半耸机关小院铁栅门高声叫我,为的是老二已昏迷,过江来入了县医院。经一天一夜的急救,刚刚33岁年轻力壮的二弟因脑溢血而撒手人寰!自那以后,我听不得半夜敲门、电话响或高声叫我,一听便毛骨悚然、浑身瘫软。然而,最骇怕的事还是朝我走来了!
1998年是包括羊角洲在内的所有百里洲人最要命的年份。孤洲危悬于滔滔大江之中,10余万条性命系于一条弯弯曲曲的老民堤之上。管涌来了,洲民扛着麻袋、抬着毛石冲上去,堵住了黄龙的偷袭;渗漏来了,洲民挑着土担卵石担围上去,一个时辰内筑起一截新的围堤……然而,惊心动魄的汛期过去,久被洪水困居、折腾的洲民中,有的累病了,累垮了,有的老病复发了,有的染上新病怪病。一日突接电话:老父倒在床上动弹不得了!我心急如焚,驱车直抵轮渡码头,远望着还停在对岸未开的轮渡船眼里直冒火。幸亏,老父是得的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经几月治疗便恢复如初。同年冬天,大妹打来电话:母亲从田里弄了猪草回屋,躺在拖椅上不省人事了!我又急又怕,急得恨不能飞过河,奔至母亲身边,怕母亲脑溢血,抛下我们走了。用车把母亲运到县城,住进医院作了初步处置,母亲才睁开双眼,如梦初醒:“怎么到了这儿?”眼睛搜索到我们兄弟,惊问:“你们怎么来了的?”直令我们作儿的心酸无比,羞愧不已。人常说“小时候父母为你端屎端尿,父母老后你为父母端茶递水”,我们无能呵,大几十岁了,居然照顾不到年迈命苦的父亲……
为从源头解决令我骇怕的问题,我一直在尝试、在努力。起初,我给父母“定”的“退休”时间是60岁,劝他俩届时把责任田退掉,只在门前菜地里种点自食的菜蔬,了不起再喂一头猪、几只鸡。花甲之年到了,他们没有一点“退下来”的意思,只得我去“督办”,结果可想而知,我无功而返,两老一如既往:种了两亩梨园,养了一头母猪一头育肥猪,外带三分菜地。父亲自有安排:“海华(我大弟的儿子,父亲仅此一男孙)考取大学后再说吧。老二正拉‘儿滩’,我趁搞得动,帮他一把呀!”只得作罢。海华上大学,父母卖梨子的钱还未攥热乎,一千块钱交给海华他妈:“没多的,就这点儿,算婆婆爷爷的智力投资,我们高兴哪!”我瞅空儿即颁“退休令”:“您们的孙子考上了大学,您们的奋斗目标已实现了,这下该把田退掉吧?”父母同声抗议:“不行不行!海华上了大学,接下来轮潇儿上大学了。我们知道你们不差这几个钱,可潇儿的学习成绩这么好,明年兴许上北大清华哩!不行,这么优秀的孙女,我们不投点资划不来啊!”去年,潇儿真的考取了北大,两老送来一千块,平时总是喜得眉开眼笑,田也种得更起劲。这回,我们几姊妹一起逼两老退田,可父亲有了他的新盘算:“梨子田不种,没人接呀。别人都把梨子树挖掉又种棉花噢。与其荒在那儿,不如稍微照管一下,多少可结几个果呵。再说,树下边还可种点猪草栽点苕,退掉了猪子吃什么?还有,潇儿下边还有几个小家伙(指我大弟的女儿、小弟的女儿及三个妹妹的子女),他们到时候上大学,如若我们奔得动,也还想投点资咧。”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也曾出现过转机。2000年春夏之间,死亡之神差点儿把我母亲掳去,只差那么一丁点儿。一日下午,父母共进了午餐之后,母亲洗碗收灶台,父亲下地去。收拾完毕,母亲提着满满一撮箕垃圾,经厨屋南门穿过堂屋走向“稻场”西南角的粪坑。这时,只听得“轰隆隆”一声,惊得母亲手中的撮箕“哐啷”落地,垃圾四散。朝厨房西山墙的轰声处一看:糟了,出拐啦!只见厨房屋顶烟尘滚滚,直冲遮掩着厨房的竹梢树梢。厨房塌了!母亲的脸吓得煞白:“天啦,差一点儿要了我的老命!莫非‘嘎嘎’(我外婆,2000年正月初一无疾而终)在那边蛮孤单,要我去打伴?”我一边取钱安排修房,一边抓紧组织“劝退攻势”。兄弟姊妹劝,妯娌妹夫劝,同族叔婶劝,还专程到幺幺家,搬来幺幺、姑父劝,终于松了口。于是,我们夫妇俩会同小弟,在城区周围四处找房,条件有点苛刻:离城中心不远(便于我们常去问问安,送点吃的喝的穿的),三大间砖瓦房,厨房、厕所、猪鸡栏齐全,屋前屋后有菜地,东西两头有邻居,门口有树和空地。好不容易觅着符合条件的一处房地产,价钱谈好了,待成交前夕,父母急带信来:“还是不想离开老屋”。我的心里呃,真不是滋味!
那年回老家过年,父亲与我道出了衷曲:我和你妈眼看就70岁了,虽然如今的人均寿命70多,而与你老爹(指我爷爷)比,我已多活了好几年了,我们都划得来了。剩下的日子,活一天算一天哩。你不要再起这个心了,你们的心我们领了。即便哪一天我一夜醒不来,硬在床上了,保证隔壁邻居和吕姓后生会很快来张罗后事,通知你们回来看我最后一眼。或是中风瘫在了床上,他们也会很快把我送去抢救并通知你们快快回来料理的。你们放心,啊?再说,过河到县城去住,我们也不习惯。四邻都是生人,等混熟了早就入土了。住在生地方,一天到黑就像关在笼子里,老了还来受这份孤老罪,不值得。还有,我们的祖宗八代都生在这洲子上,埋在这洲子上,我们两老也是一样,我们是羊角洲的洲民,羊角洲是我们的洲子,我们与洲子互相离不得。已经去世的祖先每天都看着我们,护佑着我们,我们也得看着他们,扶侍着他们。故土啊,祖先啊,真的离不开呀!
这,就是我的心憾。
我想,当今社会,住在城里的为人子的,定有不少人有着与我同样的心憾。因为反哺之情人皆有之,孝敬年迈父母是我们乐意也不容推辞的义务和责任;而坚守乡下老家的作父母的,故土和祖先难离又是人所共有的,有着悠久传统的。这样就产生了矛盾:子女尽孝心,父母便要舍故土;父母守故土,子女就难尽孝心或难以尽全孝心。一个真正的完全彻底的孝顺子女,理该尊重父母的感情和选择,尽可能给父母打造一个比较满意的“老巢”,平时多回老家嘘寒问暖,切莫顾及自己的名声(“不孝”的骂名)而强拉硬拽老人入城受罪。是的,尊重老辈的选择是会给作人子的留下永远的心憾,然而,哪怕是这个心憾再深再疼,我们也不能强求父母,以让他们颐养天年,老有所乐。
昨日,老家又捎口信来:明天是你们的星期休,我们宰年猪,回来吃“血幌子”!
我坐在江这边的书桌前,默望江那边故乡的方位,想:今年的年猪膘多厚?
拥吻老城
年近半百,仿佛睡了一大觉,世界上的好多事物怎么离了我这么久?你看,这年把以来,我不知怎么回事,竟多次向老父打听老城的消息。其实隔得又不远,渡过江,穿过百里洲,再过小河,上岸即是。可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就是没去过。也曾有过几次机会,多因公务缠身,又怕耽搁同行人,都未作成顺道之访。心里呢,只要一静下来闲下来,总要惦念上她。
癸未年的腊月十一,暗香浮动似的淡雾缭绕在羊角洲的座座农宅上,久久地依恋着不肯离去。刚为老父老母做过七十大寿,但因一直没能给老娘选上一双皮棉鞋,始终觉得是个缺憾。老父也许揣摸到了我的意愿,“今日天气不错,到老城给你妈买鞋子去吧!”遂率我和三弟徒步而去。
快过年了,洲民们有的在闹腾着宰年猪,有的在抓紧为梨子树柑子树上肥,有的在油绿的桔树下扯萝卜菜以便用手推车运回去喂猪,还有的携带家带口去亲戚家“吃血幌子”。如今生活好了,平常都像过年,但却缺少早早地酝酿过年的这种气氛。过年,不仅仅是吃好的穿好的亲友聚在一起玩好的噢。
儿时过年的氛围,多是由老城营造的。盼了一年的“办年货”,虽然皆由父亲独去,但我们总是先盼后喜最后乐颠颠的。到得那一天,父亲被母亲收拾周正,挑着一对空箩筐,怀揣着一叠参差不齐烟叶子样的毛角子出发了。西边的日头树把高的时刻,等不及的我们几兄弟早跑到“开头”村口去引颈眺望了。父亲对于像狗娃子样围拢来的我们,总有赏头,有时是圆果子“麻占”,有时是长条子“龙酥”,有时竟是好玩儿的铃铛儿、珠裹子、铜镲镲子,或是专给小家伙戴的“狗圈儿”。至于箩筐里装的芹菜、木耳、藕、姜、鱼、笋、鞭、香样样年货,在我们眼里,则一律溢满喜气吉祥气,倏忽间,这吉祥气喜气就溢上了我们的脸。进入“腊八”,从老城下来的商人川流不息,我们家在大路旁,又是高台子,不住地走来老城客,不时地有风格各异的叫卖叫买声,传来:“磨剪子唻,戗菜刀唉!”“收购破铜啦烂铁呀旧棉絮唻布巾子哩!”“针线儿顶顶儿白雀灵还有雪花膏呐!”“珠裹子哟狗圈儿哟年画哟娃娃书哟!”“颗颗糖耶打巴糖耶棒棒糖耶芝麻糖哎!”“麻花子唻油裹条唻堆沙饼子呃!”且不说所叫喊的内容诱惑人,便是其喊声简直是唱声更吸引我们。不像如今商贩的叫卖声,“卖米!”“液化汽!灌汽!”“渣货!收旧电视旧冰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