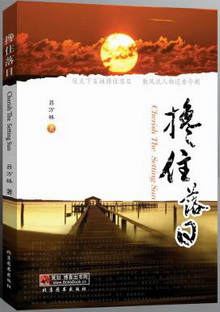搀住落日-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槐 哥
我的出生地位于百里洲之首的羊洲。22岁时通过高考跳出“农门”,此后,在那儿生活的时间便极少极少了。即便逢年过节偶尔回去住住,也只是以“客边”的身份,而一个地方的灵魂,是万万不会交给它的客人触摸的。因此,当我如今来写羊洲时,我只敢写我脱掉农装之前的羊洲——姑且称其为“老洲”吧。
在老洲上,我最敬重的人就是槐哥。
老洲本名吕家河,可能源于其开拓者是我们吕姓的祖先。传、家、中、正、万,到我们“万”字派这一辈,仅我们同一个“老太公”下来的即有二三十条汉子。槐哥与我同族同辈,是我的一大群堂兄中年龄最长的一位。他高高的个子,肩宽但背不厚,整个身板像一块门板。国字脸上悬鼻凸颧,轮廓分明。较阔的嘴巴内牙白而个大,排列齐整,说起话来是好听的男中音。
槐哥命较苦,从小就亡了爹,妈也长年病恹恹的。其祖父倒挺鲜健,人高马大腰挺直,却总见他老人家一副笑罗汉像。儿时的我特喜欢他,怪不爱说话的“闷木络子”一块,见了他便情不自禁地喊声“大老爹耶!”大老爹从不拿架子,碰到了总要问我一句:“伢子今儿学了点化子呀?”令我如果没学点东西进去还真怕见他老人家呢。
槐哥是真正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没读什么书就早早地挑起了参加生产劳动的重担。还在我刚上初中时,他已是生产队长了。我们家台子西北角下立着一棵老杨柳,柳树上就吊着铃铛。无论天晴下雨,每日天刚蒙蒙亮他就来到杨柳下,抽过一支“大公鸡”或是“圆球”或是“城乡”后,便挨家挨户去派工。一两百号劳力,一转工派下来,正好是农户吃罢早饭的时候。这时,槐哥把杨柳干上的铃绳解开,拉直,用右手勾住,一扯一松,再一扯一松,“噹啷啷——噹啷啷——”,悠扬的上工铃声便响了起来。那之后,槐哥便随男社员一起去干他作为一级劳动力的一份活了。
我读完初中读高中,高中毕业后又被派出洲去筛石头、喂猪、轧棉花,再回生产大队时,已是民办教师,而槐哥则因被塌方压断腰而改任生产大队会计了,因此我一直没能与槐哥一块儿干过活。听我父亲讲,在北漕以堤填漕“平整土地”时,旁人把土装满一担土筐,见堤被挖后形成的悬崖怪危险的,便往后退开。槐哥见崩坎还需一会儿,怕“上土”和挑土的劳力都退到后边等太窝工了,就大步上前,以扁担两头的勾绳勾稳土筐,然后转过身,背对悬崖弯腰去挑。谁知,不早不迟,悬崖恰在此时“轰——”地一声像排山样地崩了下来!众人本能地直往后退,随即大叫:“啊,槐哥!”胆大些的壮劳力迅即冲向土烟滚滚的塌方,以手快刨,把埋得身首不见的槐哥给弄了出来,急喊“队长,队长!”工地上的“赤脚医生”火速赶来把槐哥给“救”了过来,可他的腰骨断得不可逆转啦。心软的人一提起槐哥就掉泪。
槐哥的事故本可避免,问题就出在“他的思想太好了”。这是社员们的一致看法。并非“憨头”的槐哥,当上会计后仍未吸取“教训”。公社里的有些领导,常来我们大队“要”点花生、西瓜、芝麻、棉油之类,只要槐哥在场,休想拿走。大队每年都有照顾指标,以往队部开会评定时,都是几个干部让与自己亲近的社员平分了事。槐哥上任后,在评定前,布置各小队会计调查清楚,再把最贫困的家庭报到会上,“逼”着干部们“公平”。槐哥的作法无可挑剔,干部们都怕他,再有什么“好事”便避开槐哥。事后槐哥“明了水”去找,领导称“泼出去的水哪还收得回?下不为例啦,啊?”然而之后仍是一“例”又一“例”,槐哥再去找,就有点“死磨鬼缠”的了,只得作罢。
无论哪个生产大队,会计从来都是大队管委会成员。因“做黑耳朵”、“梗头子”,槐哥被排挤出了管委会,而这在全公社是独有的。很多正直而勇敢的社员站出来“打报不平”,大队和公社领导一概不予理睬,时日一长,便没人再提了。
槐哥的“纯会计”(指没有管委成员的‘官帽帽’),干到“大队”改名为“村”时止,是槐哥自己“强行退出”的。原属大队的财产都分给原“社员”,槐哥凭“抓阄”分到了大队代销店。人们都说是“槐哥积了德,该得的”,槐哥不以为然,直惊诧“运气咋恁好”。
槐哥把代销店更名为“平价店”,在他那儿买东西,无论老少亲疏,一律“只巴一点儿运费”。如此一来,周围各村的村民纷纷舍近求远跑到他这儿来购物,害得人家村的店主生意快做不下去了。再后来,“说法”就冒了出来:“槐哥的东西是水货”,“槐哥还想当干部,以便宜货笼络人心”,等等,不一而足。对这些流言蜚语,槐哥“只当是耳边风,刮过去就啥也没啦”,坚持初衷不改,“便民务民,利人利己”。
多年以后的一个夜里,已在卫生院工作的我刚入睡,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叫起来。是面容脱了形的槐哥。原来,他正读初二的小女儿因被老师冤枉“跳了河”,尸首才捞起水!40瓦的灯泡光照下,槐哥面如土色,牙巴骨紧咬着。我悲愤不已,像一头雄狮在八平米的寝室里“咚咚咚”横冲直撞。槐哥使劲按住我的肩,红着双眼叫我“坐下来商量个事”。他叫我“搜集情况,写状子告那个缺德的”。我当然写了,也帮槐哥告了,可因“证据不足”而没能打赢官司。失去小女儿的槐哥一下子老了上十岁,可他还是硬挺着病腰开店,一直开到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上完高中上中专,上完中专走上工作岗位。
人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话真是句谶语。就在槐哥准备“退休”时,他即将提拔为税务局副局长的长子突发心肌梗塞而英年早逝!如迅雷当头一劈,如利刃拦腰一刀,槐哥再也挺不住啦,噩耗传来的当场即訇然倒地不省人事。个把多月后,村人见槐哥打开尘封的店门,又做起了生意,可他的腰更弯、声音更低了。
进入20世纪前夕,刚过花甲之年的槐哥胸腹剧痛难忍,儿女们把他拖到市医院一查,一个个脸都黑了:肝癌晚期!众人强忍着心似被撕裂的疼痛,硬装出笑脸瞒着槐哥:“是肝炎呢。”一直由槐哥帮扶着的大儿媳母子俩悲痛欲绝,满眶的眼泪直往下掉,槐哥什么都明白了。他尽力撑起身子,假装出一副真肝炎的轻松模样,反过来安慰大家:“没事呀,肝炎就是不治,也还有好几年活呐。”
尚未熬到过年,槐哥到底还是走了。我赶至槐哥的灵前,边行三叩九拜大礼,边瞻仰他遗像清癯而又忧伤的面容,心底里满是苦涩。槐哥的身驱走了,但他的为人处世风范却与一股艾蒿样的苦涩浑然一体地存留在了我的胸中。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明 姐
明姐是我的一位远房表姐,属于我妈“后家屋里”飞出的一只金凤凰。
打我记事时起,她就在我们生产大队的各家各户门口和各小队的田垄间“飞”。
她个头不高但长得十分匀称。那时我们还“不醒事”,不知道什么叫“性感”啦、“丰韵”啦,反正就觉得她好看,见了她就不愿意收回目光。她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小而厚的嘴唇,长而黑的双辫。脸上又白又嫩又饱满,左右各一个酒窝,见了我总是一脸的笑容,这时两个酒窝似乎随着她的眼神飞动起来。
她起初是我们羊洲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经常唱“金珠玛咪”、“手拿碟儿”,后来常演“李铁梅”、“小常宝”。她演戏、唱歌都特好看,因为她的声音像银铃,身肢像水蛇,两条黑辫子像她的两个酒窝一样飞动,飞动起来令人心旌摇动、眼花缭乱。当然,最吸引我们男生眼球的,除了这几项,还有更重要的,那是我后来在几个高年级班的“坏男生”点拨下才“发现”的——她胸前的那两个——我一直不愿意说也确实说不出口。她跳起舞来,胸前似乎有两个小兔子在蹦跳,既有劲道又隐藏着克制着,既见不着“兔子”的身影,又分明时时感到“兔子”的欢势与挑衅。哎呀,我不说了,她是待我不错的表姐呢。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当生产大队的所有当权人在一个深夜闭门“研究”推荐谁去上医学院之时,就是她冲破重重阻力提名由我去,闹到最后险些把上级钦定的人选给轰下来。
明姐凭着她的口才和泼辣能干,一步步被提拔到生产大队管委会副主任位子上。她演戏行,“活学活用”行,作报告行,动员女社员去刮胎行,挑担、扬锨、赶牛车等男将活路她也行。两桶水粪一百多斤,压在她貌似嫩弱的肩膀上,她竟然快行如风。她还不需用手掌扁担,两手摆动得洒脱自如,承载的扁担两头一张一弛“咿咿呀呀”给她伴奏助力。最绝的是她居然能像极优秀的个别男将那样边前行边“换肩”,满满的粪水一星半点都不荡出桶沿。扬锨时,她呈弓箭步“钉”于小山样的麦堆旁,手挥木锨平地一铲,冒尖的一锨麦粒随她两臂用力一挥,即呈扇面在她身后铺开,麦芒、草屑、尘埃分别落脚于不同的半弧内,而饱满的麦粒则呈扁圆形堆于最远的半弧上。她一锨比一锨快,一锨比一锨轻松,锨舞臂摆身肢漾,风呼尘飞麦粒扬,“哧哧”“挲挲”声声浪。
赶牛车更是男将的“专利”,再充能的女劳力都不敢沾边。牛车乃那种双牛拉动的“孔明车”,车梁长而下斜,车架高而阔大。赶牛车的车把式平时现不出什么特别,相反倒还有几分多余的样子,只有到得重载“放堤”之际,方显出英雄本色。明姐就会“放堤”。满载着稻草(从小河的对岸农村买来供牛吃)的牛车,赫然如一栋楼房。稻草车被双牛拉至堤顶,牛和轭就卸下来牵到前方的路旁。只见明姐不慌不忙地走近车头,手握车把轻推紧护,“小楼”缓缓前移。不一会儿,“惯性”发作,“小楼”这个庞然大物通过两丈长、向下斜的车梁,驱动膝盖高、柱头粗的车头,由慢到快飞身下堤坡,此时若车把手稍有疏忽,将至人仰“楼”翻,栽入几丈高的堤下。明姐把住车头勿让其越轨或“打撅”,控制住车速勿令其“飞车”或旁倾,人随车势跑,车随人技行,眨眼间,“小楼”滑至二十米开外的路正中,而明姐则渐渐收拢脚步,呼吸平稳,仅有香汗微渗。
明姐以她杰出的工作业绩和俏丽的容貌成了羊洲的名人,也成了众多自认为门当户对男青年追求的目标。明姐力排众议,最后与本大队一位在宜昌当工人的转业军人结为百年同好。明姐也因此选择而付出了代价:那夫君家庭是老上中农出身,成了“老上中农媳妇”的明姐失去了被提拔到公社当国家干部的资格。可明姐不后悔,她一边继续当大队干部,一边生儿育女,相夫教子,赡养老人,伺候责任田,自甘品尝羊角洲普通农妇的苦乐。
如今的明姐过着怎样的生活?我说出来读者们可能难以置信:她和已提前退休的夫君仍生活在羊洲,住着两间偏厦,靠老伴四五百元的退休金维持吃喝穿用和人情“苛拜”。一对“千金”都在城里做小生意,“瓜分”了父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