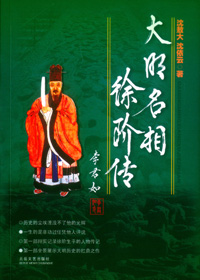大明地师-第21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朱常津作为世子,自然是最晚到、最早走的,众人都站在府署的院子里恭送世子离开。朱常津临上马车之前,拍了拍苏昊的肩膀,说道:“苏学士如此年轻,行事却如此老练,小王佩服。改rì小王再设便宴,请苏学士叙叙。”
“昊定当从命!”苏昊应道。
送走朱常津,下一个就轮到苏昊走了。刘其昌象征xìng地送了他两步,然后就安排自己的师爷狄云师负责把他送出府署大门。到了大门之外,狄云师取出一个锦盒,递到苏昊手中,说道:“苏学士初来乍到,要安一个家,所费不菲。这是知府大人的一点小小心意,以作苏学士的安家之资。”
苏昊以手相推,道:“昊怎敢让府尊大人破费?这万万使不得。”
狄云师道:“苏学士这就见外了,知府大人是欣赏苏学士的才华,这才送上一份薄礼,苏学士如此推托,岂不是不给知府大人面子了?”
“呃那苏昊就恭敬不如从命了。”苏昊只得装出勉为其难的样子,把锦盒收了下来,随手递给了陈观鱼,陈观鱼赶紧把锦盒揣进了怀里。
“那苏某就告辞了,刘知府馈赠之恩,容苏某rì后再报。”苏昊向狄云师拱拱手,带着陈观鱼以及熊民范等人,扬长而去。(未完待续。)
275 谋定后动
“这官场应酬,可真是麻烦啊!”
苏昊回到自己府上,稍稍洗漱了一下,便径直来到李贽的房间,找了张椅子一屁股坐下,开始向李贽抱怨起来。
苏昊与李贽认识不过短短几天时间,但他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和李贽聊天了。李贽不愧是当世大儒,对问题的领悟能力远比其他人要强得多,再加上他当过户部的员外郎、云南姚安知府等,对于官场的事情也是门儿清,苏昊初入官场,非常需要一位这样的顾问。
李贽正戴着老花镜在看书,见苏昊大大咧咧地闯进来,又毫不客气地自己坐下,也不为忤。他放下书,摘下眼镜,看着苏昊问道:“今日刘其昌设宴,用意为何啊?”
“就是一场鸿门宴!”苏昊说道,说完又笑道,“不过我已经把鸿门宴变成诸神之宴了。”
“诸神之宴?”李贽对苏昊嘴里不断冒出的新词表示诧异,堂堂大儒,经常听不懂一个秀才在说什么,这是挺丢人的事情。
“哦,这是佛郎机的一个典故,讲一群神仙在一起欢宴的事情,有个神仙把人家女神的裙子掀起来偷窥,结果被其他神仙发现了然后有个画家就把这事画出来了。”苏昊胡扯道。
“简直是伤风败俗!”李贽斥道,他虽然这样说,但脸上却是笑吟吟的,说明他其实并不是真的介意这个故事。
开过玩笑,苏昊便把刘其昌宴会的前后经过向李贽说了一遍,包括最后狄云师给他送礼的事情也没有隐瞒。那个锦盒拿回来之后,苏昊已经看过了,里面是一叠银票,面值共计500两,考虑到当时官员的薪俸水平,这也算是厚礼了。
“今日之事。其实刘其昌完全没有必要请崇王世子出面的,他这个举动,是在试探你的态度啊。”李贽捻着胡子说道。
苏昊道:“我乍一听说此人是崇王世子,着实吓了一跳。他们难道就不怕我这个都察院的经历把此事奏报到朝廷去?”
李贽笑道:“你奏报上去,又能如何?”
“依律,所有知情的官员都要降职查办,世子会被送凤阳府圈禁,或者废为庶人。”苏昊说道。
李贽道:“这只是律法上的规定,实际上哪有这么严格?藩王和地方官同居一城,低头不见抬头见。大家怎么可能不在一起饮酒作乐?除非藩王豢养私兵,或者与其他藩王暗通款曲,否则宗人府根本不会多管这种闲事。你若是将此事奏报上去,朝廷自然会对崇王和刘其昌进行申斥,但也就是走走过场而已。而你,就会因为这件事而得罪崇王以及刘其昌了。”
“这么说,我没有离开是对的?”苏昊问道。
李贽道:“也对,也不对。”
“此话乍讲?”苏昊道。
李贽道:“说你对,就是因为你也管不了这件事。如果因为惧怕这个规制而离开,就是拂了世子的面子。当今圣上是个很讲亲情的人,他称现在的崇王为王兄,遇上年节也经常有赏赐。你若拂了世子的面子。崇王向圣上歪歪嘴,对你的前程就有影响了。”
“呃我觉得这倒不至于,不过,得罪了崇王。对于我在汝宁办事的确是有不利影响,这是真的。”苏昊争辩道。
李贽没有在意苏昊的反驳,只是继续说道:“至于说你做得不对。那就是你的身份与刘其昌他们不同。他们是地方官,与藩王世子有些交往,别人也好理解。而你身为都察院派出的官员,这算是执法犯法,说法就不一样了。”
“我何尝不知道这一点。”苏昊叫屈道,“可是我又不能走,怎么办呢?”
李贽道:“当下之计,你必须有所表示,但又不可小题大作。所以,你要马上拟一封密函,送交都御史和王次辅,奏明此事,并说明事出有因。他们都是明事理之人,不会将此事公开,日后若有人以此事参你,他们也可出来作证。”
“我明白了,一会我就去写。”苏昊应道。
听李贽这样一说,他算明白了,刘其昌这样做,其实是要把他拴上。他是否把与世子同桌饮酒的事情报往朝廷,都是为难的事情,上报了就会得罪崇王,不报则是给自己留下了一个污点。日后他如果敢对刘其昌不利,刘其昌可以翻出他与朱常津同桌饮酒的事情出来要挟他。
李贽出的这个主意,则是破解刘其昌诡计的方法。他让苏昊以密函的方式上报,内容只限于几个关键人物知道就行了。这样一来,别人就无法说苏昊与朱常津饮酒是私下结交,而朝廷那边又因为消息没有扩散开,而不至于引起什么反应。
“那么,刘其昌给我送银子,又是什么意思呢?”苏昊接着问道。
李贽道:“这不是很明白吗?他就是希望你不要轻举妄动,汝宁府这边有什么好处,不会少了你一份。你在这里呆上几个月,抓几个不起眼的小贼,然后带着银子回京复命,岂不美哉?”
苏昊道:“刘其昌此举,是不是正说明汝宁府有问题呢?而且说明汝宁府的问题是与官方有关的,否则他何必拿钱来封我的口呢?”
李贽道:“这天下之事,哪件事是与官府无关的?刘其昌不愿意你去深揭汝宁府的事情,也不一定就是因为他与这些事情有关,也许只是怕你揭出来之后,他这个知府脸上无光。他宁可稀里糊涂地把事情捂住,也不愿意人有把它揭开,这个道理也站得住脚吧?”
“这倒是。”苏昊摸了摸脑袋,傻笑道。看来李贽的经验的确是比自己丰富,对于官员的心理也把握得更为全面。
“事到如今,你想好怎么做了吗?”李贽问道。
“先摸情况吧。”苏昊道,“有关汝宁府的情况,只是一些言官风闻奏事,连王次辅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如何知道该做什么?我的想法是,先掌握情况,了解汝宁的种种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一般的小问题先不去动,只有大问题才考虑解决。而且,要么就不动手,要动手就一定要打在七寸上,绝不能让对手有还手的机会。”
“谋定而后动,这个想法不错。”李贽道。
苏昊苦笑道:“想法是不错,可是我现在根本就不知道从何下手。来到这汝宁府,我是两眼一摸黑,都不知道该去找什么人来问什么事。在淮安府的时候,知府大人和我是一条心的,什么情况他都会告诉我。现在汝宁知府明显是防备着我,没准还有崇王的势力也在防备我,我周围只有敌人,没有帮手,怎么做下去?”
李贽笑道:“这就更见一个官员的能力了。看看你能不能在短时间内就建立起自己的眼线来。”
苏昊道:“我已经安排陈观鱼去办此事了,他是个老道出身,忽悠人是本行。在淮安的时候,很多情报也是他帮我搜集上来的。”
李贽道:“改之啊,我这两日琢磨了一下你的事情,倒是有一个感觉,也不知道对不对。”
“李先生请讲,你的感觉肯定是对的。”苏昊道。
李贽道:“你说举荐你到汝宁来的,是户部侍郎邬伯行,你与他可有什么过节吗?”
“过节?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怎么可能有过节呢?”苏昊说道。
“是这样?”李贽摇摇头,“那我就有些不明白了。”
也难怪李贽不明白,因为苏昊所说的并非实情。邬伯行与苏昊并非没有过节,而是早已惦记苏昊许久了。苏昊最早离开丰城前往重庆的时候,曾经投宿樵舍驿,在樵舍镇上与当地豪强地主邬员外发生过冲突。而这位邬员外,正是邬伯行的族弟,名叫邬伯贞。
邬伯贞当日在苏昊手里吃了亏,事后找新建县衙和驻军去找苏昊的麻烦,也被苏昊给化解开了,邬伯贞算是结结实实地折了面子。后来,他便将此事告诉了族兄邬伯行,让族兄替自己出气。邬伯行当然不会把一个小小的百户放在心上,以户部左侍郎之尊,专门去寻一个百户的晦气,说出来都丢人,所以他便将此事放下了。
令人想不到的是,苏昊这么一个小百户,居然会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连得到提升,名字开始出现在朝堂之上了。鉴于苏昊身上的“阉党”标签,朝臣们对他本能地就有反感,邬伯行想起族弟跟自己说的事情,这才站出来给苏昊刨了个坑,想让他栽个跟头。
苏昊怎么也想不到樵舍镇上的事情会延续这么长时间,不知道当年的邬员外与邬伯行还有这样一层关系,所以当李贽问他的时候,他才会说自己与邬伯行并无过节。
“我总觉得,荐你到汝宁来的人,居心不良。汝宁的事情,绝不简单,别人并不想看到你无功而返,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是你在汝宁身败名裂。”李贽分析道。他虽然不了解具体的背景,但多年的官场经验还是让他作出了一个正确的预测。
“苏守备、苏守备,你快去看看程姐姐吧!”
苏昊正待与李贽更深入地讨论一番,歌伶风风火火地冲了进来,神色惊惶地对苏昊喊道。
“程仪怎么啦了?”苏昊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她从上午进了房间,到现在都没出来,我叫了她很多回,她也不理。我刚才扒在门缝上偷看,看到她趴在床上大哭呢!”歌伶说道。(未完待续。。)
276 伤心故地
歌伶和程仪两个人被安排住在苏府的后宅,据说是原来那个官员家小姐的闺房。因为房间比较多,所以歌伶和程仪一人住了一间。据歌伶说,程仪自从进了汝宁城之后,就一直脸色阴沉。到了房间之后,更是一下子就关上门,然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吃中午饭的时候,歌伶去喊了程仪一句,结果没有得到回音。歌伶与程仪也才认识几天,不算太熟悉,所以不敢再叫。现在快到吃晚饭时候了,歌伶又去叫程仪,发现程仪的门依然没开。歌伶生怕程仪出什么事,便扒着门缝往里看,结果发现程仪趴在床上,肩膀耸动,明显是在哭泣的样子。
“你怎么还会扒门缝啊?”苏昊贬损道。
歌伶反驳道:“又不是人家想扒门缝,人家就是担心程姐姐出什么事情嘛。人家如果不扒门缝,怎么会知道她哭了一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