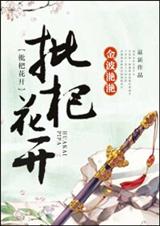���ۿ�-��110����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ǰ�������֪֮���꣬�Ի�̫�����ڳ��䣬����ܹ������ѧ����������ΪȻ�������ҷſ�д�������й�����÷���ֵĹ���ǰ;���ɾ�ȫ����ƪ�������ˡ���
����������÷�����¶����Ƶ����ѣ����������������롣��
������������������䣬�����ߵ�����ǰ��ֽ��ī����������������̫���Ǹ���ʵ�²������۵��ˡ���Ȼ���˹�ѧ����Ŀ�������ľ���ǿ϶�Ҫ�ģ������ɴ�����Ҳ��Ҫ�ġ�
��������������������ΰҵͻȻ����һ���������ߵ���ǰ��ץ����ī��������ӬͷС����ʱ�ӱʼ������ʶ�����
��������������к��棬������Ī�������˸ղź��ң���ʵ��ͶԹ�ѧ�����о����ɣ�������ô��̼�����ܵð�ǧ�ԣ����չ�ͷȥ��ϸϸ������������ʱֻ���������������أ�д���ѧ���Ź�ȻԶʤ�Լ��Ļ���Ʈ�ݣ��������������ֱʡ�����Խ��Խ���ľ���ͬ�����ľ�̣������ۣ�����������룬��ôϸ�����������������dz����������ʡ��
������������������岻��ʱ����ΰҵͻȻͣ���˱ʣ�������ؿ��ź���������Ӳ��ܼ��������ȣ����ѳɴ������̫��Ϊ�ζ���Ҫ�ݼ����ӣ���
������������ʱ�������������ý���ƪ�Ѿ�д�˰˳ɵ��ϼ�֮�����ߣ����ﻹ����˼����ΰҵ�ֱ桰�������������Ⱥ�����⡣��δ���������
һ��һ���Ž��ľ�չ��֦������
������������ƪ���²�����������ȟR��һӦ��ʿ������������һƪ��
����������ʫ����Ȼ�Ա����ԡ�֪�����ƺ���Ҳʱ��ȥ�����������߶���������̫��ת��һЩ��ʵ����Ҫ������ֻ�Ǻ��ϸ���֪���������ϸ����ζ������Ѿ����ݣ���������ʱ�䶼������������������ȟR���ҡ�
�����������Ϊ����֪�����ű���λ��֪����ץס������ʵ����һ��������
����������ʫ����ǰ����һ�ۣ����������£����Ǻ������������ǰ������
���������������Ķ��ӡ�����ȟR��Ȼ����ʮ����ӡ�ӿڵ�������ô��ȥ�����µģ���
�����������������Ƹ������ʫ����æ����һ�䣬�ĵ����ѵ���̫���������ʲô���ڣ���ô���ſ��Dz��ư���
����������ȟR����ͷ����һ�飬������д�õ�ȷ������������ϧ����֮�����ڻ���̤��������Ƴ��������˼�Ц���ǣ���Ȼ��û�п��С�
����������ʫ�治֪����̫�Ӹ�̾ʲô��С���ʵ��������£����˿��в���
����������ȟRҡͷ�����������˸������ˣ���������һʱ���Դ��Ŀ�����ȷ������ʢ�������ѵ�����ѧʵ����������ھ�ʱ��д������ߣ����ڹ���Ҳ�ǿ����ġ���
����������ȟR�������ԡ���ĩ�Ĺ���֮�У������ĵ�ֻ����λ���ٿ�ȫ��һ��ķ����ǣ��Լ�����������¡��һ��ȡ����µĺ��
��������ǰ������������������ʦ������Ϊ̫�ӣ�������̫���������������˿�������Ϊ�Լ����ڵܵ��ǵ�ǽ�ǡ��Dz��ǻ���˦�ڿ������ô��˵������¡����ں����Ȼû����ô����ѧ���������������������ߣ�ʷ�ɷ��¶��������ű�������ִ����ݣ�Ҳ���ǽ�����̳����С������
����������ֻ�ǣ���������̫�����ǵ�ϲ�����롶�������ҡ�������£����Ƴ�֮�ж���֪������������ȟR����Щʧ������������û���������Բ߰ɣ���
����������ȷʵû�С�����ʫ���ͷһ���亹�������������ˣ���˵��������ȥ��һ�顣��Ȼû�У��������뵽ȥ����
���������������Բ�д�õ��ã���ʡ�������ս̲�֮�ж�����¼������ȟR���һ������ֻ����һ��СС��Ա����Ȼָժʥ���ӵIJ��ǣ������ǿ�����û��û״�ˣ���
������������븴����������һ����ϲ������ʱ�ף��������ӵ�ʧ������֮ʱ����������Ŀ�����뵽�Լ����ױ������У�����һ�Ⱦ�д���ˡ����Ӳ��Ϊ���������ģ���Ȼָժ�����۲����������ޡ���Ϊһ��Т�ӣ������������������ǹ����������ܽ��ʲô���⣿ԭ�����ֵľ��˹���Ҳ��˷��ߡ������ȥ�ˣ�����Ծ��Ǹ���Ա��Ϊ�ȸ���ؽؽ���ߣ�����������Ͷҽ��
����������ȟR�������������ִ���������ι��ֶΣ�Ҳ������������Ρ��������ô�����������������֮�����Ǹ����������Լ���ʳ������Ҳ���������ӵĺø��ס����۴��������壬���������ദԻ�ò�������У���ȟR���������ԭ�º��
��������������ƪ�����Ϊ�������������Լ����¶���������������������ȟR��Ը���������뵽Ȩ����������
������������������ƪ����ʵ��̫�������ˡ�
����������ȟR������ƪ�����ֿ���һ�飬��Ȼ���Եõ��������籾Դ�������ȡ������������������ȡ����������������ǡ�������һ�����Ⱥ����Ψ��Ψ����Ǵ�ǵ������ϣ�������ȫû�в���������ǿ���������ڴ�ѧ֮ǰ��־�ľ��µľ�������д�˺������¶��ڵ�����ũѧ�Ĺ��ס����ֱ������ȟR������С�ް�����ȫ����̫�������ź�������ͬһ������ϣ���ֱ��׳�������´��壺��Ȼ���Ļ�̫��ֻ����֪��������������̫�ӵ�������д����������˭֪��δ������һ���������µĴ���ʦ�أ�
�����������ú�������Ұɡ�����ȟR�Ա���һ����ΰҵ������ΰҵ��������**������������Ӽ���Ƶı�ڷ��ӣ���ȟR�������䷳��Ϥ�Ľ�������ȻĿǰ������һ���ȣ�����û������ľ���ɵ�ı�ǩ����������ͽ����ϳ������ˡ����ֻ��������ʢ�����һֱ�������ߺúõ��������ٿ��������IJ�����Щ�������ڹ���������¡�
����������ʫ��ֻ����һ��ͽ���������ӡ�������������ȴ��Щ�ɻ����ķ����г�������������Ի���ѵ��������в������ѵ�����������Ķ�������ʳ��ģ�����֮�����뻯������ݹ�������������Ҳû�����ܹ���������
����������������֮ǰ�������ӵ�������֮һ��
����������ʫ��ͻȻ����Щ�����룬�ٽ���ΰҵ���������衢���������������������߷�������������룬ԭ������Ũ��������Ϣ�����£�����չ¶��һ���ֽ���ˮ���������
����������������ʫ���ʱ�Ϲ��Ͼ�������Ҿ����ʫ��ȴû����Ի�������Ŵ�����������ʵ�����Իǰ�㽻�������ģ��dz��Ժ���֮�֣�������ô�ʻ����Ѿ�����ԭ�����Ǻ���ˡ�
��������������о�ϲ���ӣ�ϲ����Ȼ����ƪ������Ȼ���̫�ӷ��ۣ�������ʫ��Ҳû��Ҫ���������˶����ߣ���������ʫ��һ��С���ˣ���Ҳ����С���֪�����������˶��ߡ�
��������Ϊ�����̫�ӣ�Ԯ�ȸ��ף�����˶�����������������ѧ���иж��á���
����������ʫ���ֿ��˺��һ�ۣ����а����������ʵú�����������˼�����⸱���������������ݳܣ�����̰��֮����
���������������ҽ�ȥ����̫����ǰ�����˶ԡ�����ʫ��ת��������ȥ��
��������������д�ϲ����æ������ʫ��������ȥ�������ǵ�һ�ν���������ֻ���ô˼侰ɫ��Ȼ���б����ֵ���ɫ�������Ժ�������ΪҪ����������һ�����ţ����ݽ�겣��뽭����ɫ�ɲͣ�С����ˮ���ྶͥ��
�����������˻�̫����ʱ���ٵ��鷿�ſڣ�����ͨ�����ܿ�ʹ������ġ�������������������δ���ɣ�����������֮������Ȼ�ǻ�̫�����ɡ�
�����������һ�����أ���ס����Ҫ������ǻ�����࣬һ����Ų�˽�ȥ��
����������ȟR�ں����ŵ�˲��ͽ��������˸����ú������������ԣ������������������յ�ǰ����������̬����������ͽ������Ķ��š�
���������������ȟR����һ������û�뵽��Թ�ѧҲ����˼�ʶ����
����������ѧ��ֻ��һ��dz�������ҵ����¿��ޡ�������������װ��¡�
����������ȟR������һ�����ˣ��ֵ�������Ի������ʱ��Ҫ���£�������������°�æ�ɡ���
���������������һ������������λ���»����ǿ��˿��Ҳ�գ�ֱ���˵�˵������ã������Dz���Ҫ�ȿ�������
������������ѧ��֮��������������ǻ�����ְݵ��ڵأ����Ҹ�����ǰ���������������Գ��������������Ѻ���С���ѧ����������������Ϊ�������������Թ����������¡�
����������ȟR���˻��֣����ͷ��������Ȳ�Ҫ�ޣ����֪���㸸��Ѻ�������
����������گ�����������������
����������ԭ����֪����������ȟRƲ��Ʋ�죺����Ȼ֪����گ����������������飿�ѵ���Ҫ��������ô������ȟR�ò�������İ���֮���ֱ������ˡ�
����������Ϊ���⮡��Ѿ�ȥ�������DZ����һ���飬��������ĵ����������¿�һ�����١���ʱ���ʱ�����Ը�⿴�������������˸����ģ����̫�����������ڡ��з��������������������Գɣ�������������˭֪���ʵ��Dz���Ը�⿴��̫�ӵ���������**��
�����������Һ�����������Ĺ�ϵ˵������������д�˵�������Ǻ������̾ơ������ڽ�殣����˵������ǰ��λ��Ӵ������ġ��������������������ӵ��ʮ��������͢���ȣ��������ʳ�Ͼ����·�һͷ���������������ǣ���͢�������Ķ�������ϵ�Σ��ѵ��Ź�������������û��ǣ�ң�
�����������������ĵ�˵����̫�ӾȺ�������������֮�ⲻ�ھƣ��ں���������Ҳ��
������������ʱ����ȟR�ָ�����Դ���
��������������Т�ӣ��ѵ���Ҫ������Т֮��ô������ȟR��������
������������ŵ�ҭס�ˡ�����δվ�ڻ�̫�ӵĽǶ�˼�����⣬��ʱ��̫��˵���������߶�������·��ͷ��β���Ǵ��ģ�
���������·�һ����ˮ��ͷ���£�����ð��������������Ӱ���ڳ�Ц��λ�Ӳ�ƽ�����˵ĺ�ӣ��·���˵��������������׳գ������㾡�İ׳գ���
�����������ֻ����������ת������ͻȻ����һ�����ȣ��������ѡ�
���������������£��쐪�������
��������ÿ��Ȩ�������ŷ�����һ�����������������Ÿ�����ˡ��еĿ��˿�����ӭ������ͨ������νͨ��֮�ã��еĿ��˿��Կ�����ͨ����Ҳ�еĿ���һ¶�������˾����ó���ȥ�ˡ�
���������ڶ����������ϣ��⮡��ǵ�һ��Ĵ������쐪���ǵڶ���Ĵ�����
��������������̫�ӱ��˶�û�뵽�쐪�������ʱ����֡���δ���������
һ�������Ž��ľ�չ��֦���ģ�
���������쐪�Դ��뿪��Ӫ֮�����û����Ѷ������ȟRԭ��������һ�����������·������ϸ������Ӧ�ò�����ô����ƭ�ӡ��ò����ױ�����ί�����Σ�ȴֻƭ������ӣ�����ð����ٴ�������������ײ˵�Ǯ��
���������쐪������ʱ����ʫ��ͺ���Ѿ��Ӳ��᷿��ȥ���������ߵ���ȟR��ǰ�����ף�������Ѯ�²�������������ˡ���
��������������ˡ�����ȟRЦӦ������������
���������쐪л������һ**���������ӣ����ϼ���һ������������һ·������������ȷ�Ѿ��������ܵļ��ޡ�ֻ������һ��Ӳ��������������˴��ݵ�ģ����
�������������衣����ȟRҡ��е���
���������������̺ܿ�Ϊ�쐪������裬��æ���˳�ȥ��
���������쐪�ܵ��촽��Ƥ��Ҳ���������ȶ��������һ�ڣ����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