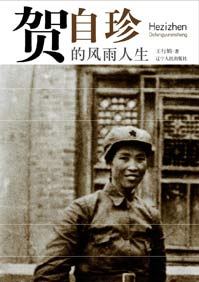风雨独立路-李光耀-第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们斗打架鱼。我们通常在樟宜路两旁的浅沟里抓打架鱼。抓鱼时用的是一种用柳条编制的〃畚箕〃。筑路工人用它来搬运泥土,我们却用它来抓鱼,然后把鱼装进玻璃瓶子里。打架鱼身长25毫米到40毫米,呈深红和紫色,一被激怒就把鳍张开,展现出耀眼的红、橙、蓝三色,异常美丽。我们把两个各装着一条打架鱼的玻璃瓶并排放在一起。两条鱼一触目,搏斗的本能便引发出来了。接着,它们仿佛跳起战舞,拍打着鳍,摆出准备战斗的姿态。这时候,我们便把这一条倒进另一条的玻璃瓶子里,让它们厮杀到其中一条惨败而逃,在惊慌失措中,身上耀眼夺目的色彩顿时消失。打胜的那条鱼的主人,把打败的那条当战利品,其实并没有什么战利品可言,因为它全身伤痕累累,不但鳍被咬断,连身上的肉也一大块一大块被咬掉。经此一败,它的战斗精神很难恢复过来。
我们也斗风筝。我们用两根细长的竹片和特别的风筝纸,自己制作互斗用的风筝。要做一只轻盈而能操纵自如,又均衡得当,不会侧向一边的风筝,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我们把风筝线拉在两根木杆之间,把掺了碎玻璃的浆糊小心地涂在线上。碎玻璃越粗糙,越呈砂砾状,涂在风筝线上时,就越有可能割破自己的手指,也越有可能割断对方的风筝线。斗风筝的目的就在于此。断线的风筝飘落地面时,谁捡到就是谁的。后来,我在剑桥大学念书时,才得知罗马法把这样的风筝称为〃无物主的财物〃。
我们比赛陀螺。陀螺是从店里买来的,最贵的一种用硬柚木制成,经得起对手陀螺的撞击,不会留下任何深凹痕。为了增强陀螺的防卫力量,我们用铜制图钉给陀螺的外表钉一层装甲,使它能挡住对手的攻击。
我们也比赛弹子。在一片坚实的沙地上,我们挖三个排成一线的洞,以便轮流把弹子弹进每一个洞里。比赛的时候,是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把弹子放在适当的位置,然后用右手食指把弹子弹出去。你也可以攻击对手的弹子。如果弹子靠近洞口,你尽可以用自己的弹子大力把它撞开,最好是把它撞破。便宜的弹子通常是用灰泥做的,也有用水泥和石膏混合做成的。这种弹子一经撞击,很容易裂成两半。只有贵的那种,是用坚硬的石块或是真正的大理石做的。
这些游戏,能培养一个人的战斗精神和争取胜利的意志。我不晓得这是否为我日后从事政治活动预先做好准备,但这对于一个人的生存能力倒是一种很好的训练。何况我们并不软弱,也未被宠坏。当年我没有花哨的衣服和鞋子,今天我的孙子却样样有。他们所穿的轻便运动鞋,仿照成人所穿的最新款式,鞋后跟还装上电池和灯泡,能够发出绿色、琥珀色和红色的闪光。我这一代人所穿的是简单的树胶底帆布鞋,每双四五角钱,多数是本地鞋厂制造的。后来,霸打鞋公司生产了一种质地较好的胶鞋,每双一块钱。每年正二月华人农历新年到来之前或是年中,如果幸运的话,父母亲就会到密驼路的鞋店给我买双质量很差的本地制造的皮鞋。鞋内底,甚至那未外露的后跟,都是用硬纸板充数的。如果皮鞋给淋得透湿,就会扁松开来。
当年的世界比较简单。我们不穷,也不富裕。我们没有大量的玩具,更没有电视机,要使自己富于机智,得靠多阅读和发挥想象力。这对我们的求知大有帮助。可是当时没有那么多的图书可供儿童借阅,而且书的价钱又很贵。我通常购买廉价的惊险小说,并追读哈里·沃顿和比利·邦特等一伙男童在格雷菲尔斯的奇遇故事。每个星期五,我总是怀着热切的心情,等待从英国开来的邮船开进丹戎巴葛码头。邮船载来英国的杂志和画报,这些出版物的价钱并不便宜。等我稍微长大时,我便开始利用莱佛士图书馆。每次从那里借来的书,可以阅读两个星期。我以兼收并蓄的态度阅读,但是比较喜欢西部小说,不大喜欢侦探小说。
谈到度假,我们一家人往往到外祖父蔡金鼎坐落在菜市的树胶园木屋去,在那里逗留几天或一个星期。我们乘坐牛车从樟宜路前往树胶园。牛车由两头牛拉着,负责赶车的是外祖母的园丁。牛车的木轮用铁圈箍着,但没有消震器,所以车子在布满辙印的泥路上行走时,总是颠簸得很厉害。50年后,也就是在1977年,当我搭乘协和客机,以三个小时的时间从伦敦飞越大西洋到纽约时,我不知道同机的搭客,有谁体验过乘坐牛车的乐趣。
我们三餐吃得比较简单,也比较健康。当时没有汉堡包和意大利馅饼之类的快餐,也没有不健康食物和特许经营的餐馆,更没有外国的小甜饼,有的是本地烘制的糕点。每年一次,母亲和阿姨们为了准备农历新年除夕和往后两个星期的节庆所需,会一连几天烘制糕饼,然后把一个个玻璃瓶装得满满的。当年也有本地生产的〃和和〃饼干,是仿制英国亨特利和帕尔默饼干厂的产品。至于英国饼干,只有英国老板和本地富有人家才吃得起。我们都吃得饱,从没挨过饿。在我记忆中,当年在家里,在渔村里,或是后来(1930年一1935年之间)在直落古楼英校里,都没见过肥胖的孩子。
母亲是个勇敢的女人
儿时的生活并非完全充满欢乐。父亲偶尔会怀着恶劣的心情回家来,这一般是他在安珀路中华游泳会会所赌21点或其他纸牌输了钱。他要母亲把一些首饰给他,让他典当后再回去碰碰运气。这时候,两人会发生可怕的争吵。父亲有时变得很狂暴,但母亲却是个勇敢的女人,无论如何都要保住父母亲给她当嫁妆的首饰。她性格很坚强,精力充沛,足智多谋,15岁出嫁太早了。在她那个时代,女人的任务就是做个贤妻良母,多生孩子,把孩子抚养成未来的好丈夫、好妻子。如果她晚一代出生,而且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那她轻易就能成为精明能干的商界执行人员。
她穷尽一生的精力抚养孩子,让他们受良好的教育,成为自食其力的专业人士。为了孩子们的远大前途,她毅然挺身跟丈夫对抗。我和弟妹们深知她为我们作出了不少的牺牲。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不能使她失望,所以尽我们所能,做到无愧于她,更不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由于我是家中长子,在我稍大时,她便开始跟我商量家庭的重要决定。所以说早在少年时代,我便成为事实上的家长。这倒教会我平时遇事如何做决定。
第三章 学业竞争的对手
每学年有三个学期,期末都有考试。第一学期数学考试成绩我高居榜首,考到90多分。但英文和经济成绩最好的不是我,我排名第二,落在一个名叫柯玉芝的小姐后面,分数差了一截。这使我十分震惊。我在莱佛士书院见过柯小姐。1939年由于她是这所男校中的唯一女生,校长叫她在年终颁奖日颁奖,我从她手上领过三本奖给我的书
外祖母对我的教育有她自己的一套。1929年我还不满6岁,她坚持要我跟其他渔民的孩子一起,到附近一所学校上课。学校设在一栋木屋里,地面是坚实的泥地,屋顶盖上亚答叶。教室只有一间,里面摆了用木头做桌面的课桌和长凳。还有个房间,那是骨瘦如柴的中年华文老师的家。学生年龄从6岁到10岁,都用同一种简单的课本,一齐跟着老师诵读。按说我们学的是华语,但大概是老师没受过良好的教育,教的福建话比华语多。事实上他根本没教,只叫我们跟着他背词语,也不解释词语的意义,即使解释我们也听不懂。
我向母亲诉苦,她就向外祖母提意见。但母亲当时只是个22岁的少妇,外祖母却是个48岁的经验丰富的家长,养大了两次婚姻所生的九个子女。她决心让我受一些华文教育,于是把我送到离家一英里,在如切台的浚源学校。我每天走路上学。这所学校像样得多,是座两层楼的木结构建筑,大约有10间教室,水泥地面,学生每人一张书桌。每班35到40个学生,6到12岁不等。但是华文课依然叫人头痛。我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巴巴马来语(混杂华语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掺点福建话。学校所教的华文对我来说陌生得很,跟我的生活沾不上边。老师所讲的大部分我听了摸不着头脑。舅父也帮不上忙,因为他们受的不是华文教育。
两三个月后,我再恳求母亲让我转英校,这回外祖母答应了。1930年正月我转到直落古楼英校。学校离我家也是一英里左右,在我家的另一边。我仍然走路上学和回家,不只走的方向不一样,学校也有所不同。这是一所政府小学,只用英语教学。老师说话我听得懂,不费多大气力便有所进步。学生多数是华人,有三几个印度人,一些马来学生是从直落古楼马来学校转来的。
小学生活平淡无奇。我还记得开运动会时,操场上挂满彩旗,放着栏架,用喇叭筒宣布优胜者的名字,然后颁奖。我没得过什么奖。最热门的体育项目是足球,我光着脚漫不经心地参加。马来学生是天生的足球员,踢起球来比华族学生强得多,一般体育项目他们也占上风。华族学生学业成绩却比他们好,特别是数学。
我从一年级读起,跳了一级就读l号,只用六年时间读完本来要七年才读完的小学,5号班结业就参加全岛会考,争取进入政府中学①。1935年临毕业那年我更加用功,考到全校第一名。莱佛士书院录取了我,这所书院只收最优秀的学生。
外祖母患上肺结核
但就在前一年,也就是1934年,外祖母患上肺结核,病得厉害。这件事标志着我的童年生活时期结束了。外祖父外祖母住在我们隔壁,外祖母常常咳个不停,晚上隔着板墙也听得到她的咳嗽声。她越来越瘦,头发也灰白了。诊治外祖母的西医最后绝望了,说她已时日无多。家人讨论该怎么办。家中受过教育的儿子,年龄最大的是庆和舅父,他同意请马来巫医来尽人事。据说马来巫医有本事治疗病入膏盲的病人。
请来的巫医年龄50岁上下,身材瘦削,留着山羊胡子,两眼炯炯有神,个性很强。他给外祖母作了检查后,告诉舅父和舅母们还有办法。他给了些草药和符咒,为外祖母祷告。几天后外祖母似乎好了些,也精神起来,但仍然咳嗽。病情好转后又恶化,反复了四个月,直到同年9月。有一天外祖母情况严重恶化,晚上家里人赶紧把巫医请来。他给外祖母治病的情形我记得很清楚。他让外祖母俯卧着,掀起她的上衣舔她的背部,每舔一下就吐一口血样的东西到盘子里)舅父起了疑心,拿起盘子端详,说那东西像血。巫医舔了10分钟后,外祖母沉沉睡去,也许是昏迷了。
巫医告诉舅父,必须安抚鬼神。第二天晚上须在屋前的花园里演马来戏,还得供奉水果、鲜花和加入姜黄的椰浆饭。供品须放在一艘微型马来船上面,从实乞纳海边送进大海。两天后马来戏上演了,马来演员在哀怨的马来笛声和奇特的鼓声伴奏下跳起祭舞,看得我目瞪口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莫名其妙,心里不禁恐慌起来,甚至产生不样的预感,下意识觉得外祖母可能很快就会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