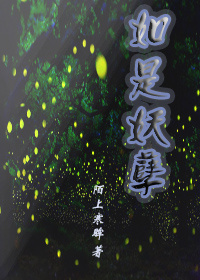一梦如是逝水长-第1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于福自然也不例外,心里很是好奇。
而今日,在他随老爷在府门外接驾时,终于见到了那位传说中的天女。
第一眼看过去,他就忍不住要担心这位天女会被当空酷热的烈阳给烤化了,那样一个冰雪凝成的人儿。
冰雪一样皎洁的身姿,冰雪一样冷凝的气势。
静王妃一身玉色衣裙,头戴蒙纱斗笠,扶着身边宫女的手臂缓缓步下车来。斗笠上长长的面纱垂下,挡住了她的面容,隐约可以看见面纱内两颗寒星闪烁。
只一眼,于福便马上收回了视线。他本就一直低着头,只敢悄悄瞥了一眼马车的方向。这回更是屏气凝神,两眼瞅着脚尖,本就恭恭敬敬的姿势又随之低了几分。
纵使静王妃没有看到他,也没有开口说一句话。不知怎地,在这位王妃娘娘面前,平日威风惯了的总管于福只觉得自己不禁怯弱起来,心里原本存的几分探究和好奇当即就在这股气势下消失的无影无踪,只剩下满心的敬畏和惶恐。
“小姐,今晚是州牧大人为您设的洗尘宴,您为什么那么早就退席啊?啊,莫非是饭菜不合口?”菱儿一边小声问着,一边转身从包裹里拿出几样茶点,绝颜摇首拒绝。
“不用了。”
“小姐,这怎么行,今天席上您分明没吃什么嘛。”
绝颜又摇了摇头,示意菱儿退下。她的确没吃什么,但能得江州的几位重臣列席作陪,这顿洗尘宴也足够她受用了。
她啜了一口杯中的清茶,将今日所见的官员名目在脑中过了一遍。行前她早已对两州的官员做了一番调查,如今一一对照,不仅仅是把名字和面目对上了号,更对其中一些人有了一番初步的评判。
如她所料,江州的两位重臣——盐铁使吕为学和州牧于宣和都对她这位静王妃的驾到颇有顾虑。
盐铁转运使吕为学是五皇子一派,他原本在江州任了多年的州牧,能得寒盟之力更上层楼,心里本是志得意满。偏偏天不作美,弄出这一场大旱,首当其冲的便是朝中代父祭神的五皇子。他既是五皇子的门生,自然也免不了烦恼。
想寒盟年初祭神时何等风光,此时也只能代父受过,原本该由天成帝颁下的罪己诏落在了他的头上,寒盟只得上书圣上,在那道宣告天下的奏折中力陈己过自请降罪,之后更是前往云间寺斋戒祈雨,直到现在也没能回宫。
在这个时候,分属三皇子一派的她前来江州省亲,吕为学的心里难免会对她猜忌防备。这也是人之常情。
另一个接任州牧的于宣和则是举荐出身,虽然也在仕途沉浮几载,却都是些有职无权的闲差,此番他能出任江州州牧,还是多亏了寒照的力量。
按理说他该对同属一派的自己心无芥蒂,但是今日一见,显然不是这么回事。
接驾时也还罢了,到了洗尘宴上,她终于可以肯定自己从到达以后隐隐约约的感觉——这个于宣和对自己很是忌讳。
不过这个忌讳倒不为别的,恐怕最大的原因——只因为她是个女子。
虽然碍于她的王妃身份他不得不彬彬有礼,但是那眼中的不快和疑虑早已泄露了他的情绪,对于她作为护国天女的那番功绩,只怕他是大不以为然的。
绝颜从雍给她的资料里知道这个于宣和生性古板,学识渊博,只可惜他读书虽多,却不识变通,为人虽然刚正有余,但却难免失于迂腐。今日一见,回想起雍话里的意思,她不禁微笑起来。
席间这两人虽然礼数周到,觥筹交错间绝颜却已看出些端倪。她发觉于宣和有话想对钦差大臣奏报,却因为她的在场而隐忍再三,大概是怕她这个明明不在其位的王妃又和之前一样,不守女子的本分来干涉政事。看出他欲言又止的心情,绝颜便借口身体不适早早退席,留下容王世子和于宣和商谈那些他心目中的要事。
这样的人其实最易受人蒙蔽,也许就因为此,左家才会不介意寒照将他安插到江州来吧。这个人,绝不会是左家家主的对手。
真正引起她注意的倒是另一个没有官职在身的白衣——左家专程派来迎接她的“表兄”左少堂。
左家为了迎接她这位静王妃回府省亲,早就做足了准备,但左家的府邸不在城中,距此还有百里之遥,绝颜决定今夜暂歇此处。所以左家才会遣左少堂先行来州牧府迎接。绝颜对左家的人自然有些留意,几番应答下来,左少堂口齿伶俐应对得当,一问一答丝毫不乱,但从他的口中,绝颜只知道了那些早已探知的信息,心里不由得暗暗记下了这个人。
“小姐,厨房有人送饭菜来,说是他们大人的吩咐,见小姐晚宴离席太早,所以派人另作了几样小菜送来。”
菱儿的问话打断了绝颜的沉思。这个于宣和倒也有心,难道说她对此人的猜测有误?绝颜抬起头道:“让她进来吧。”
菱儿应声下去,再进来时身后跟了一个拎着食盒的侍女,绝颜本来并没在意,视线转回到杯中的茶叶上,却感觉到那个拎着食盒的侍女似乎盯着自己看个不停。余光轻扫,这一看她发现侍女的神态的确有些异样,年纪也和寻常派来服侍的侍女不同,竟是一个妇人模样的女子。
“你不是被派来这里的侍女。”绝颜的口吻隐隐生出一分威严。
“是……不是,奴婢的确是这府中的下人。”那妇人连忙弯腰施礼,绝颜看了她一眼,妇人因这一眼定下心来,原本迫切的口吻也缓了下来,开口道:
“奴婢是这府里厨下的帮役,因为宵夜已经做好了,一时没找到人手,奴婢就自己送过来了。”
绝颜微微一笑:“如此有劳了。菱儿。”她看向一旁的菱儿,后者会意的拿出打赏用的钱袋,妇人慌忙摆手:“这怎么使得。本就是奴婢分内的事情。”说话间也一直偷眼瞧着绝颜。
绝颜怎会觉察不到,她直觉这个妇人今夜来此不只为了送菜那么简单,唇角一勾,笑得愈发和蔼可亲,正要开口询问,妇人却突然面色一变,盯着绝颜的面容,眼里竟流下泪来:
“小姐,和小姐真像啊。简直是一模一样——”
绝颜心中一凛,一个几乎不可能的念头在心中浮现,她立刻扬手止住想要开口的菱儿,试探性的问道:“你说的小姐是谁?”
妇人闻言更加抽抽噎噎起来,一面拉起袖子抹眼泪,一面点头道:“我家小姐,正是左家的大小姐。”她抬头看着绝颜,像是从她的脸上看见了另一个人,“也就是王妃娘娘您的亲身母亲啊。”
绝颜不禁精神一振,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通过催眠仰溪她也只得知了柳家夫妇婚后的情况,至于左氏之前的情况,连仰溪都不清楚,更不要说自己了。所以她此次回江州,其中也有查访故人之意,而今来了一个左氏生前的丫鬟,怎不让她欣喜。
“你说的都是真的?”绝颜心思连转,“可是你怎么会在这里的?你不是该在左家么?”她猜测这人是左氏出闺前的侍女,并未成为陪嫁中人。
妇人神色更为惨淡:“王妃娘娘有所不知。当年小姐不听老爷吩咐,死也不肯进宫,老爷一怒之下,就把小姐锁在了房里。小姐要奴婢助她逃走,奴婢虽然心里害怕老爷,但是小姐一向待奴婢情如姐妹,奴婢实在不忍见小姐日日憔悴下去,便横下心帮小姐逃出了左府。逃出府后,奴婢就一直跟着小姐,后来听说老爷让二小姐进了宫,小姐才回了府里。等到芜王公子再去提亲时,老爷也只能允了。等到小姐嫁去芜州时,奴婢本也跟过去的。直到后来,小姐她送了奴婢一笔资财,让奴婢自己择个人家,从此也好自在度日。”妇人停了下来,一脸怀念,“小姐她,一向都是菩萨心肠。”
“那后来呢?”绝颜一一记下,随即问道,“对了,我娘亲她,”她为“娘亲”这个词在心里顿了一下,“和姨母两人要好么?”
左婕妤母子的行径始终是她心头的一根刺,背叛的原因她已不在意,但是左婕妤熟知柳家人的下落却令她心惊,而且她相信把消息透露给袁智的也正是他们母子。袁智的真正身份连寒诀都不知晓,他们究竟是从何而知,又知道多少呢?
“是奴婢自己命薄,夫家早逝,剩下奴婢一人孤苦伶仃,没奈何,只能重又出来给人帮帮工。”妇人的嘴角扯出一丝苦笑。“小姐她和二小姐俱是一母同胞,关系自然是极好的。”
“那你这次进州牧府来帮工,是特地来找我的么?”绝颜可不相信她是偶然在此和自己相遇。
“是。奴婢听说小小姐如今也长成了大人,还做了王妃娘娘,所以无论如何都想亲眼见见小小姐您。”
妇人的眼中一片诚挚,转而又暗淡下来,“还有,奴婢听说小小姐要回左家省亲,心里不知怎地,就是有些……有些……担心。”大概是终于说出了这句话,她长长舒了口气。
绝颜脸上显然因这句话而有些惊诧:“担心?”
妇人一脸后悔和惶急:“许是奴婢多虑了,奴婢也说不上来。就是觉得有些……担心。娘娘不必放在心上,这都是奴婢自己胡思乱想来着。”
绝颜笑着安抚她道:“不要紧。我明白你的心意。你刚才说,我娘她和进了宫的二姨感情甚好是吗?”她像是在回忆什么,脸上终究却只现出一脸惆怅之情,“可惜我那时还小,不记得娘亲是不是常常提起宫里的二姨,也不记得有没有再见过二姨她了。”
“是啊,二小姐进宫的时候,小姐她还没出嫁呢。”妇人见到绝颜这副神情,渐渐放松下来,话里不禁多了几分慈爱和感叹,“小小姐多半是不记得。小姐和二小姐自小姐妹情深,无话不谈,后来二小姐虽然进了宫,可也一直没断过书信。”妇人的神情陷入了回忆,“小姐总担心二小姐在宫里凄凉寂寞,又怕她受人欺负,所以信写得可勤了。”
姐妹情深,无话不谈。
绝颜的心紧紧萦绕在这八个字上,虽然仍在倾听,思绪却有些飘离。无话不谈?怎样的无话不谈?会不会把自己所嫁之人的身世也在闺阁女儿的半夜谈心时透露给了妹妹知道?
绝颜的眼前仿佛看见一个芳心初动、陷入情网的少女,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对着最信任最亲密的妹妹谈论着自己心中的情郎,言语未尽,已是满面娇羞。
如果她一直和左婕妤这个妹妹书信往来的话——
绝颜的心狠狠坠了下去,那么左婕妤也就可能知道柳家曾经的仇人是谁,其中自然少不了搜捕过柳家的袁智。于是她便想出向袁智告密的主意,尽管她知道的最多只和柳保宗一样,也不清楚袁智的真实身份,但是已经足够了。
她知道袁智曾经搜捕过沦为钦犯的柳家,而柳家的后人还活着,活在一个她知道的地方。
这就足够了。
足够让她那位在朝为官的哥哥奏上一本,重新使天成帝的视线投向柳家,命人追杀柳氏的后人。而她,则是悄悄在后面为袁智指出明路。这一点,应该连天成帝和袁智自己都不知道。
心思百转千回,脸上却仍在笑着,看在那妇人眼里,更加的感慨,言辞更是滔滔不绝起来。绝颜依旧侧耳倾听,眼中的笑意几乎要满得溢出来,只不过面前人看不出这笑容在她心里早成了冬日屋檐一串串的水滴,还未溢出就凝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