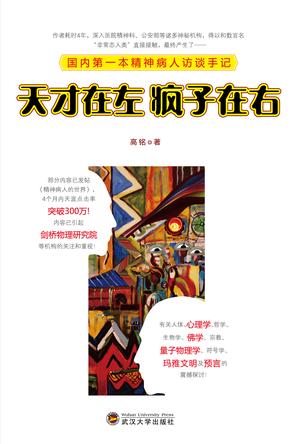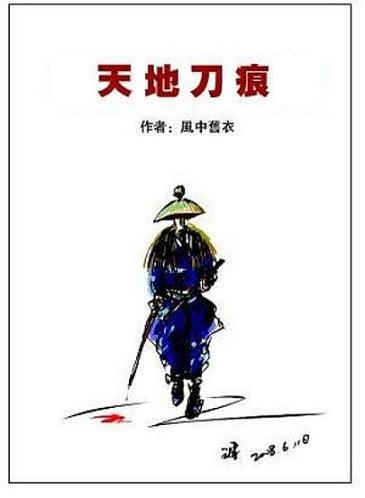御前疯子-第4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夏笙寒故作委屈地将她松开,问:“你怎么知道我是装的?”
傅茗渊理了理袖子,学着他的语调:“我还不了解你?”
他微微一愣,苍白的面容上展露出一丝微笑。
对,正是因为我知道你了解我啊。
回京之后,景帝一看到夏笙寒便扑了过来,上下左右细细端详一番,看看是不是哪里瘦了,罢了才想起他还有个跟着军队走了数月的老师。
豫王等一干同党,以及那个曾经想要掳走傅茗渊的细作都被关进了大牢,这些人也知死到临头,索性什么也不说,倒是豫王开了个条件:他可以供出在京城的同伙,条件便是放他一条生路。
当初他谋反时恰是韵太妃死后不过数日,若说京中没有眼线根本不可能,但既然他能如此有恃无恐,想必不是随口胡扯的。
而放了他,是更加不可能的事。
景帝觉得他实在没救,况且又有关东和通州一带的事宜要尽快处理,遂将审理豫王一事押后几天,剩下的人则是全部丢给了大理寺审问。
毕竟到了深秋,天牢之中凉风飕飕,豫王独处一间,倒是过得悠闲,仿佛根本不在意自己即将要死之事。
黑暗之中传来了一阵脚步声,大约是两人,随后狱卒便侯在了外边。豫王余光瞥去,试探地唤道:“又是那个来跟本王磨牙的陆大人?”
对方没有回答,越走越近。
“这般沉稳,是寺卿大人亲自来了?”豫王幽幽一笑,一抬眼果然见得两人正在外边,目光却落定在其中一人的身上,“都过了这么多天才来找我?”
那男子立于阴影之中,只有稀疏的阳光照耀在他的深衣上,看不清面容,冷笑道:“谋反失败,你居然还这么悠闲地坐在这里?”
豫王面不改色地凝视着他:“你会来救我,就代表我们是一丘之貉。”
“一丘之貉?你连陈王这么没心眼的人都不懂得利用,谁会与你为伍?”男子的目光中闪烁着锋芒,笑容肆意,“本王啊改主意了。”
豫王闻言,神色中难得露出了恐慌,却尽量保持镇定:“这里可是大理寺,你想作甚”
他话音未落,脖颈骤然被人一掌击倒,接着又往他嘴里灌了什么东西。瞳孔渐渐涣散,他急忙想喊出什么,可眼神却愈发呆滞,直至侧着脑袋倒下去。
那男子定定地望了他一会儿,唇角一弯,抬手从袖子里取出什么东西,往地下一轻轻一抛。
借着微弱的日光,依稀可见那是一块令牌,其上刻着一个“湘”字。
作者有话要说:这章码的时候有点快我困了_(:3」乙_有错别字回来改_(:3」乙…
第51章 「太平」
算一算不过只是数个月,可感觉上却仿佛过了好几年。傅茗渊回到博书斋后,天天盼着她回来的安珞差点没忍住哭出来,直以为她死在战场上了;其余的小书童虽与她感情一般,但到底担心自家主人翘辫子之后,再也无处去,此刻亦是很喜悦。
她差人将阿尘接了回来,对方一见她先是抱了她一下,随即气冲冲道:“谁让你把我送去乔府的?!”
“额我若是不在,难免有人对你下手。”傅茗渊摊开手道,“再者,我又不知道你老家在岭南的哪里。”
瞧她神色疲惫不堪,阿尘叹了口气,无奈地抽了下嘴角:“装得还真像,你要是不说那句‘人贩子’,我真当你疯了。”
傅茗渊冲她笑笑。
豫王谋逆一事虎头蛇尾,显然是在京中也有什么计策,然而到现在也没有任何风声。左军之中但凡带头叛乱的都死的一干二净,自尽比剃毛还利索,景帝无奈之下只好将关东军编入这支队伍,又另派人马去了关东一带。
早朝回来后,他托着腮帮子思索道:“齐王那个胆小鬼是受了唆使,陈王也是听命于豫王,查不出源头来。汤丞相今早提议削藩,以防此事再度发生,百官看法不一。”
他说这话便是想听听傅茗渊的意见;她想了想,摇头道:“削藩不失为良策,但而今几个有威胁的藩王都尚无子嗣,贸然夺了人家的兵实在不妥,而且连在豫王谋反之后,难免会有人说陛下没能力。毕竟先帝当年”
她忽地意识到什么,略略尴尬地闭上了嘴。景帝明了她的意思,垂头道:“朕并不想走父皇的老路。”
在老首辅身边跟久了,允帝的事她也了解许多,比如当年是如何舌战群雄,又是如何令一干藩王对他闻风丧胆她知晓这大延王朝的昌盛允帝功不可没,但具体是个怎样的人,景帝却不怎么愿意提起。
傅茗渊终究有些在意,前去慧王府时恰好看见严吉急匆匆地出门,遂狐疑地进屋,不见夏笙寒如往常一样在亭子里干坐着,而是在书房里画画。
她不得不承认他的画工很是出色,每一幅都是惟妙惟肖,却只画景不画人。夏笙寒并不讶于她的到来,与她笑道:“这么快就想我啦?”
“”傅茗渊白他一眼,目光却直直落定在他苍白的脸上,“我一直想问,你头上的疤可是与先帝有关?”
夏笙寒望了望她,继续执笔作画,笑得轻描淡写:“先帝才不会对我动手,只是默许他身边的宫人罢了。当年唐王身边走漏了些消息,先帝便将韵太妃扣在宫中,唐王来讨人未果,回藩地的路上就遇刺了,就连王兄也曾遇到过不少这样的事”他像是想起什么,顿了顿,未再开口。
头一次从他口中听到真相,傅茗渊抿抿唇道:“先帝对你们都是这样的么?”
“要不然豫王怎会如此恨他?”他耸耸肩道,“不过无论如何,他是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有这一点便足够了。先帝生前谁也不相信,别说是大臣,连皇后他都处处防着,唯一相信的便是他自己。或许活得太累便是他英年早逝的原因罢。”
难怪,景帝会露出那样的表情
的确,身在帝位一切都需小心谨慎,对凡事也该留个心眼,但若事事针对事事怀疑,到最后身边真正愿意舍命效忠的,反而不剩多少。
“其实在通州传出你谋反的消息之后,我犹豫了一瞬。”她目光明净,坦白道,“我想知道,你一直以来追求的是什么。”
夏笙寒的画笔悬在半空,抬头看了看她:“宝宝。”
“”她额上青筋一暴,“不许发疯。”
“噢”他颇为失望道,“那我想要天下太平。”
他一边作画一边回答,说得云淡风轻,却叫傅茗渊一时怔了怔。她有时会觉得看不透他,而有时也会想:也许他要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一个国泰民安的王朝究竟是什么样的,又需要牺牲掉多少人才能换来这份安宁,对他们而言都是个未知数。入朝为官一晃已近三年,有时连她自己都忘了最初的想法是什么,而今听到这个回答,竟是这般简简单单。
天下太平。
她渐渐出了神,恍然察觉到夏笙寒不知何时走到她面前,嘴角扬起了一个大大的弧度:“我回答你的问题了,该你回答我的了。”
他每每露出这般笑意时,总是会让傅茗渊觉得毛骨悚然,遂警惕道:“什么问题?”
“什么时候送我宝宝?”
“你怎么还在纠结这个!”她扶额叹气。
夏笙寒甚是委屈道:“我连名字都想好了。”
傅茗渊感到不可思议,好奇又好笑,但看他这般认真的样子,遂含糊问道:“叫什么?”
他没有立即回答,转身从案上取出一幅卷轴,徐徐在她眼前展开,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看得她头皮发麻,眼花缭乱,谁知他手里竟还握着半卷没展开,依然全是字,开头一律为“夏”,有两字有三字,一排一排写得工工整整。
“选一个吧。”
“你赶紧吃药去吧你!”她吓得落荒而逃。
不行不行,这个疯子再不治真的没有救了。
夏笙寒似乎不理解为何会把她吓跑,将卷轴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收到一半灵光一闪,提笔在卷轴上又添了个名字。
他满意地存放好后,严吉敲门进屋,神色却是十分严肃,低声问:“王爷,方才傅大人来过了?”
一见到他,夏笙寒目光一凛,不复方才的笑意:“又拿到什么可笑的东西了?”
严吉沉着面色,迟疑片刻,将手里的一张字条递了过去:“老奴从外面回来时,有人交到我手上的。这毒连苗疆那边的人也丝毫没有办法,倘若不应他的话”他没有说下去,苦着脸道,“老奴知道老奴自私,但你当真不告诉傅大人?”
“告诉她作甚?”夏笙寒满不在乎地笑笑,接过字条看了一眼,俊秀的面庞忽而一冷,指尖一拂,将字条撕成了碎片,不屑地哼了一声。
这可真是世上最可笑的威胁。
次日清早,傅茗渊听说朝中出了事,遂急匆匆地要赶去,哪知刚一出门便与陆子期撞了个正着。
从国子监辗转到吏部,再从吏部辗转到大理寺,这个热血青年比原先靠谱了许多。此行急忙来找她,定是有要事,却不想这“要事”是如此出乎意料。
豫王在牢中遇害,而那个在营地来掳走她的刺客也不明原因地死了。
傅茗渊大惊失色,沉默许久才平定心绪,抬头道:“你来找我,不止是为了这个吧?”
陆子期点了点头,环视四周一圈,小声道:“这件事乃是今早被我发现的,从寺卿大人的名册上看来,牢中无任何人来访。所以”
“你怀疑是大理寺卿做的手脚?”
“他是最有可能的人。”他顿了顿,略略迟疑道,“还有就是在豫王的遗体边上,发现了湘王府的信物。”
“!”
她再次惊愕,闻言蹙眉,却是思索不出这其中的联系。在他们回京之后,湘王也很快从藩地归来。关于丘城遇袭一事,景帝曾派人去慰问过,而对方只是轻描淡写地回应。
谁人都知道这大理寺卿是被湘王提拔上来的,陆子期能注意到这其中的不对劲,想必朝中也有其他人察觉出了,那么抓捕寺卿与湘王便成了迟早的事。
傅茗渊赶到御书房时,百官正在外面商讨对策,道是寺卿于中一早前来负荆请罪,恳请景帝莫要责罚大理寺的其余官员,豫王之死的责任由他一人承担。
此言一出,众官哗然,所有人都毫无意外地联想到了湘王,却又皆是有所迟疑。
一人扬眉示意:湘王往朝上一站,指不定就有人跪下叫“陛下”了,何必做这么麻烦的事啊!
另一人挤了挤眼:如果说是陷害,那这寺卿大人要如何解释?他可是早就跟在湘王后面了啊!
又一人抖了抖裤腿:湘王是何人,怎么可能留下这么蠢的线索?
他们的肢体语言越来越丰富,聊八卦聊久了全都心灵相通了起来,又不敢当着景帝的面讲。尽管是个人都知道这其中有猫腻,但眼下证据确凿,须得与湘王对峙。
景帝与傅茗渊对视了一眼,一想到要去捉拿湘王就腿软,百官更是躲得老远,年轻的说老了,年老的说快死了,竟是一个都不愿去。
最后,这个担子落在了刚刚上任不久的状元李诉身上。
在吏部呆了将近一年,李诉头一回领到这么大的任务,兴冲冲地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