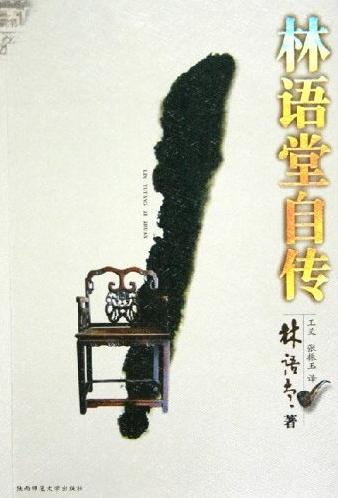林语堂-苏东坡传-第2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曾赴宴席侑酒。她常和书家兼品茶名家蔡襄比赛喝茶,都曾获胜。苏东坡经过杭州,太守陈襄邀宴,周韶也在座。宴席上,周韶请求脱除妓籍,客人命她写一首绝句。周韶提笔立成,自比为笼中白鹦鹉“雪衣女”。诗曰: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席上其他诗人也写诗为念。苏东坡补言当时周韶正在居丧,着白衣。众人都受感动,周韶遂脱籍。
过这样的官场生活,自然须要做妻子的信任和了解。要做一个好妻子,主要是如何物色一个好丈夫;从反面说,要做一个好丈夫,主要就是如何物色一个好妻子。
有一个好妻子,则男儿不违法犯纪,不遭横祸。苏东坡的妻子知道她嫁的是一个人人喜爱的诗人,也是个天才,她当然不会和丈夫去比文才和文学的荣誉。她早已打定主意,她所要做的就是做个妻子,一个贤妻。她现在已生了两个婴儿。做一个判官的妻子,她有一个舒服的家,享有社交上的地位。她还依然年轻,甘四岁左右。
丈夫才气焕发,胸襟开阔,喜爱追欢寻乐,还有——是个多么渊博的学者呀!但是佩服丈夫的人太多了——有男的,也有女的!难道她没看见公馆南边那些女人吗?
还有在望湖楼和有美堂那些宴会里的。新到的太守陈襄,是个饱学之士,在他们到差之后一年来的,这位太守把对外界的应酬做得很周到,官妓自然全听他们招唤。
另外还有周那、鲁少卿等人,并不是丈夫的真正好朋友。歌妓们都有才艺,会唱歌曲、会弹奏乐器,她们之中还有会作诗填词的。她自己不会做诗填词,但是她懂那些文句。那些诗词她也觉得熟悉,因为她常听见丈夫低声吟唱。她若出口吟唱,那可羞死人!高贵的夫人怎么可以唱词呢?她丈夫去访那些赤足的高僧——惠勤、辩才,还有那些年高有德的长胡子的老翁,她反倒觉得心里自在点儿。
苏夫人用了好几年的工夫才摸清楚丈夫性格,那是多方面的个性,既是乐天达观随遇而安,可是有时又激烈而固执。到现在她倒了解一方面,就是他不会受别人影响,而且你无法和他辩论。另一方面,倘若他给歌妓题诗,那又何妨?那是当然的。他对那些职业性的女艺人,决不迷恋。而且她还听说他曾把一个歌妓琴操劝服去遁入空门修道为尼呢!琴操真有很高的宿慧,诗与佛学一触即通。苏东坡不应当把白居易写歌妓末路生活的诗句念给琴操听。苏夫人聪明解事,办事圆通,她不会把丈夫反倒推入歌妓的怀抱。而且,她知道丈夫这个男人是妻子管不住的,连皇帝也没用。她做得最漂亮——信任他。
她是进士的女儿,能读能写,但是并非一个“士”。她只为丈夫做眉州家乡菜,做丈夫爱喝的姜茶。他生病时,多么需人照顾啊!若丈夫是诗人,因而有些异乎寻常之处,那是应当的。丈夫知道有书要读,上千上百卷的书,做妻子的也知道要管家事,要抚养孩子,要过日子。因此,她愿忍受丈夫睡觉时有名的雷鸣般的鼾声——尤其是酩酊大醉之时。
这些先不说,与这样人同床共寝,真得承认这个床头人是够怪的。妻子在床上躺着难以入睡,听着丈夫打鼾,却不能惊醒他。在他入睡之前,他要不厌其烦把被褥塞好。他要翻来覆去把躯干四肢安放妥帖,手拍被褥,直到把自己摆放适当又自在又舒服为止。他身上倘若有地方发僵发痒,他要轻轻揉机,轻轻揉。这些完毕,这才算一切大定。他要睡了,闭上眼,细听气血的运行,要确待呼吸得缓慢均匀而后可。他自言自语道:“现在我已安卧。身上即使尚有发痒之处,我不再丝毫移动,而要以毅力精神克服之。这样,再过片刻,我浑身轻松安和直到足尖。睡意已至,吾入睡矣。”
苏东坡承认,这与宗教有关系。灵魂之自在确与身体之自在有关联。人若不能控制身心,便不能控制灵魂。这以后是苏东坡一件重要的事。苏东坡在把自己睡眠的方法向两个弟子讲解之后,他又说:“二君试用吾法,必识其趣,慎无以语人也。
天下之理,戒然后能慧,盖慧性圆通,必从戒谨中入。未有天君不严而能圆通觉悟也。”
后来,苏夫人还发现夜里和黎明时,丈夫习惯上要有更多的改变。用细梳子拢头发和沐浴是这位诗人生活中的重要大事。因为在那一个时代,若有人细心观察人的身体及其内部的功能,并注意草药及茶叶的研究,再无别人,只有苏东坡。
苏夫人头脑清爽而稳定,而诗人往往不能。丈夫往往急躁,灰心丧气,喜怒无常。苏夫人有一次在一个春天的月夜,做了一个比照说:“我对春天的月亮更为喜爱。秋月使人悲,春月使人喜。”数年后,在密州,他们正过苦日子,苏东坡对新所得税至为愤怒,孩子揪着他的衣裳对他晓晓不休。
他说:“孩子们真傻!”
苏夫人说:“你才傻。你一天闷坐,有什么好处?好了。我给弄点儿酒喝吧。”
在一首诗里记这件事时,苏东坡觉得自己很丢脸,这时妻子洗杯子给他热酒。
这当然使他很欢喜,他说他妻子比诗人刘伶的妻子贤德。因为刘伶的妻子不许丈夫喝酒。
但是在苏东坡的心灵深处有一件事,人大都不知道,苏东坡的妻子一定知道,那就是他初恋的堂妹,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她的名字。因为苏东坡是无事不肯对人言的人,他一定告诉过他妻子。他对表妹的深情后来隐藏在两首诗里,读苏诗的人都略而未察。
苏东坡并没常年住在杭州,而是常到杭州的西南、西部、北部去。由神宗熙宁六年十一月到次年三月,他到过附近的上海、嘉兴、常州、靖江,这些地方在宋朝时都属于浙江剩他的堂妹现在嫁给了柳仲远,住在靖江附近。他在堂妹家住了三个月,他虽然写了大量的旅游诗记述这次旅行,并且常和堂妹的公公柳懂一同写作游历,他却一次也没提到堂妹丈夫的名字,也没写过一首诗给他。他写过一首诗记堂妹家的一次家宴,还写过两首诗论书法,那是堂妹的两个儿子请他题字时写的。
苏东坡对柳道这个诗人和书法家的成就颇为器重,对堂妹的孩子也很顾念。但是到堂妹家的盘桓却对堂妹的丈夫一字不提,实在难以理解。
此行写的两首诗,暗含有对堂妹的特别关系。一首诗是他写给刁景纯的,主题是回忆皇宫内的一株花。其中有下面的句子:厌从年少追新赏,闲对宫花识旧香。
那时他并没坐对宫花,因为他并不是正置身皇宫之内。他说“厌从年少”的伴侣时,他显然是描写自己;而“花”照例是女人的象征,“旧香”可能指一段的旧情。
这个暗指在另一首诗里更为清楚。那是给杭州太守陈裹的。题目中说春归太迟,误了牡丹的开花时节(诗前叙言颇长)诚然不虚,他回到杭州时,牡丹的花季已过,可是暗示少女已嫁,今已生儿育女,则极明显,并且在咏牡丹的一首诗里也滑有理由用两次求爱已迟那么明显的典故。为明白这两个典故,要说明一下。在唐朝有一个少女杜秋娘,在十五岁时写了下面一首诗: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空折枝”便表示误了求爱时期。唐朝杜牧与杜秋娘同时,也写出了下面的一首诗: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时,狂风落尽深红蕊,绿叶成阴子满枝。自从杜牧写了这首诗,“绿叶成阴子满枝”就用来表示少女成了母亲之意,更因为中文的“子”既代表“果子”,又代表“儿子”。
在苏东坡那首诗里,思想似乎并不连贯,并且特别用“金缕”、“成阴结子”、“空折枝”这些字眼儿。他的诗如下:羞归应为负花期,已是成阴结子时,与物寡情怜我老,遣春无恨赖君诗,玉台不见朝酣酒,金缕犹歌空折枝,从此年年定相见,欲师老圃问樊迟。这首诗给陈襄,或是赋牡丹,都不相宜,仔细一看,连与诗题都漠不相干,“成阴结子”与牡丹更无关系。他也没有理由要太守陈襄“怜我老”。“从此年年定相见”是分别时的语句,并且用于归见同僚,而且苏东坡心中绝无心在陈太守邻近安居务农的打算。倘若说这首诗确是写给陈太守的,用绿叶成阴求爱已迟,必然是够古怪的。诚然,在唐朝这类诗里,中间两联里字的词性要同类相对,中间两联有时只做点缀之用,前后两联才真用以表达作者的情思;不过唐律之上品仍然全首有整体性的。苏东坡写的诗里用几行空洞无物的句子充数儿的坏诗,可少见得很。若从另一角度观之,看做是他写给堂妹的,则这首诗在主题和思想上便很完整了。第一行说此次归来实感羞愧,因自己误了花时,也可以说误了堂妹的青春时期。第二行分明说她已儿女成行。第三行求她同情,又表示自己的孤独寂寞。第四行说因有她相伴,今春过得快活。第五和第六句分明他对求婚已迟感到歉咎。第四联自不难解。苏东坡这时写了一首诗,表示愿在常州安居下来,这样离堂妹家不远。他后来的确按照计划在常州买了房子田地,他后来就在常州去世的。
我知道敬爱苏东坡的人会不同意我的说法,怪我说苏东坡暗恋堂妹。这是否在苏东坡的品格上算个暇疵,看法容或因人而异。这事如果属实,并且传到人耳朵里,那些道学家必会谴责苏东坡。不过自古至今,堂兄妹、表兄妹却不断相恋。但苏东坡不能违背礼俗娶自己的堂妹,因为她也姓苏。
苏东坡游靖江时,他在焦山一个寺院的墙上题了一首诗,西方的读者对此最感兴趣。苏东坡料必知道唐朝段成式在《酉阳杂咀》中所写“叶限”那篇短故事。述说小姑娘叶限受继母和后妹折磨,丢了鞋,后来嫁给国王的经过。但是据我所知,苏东坡是第一个记载老翁睡眠时怎么安排自己须子的人。他用一首简易的韵语说一个有长须的人,从来没想过在床上怎么安排自己的胡子。一天,有人问他睡觉时胡子放在什么地方。那天夜里他开始惦记他的胡子,他先把胡子放在被子外面,后来又放在被子里面,又放回外面,折腾了一夜没合眼。第二天早晨,他一直感觉坐立不安,心想最好的办法是把胡子剪掉。由那首诗看来,那只是通俗故事,不是苏东坡创作的。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一下《盲者不识日》的故事,这倒是苏东坡第一个想到的,这篇寓言写在密州。爱因斯坦似乎在什么地方引用过这篇故事,来说明一般人对相对论的看法。
日喻
生而眇者不识日,问之有目者。或告之日,“日之状如铜盘”。扣盘而得其声,他日闻钟以为日也。或告之日“光如烛”。扪烛而得其形,他日揣备以为日也。而眇者不知其异,以其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未达也,无以异于吵。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自盘而之钟,自烛而之将。转而相之,岂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见而名之,或莫之见而意之,皆求道之过也。
说也奇怪,这篇寓言是苏东坡在殿试时写的。他用以讽刺当时学者盲从王安石的《三经新论》。
苏东坡这个人物个性太复杂,方面太多,了解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