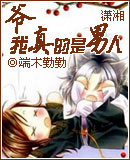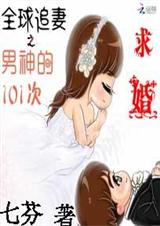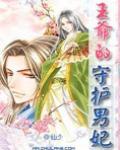���Ĵ���-��1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ڶ��¡�������������������
������ͷ�涨����ѧ��ҵ�������µ�λ����Ҫ�����ĵط����������£�������������������������ΰ��Ҳ�����⡣����һ����䵽����ʡ�������������֮��һ�������˾�ס�ġ��а�¶���ɽկ�ӡ�����������
��������ǰһ������磬�����糤�Դ��˵����֧����������������顢��ΰ����λͬ־ȥ��¶�������ʱ�������¡���Ұ��������Ĺ�����̯һ�¡�С�º�С��Ҫ����˼�������������ﲻҪ�����⡣ס�����ش���ļ��ͬ�ԣ�ͬס��ͬ�Ͷ�������Ҫ���պ�����ѵõĻ��ᣬ��������˽��ϰ��յ�Ը��������״�����б�Ҫʱ������д������֯��ӳ�ϰ��յ����Ѻ�Ҫ���ر���Ҫǿ�����ǣ�������Ҫ���������һ��Ҫƽ����ȥ��ƽ���ط��أ����ﻹ�������µ������ǡ�ɽ·�����ߣ����������賿�͵ó������������Ա�����ǵ�ɽ���µĴ��������Ҹ���С¿��������������ɽȥ������һ��Ҫ������Ʒ���ֵ硢���ߡ���ߡ�ҩƷ֮��Ķ�����һ��Ҫ���롣��˵��������糤��Ȼ����������������⣬���ߴ��һ������Ϣ��С�¡�С��Ҫȥ���Ǹ��ط�����������1950��˷�ʱ�������Ǹ�����կ�ӡ����˽⣬����˷�ʱ�����Ǵ�·���ϸ���������������կ�����ұ����˸��ϸ�����Щ�Եġ��õĶ�������ð������͵������Ա���������������
�������һ��˵�Ǹ�������������������Լ��ͬ�ش�����������������������
���������ʣ������ϸ����������������𣿡�����������
���������Ա����ԭ����û��������Ҳ����̫���ˡ�������������
�����ڶ����賿����ΰ��ͳ����鶼�����Լ��ı����������Ա�����������������г������ˡ�С·���ƽ������С�����������ţ�˭Ҳ�˲���˵���������أ�����¶��һĨ��ǰס���ΰ��ͳ�������ſ�������г���������������Ķ���������������
���������壬����������Ķ������Ǹ�������������ѽ��������ΰ���е㾪�ȡ�����������
���������Ա������ͷ��������������
���������飺�������治�١�������������
���������Ա����Ҫ������Ӳ�����س���һ���֣�������Ҫ���ء�������������
������ΰ�棺�����壬�������������ʲô�ˣ�Ϊʲô���һ��˵�Ǹ��������������������˵ú�������������������������
���������飺�����ˣ����壬Ϊʲô˵��������ǵ����������ϸ��������Ҷ�Ū��Ϳ�ˡ�������������
���������Ա���������벻�������£�������������
������ΰ��ͳ����黶��أ����롭��������������
���������Ա�����ðɣ��Ǿ����Ǹ�����·�Ͻ���ưɡ�������1950��Ĵ��죬���ǽ�ž�Ϊ����������ɵIJ���˰��������ʡ������ɽ������һ��ɽ�أ��������ܶ���ԭʼɭ�֣���������·�ĺۼ�������ʱ��ʱ�꣬����������·�������ˡ�������֧���׳����棬˵������·�ˣ������Ҳ�����ׯ��Ҳ�Ҳ����ϰ��ա���Ҫ�����Ǹ����Ѿ����꣬Ҫ����ʳ���Ҳ����ɲ����������Ա�洶�°���ÿ�Ҫ���¡����ڴ�Ҽ����Ӷ�ץ����ʱ������������������������������з�������ë¿���·æ��æ��æ��Ϊ�İ㣬�ϵ�����Ƿ˼��������ͻȻ��������һ����ʲô�ˣ���ԭ���������ͬ־�������·�ԣ��͵����˽������Ȧ���û�����û�뵽��Ҽ�������һ�����ݵ��ϵ��ˣ��Ұ�ɫ�ĺ��룬ͷ�����ң�������ɫ���ۣ���̤��ѥ�������ź�«����һƥ��¿��¿���Ϲ���һ֧�չ�������¿Ҳ���ָ����ݡ���������Į�����̲�����˵�������ʺη���ʥ��������ϵ�����衣�����������ȵ�������������ʲô�ģ������ϵ���˿��������ʱ��֧�ӽ̵�Ա�߹�ȥ���������ʵ�������λ��ү�����ǵ����ˡ��������й������ž�������������㡣����˵�������ΰ�治����غٺ�һЦ�������Ա���һ����ΰ�棬�ʣ���С���ӣ���Цʲô��������������
������ΰ�棺���ٺ٣����彲ʲô������������������������з�������ë¿���·æ��æ��æ��Ϊ�İ㣬�ϵ�����Ƿ˼�����ĸ�����ʲô��Ҽ������ݵ��ϵ��ˣ��ϵ�������һƥ��¿��ͷ�����ң�������ɫ���ۣ���̤��ѥ��������«��¿���Ϲ���һ֧�չ�������Щ������ڣ��Һ���������С˵�п�������������������
���������Ա���������ܣ��ҽ�������ʵ���������Ժ�����������糤�����������Dz����������ҾͲ����ˡ�������������
���������������ΰ��һ�ۣ������壬��������������������������˵��������������
���������Ա�����ðɣ���������ķ��ϣ�������˵�������ϵ�һ������ɲ�ģ����������ͦ����ò������˵�ǽ�ž����ˣ�����æ��С¿���ϻ������������Źչ�˵����ԭ���Ǿȿ���ѵĽ�ž����ˣ���ʧԶӭ�������к������ʣ����ؿ����������̵�Ա˵�����������Ҹ����䣬��Щ��ʳ��Ȼ�������·�����ϵ�˵������˵����˵��ǰ�治Զ����ɽͷ���չ�ɽ���Ǻ��ᡣ������������˵�ţ���֧�Źչ���һ����Ծ��¿�����ϵ�����һ����«���ҿ����ӣ�����һ��ھƣ�����ȡ��һ����«�ϣ��������������ء����ء���������������ɽ����졣����С���ڽ̵�Ա�����ֹ�������֪���ϵ���ʲô���ã�����������˱��Űɣ����̵�Ա˵������Ҫ����������������߾�������ˡ���������������
��������Ҹ����ϵ�����һ��ɽ��������һ��ʯ���ţ��ƹ����ܵ����֣��㿴�����������é��ɢ����ɽ�ߡ�ԭ���ϵ��������쵽�˰����˵�կ�ӡ���ʱ������կ�Ӷ�Ʈ��һ�ɿ���������ζ���ϵ�˵������������ò�����ζ���ȿ����ͣ��˴����ճ��Ժ������������Կ����������ͣ����ɾ��⡣����ʱ��Ҳ����������ղ��ϵ�����«�ϣ���֪ͨ������������緹���̵�Աæ˵����̫���ˣ�лл�����Ƕ����ǵ�һ�����⡣��������������Ƿdz����飬���������������ڵĿ��������е����绹�����˽��еļ����������̵�Ա����˵����ע��������ɰ���ע�⣬��������Ķ���һ��Ҫ��Ǯ����Ҫ�������磬�Թ�������������������������������������������
�����ÿ���txt������
���������ӳԹ�����ȴ�Ҳ����Ǹ��ϵ��ˡ�֧�ӳ��ͽ̵�Ա�����ˣ���Ϊ�������ɽ�����У�û����Ϥ���ε��˵����粽���С�֧�ӳ������˵�������������Ǹ�ʲô�Եģ�����ȳ�ȵ��ϵ���û��ס���㲻���ϵ������һ��������������͵���ͷ�ˡ���������ż��أ���ɽ�DZߴ����˺�«�ϵ����ɣ��ϵ�������ë¿�������������ء�������������
�������������Dz�֪�����ϵ��а�����������ʮһ�꣬�����游������̣������ĺ������˲��֡�����ˮ�������Ϳ�������ʮ�������꣬��ɽ��ҩʱ��С�Ĵ���ʯ��ˤ�£���Ȼ��ס��������ȴ����ˤ���ˣ���Ҳ���Ĵ����Σ�ֻ�ûص����硣���������������һ��û�н�飬����Ѵ��˶��������Լ��ĺ��������կ�ӵ��˶��DZ��������ɱƵ���ɽ�������ģ����غ��٣���Ҷ�������ڽ�ž����ˣ������������ô�����˱�ͷ���������������ǵ���������������
������ΰ�棺����ô�ϵ������ֳ����ϸ�������������������
���������Ա������ΰ��һ��˵�����ҽ����²���Ϲ��ɣ�������������
������ΰ��ЦЦ�����ٺ٣�����Ϲ�࣬ȷ�����£�ȷ�����¡�������������
���������Ա�����Դ������ϵ���������������·�������˼���ʤ�̣��ܵ����ϼ��ı����ʱ�о����̣����ģ��Ե��ģ�˯���ģ�������û������ϴ�衢ϴ�·��������������϶�����ʭ�ӣ���ҹ�ʭ�ӽи����档һ�л�����������Ϣ����ҾͰڿ����ƣ�����ѵĿ��ӣ�Ѱ�����·���������ʭ�ӣ�������ȣ���˭���ϵ�ʭ����ࡢ��ʣ�˭��������������ǰ�����������ͷ����������������һ���ҵ��ݣ�����Ҳ����������ͷ���ͺ����϶���ʭ�ӡ������ϵ�ʭ����࣬������������Դ�ҷ���Ϊ�ϸ�����������������
�������������ΰ��ͳ����鶼���ɵ���Ц��������ΰ��˵����ԭ������ô���ϸ���ѽ���涺�ˡ�������������
���������Ա���������˵��»����ء�����Ҷ�ʮ���������������Ǵ���һ������¿��ȳ��ͷʵ�ڲ����㣬�ر��Ǽ��о���ʱ����ƥ��¿���ر����Ӳ���ԣ�Խ��Խ���ߡ�����֧��ר���о�����������������������ɻ�ǹ�ִ��������ϵ��ߡ��������ҵ�ɽ����̨ͬ�磬����ͷһ�װ������ң������Բ��������ʹ����ľ��������ӵ�֧��֪ͨ�����dz����ˣ���Ϊ������ͷС�������ᣬ��һͦ��ǹ�ز��˶��١����DZ������κ���˵ɶҲ���ϱ��ˡ�ԭ�������ر𰮸ɾ���ƽʱע�����������ϵ�ʭ�Ӽ����Ҳ��š��ɵ������ϵ�ʭ��ʵ��̫���ˣ����������������ϡ���������ܲ��˵��ǣ��������겻ϴ�裬�������ǹ����ŵ���ζ��Ѭ�ô������������̵�Ա�Ҵ���̸����˵����֧�������ģ��Ǹ�����Ҫ�����뱳Ҳ�ñ��������ʹ�����������˵���ܴ���Ҳ��������С�鿪������������������Ϊʲô��Ը�ⱳ������������ʱ�����˶�������Ĵ�����������������߿ޱ�˵������������ϵ�����ζ��˵������������������˵�Ҳ�Ը�ⱳ���������Ҳ����Ϸ�ʭ�ӡ���������ʮ�����ġ�����һ��͵������̸���İ��������߳���˵������Ҳ����Ҳ����������֮����������֮ͨʭ�ӣ���������֮�����������Ҷ���֮��ʭ�����Ҹ�������֮��ζ���ȣ�������������ˡ������ô�Ҷ�Ц����������˵����������Ա�̲�סЦ�����������������ΰ��Ҳ������Ц�ˡ������Ա����˵��������������һ���£�����ʹ�����ı��˶��ϵ����Ŀ���������ʹ���������˸��Ӱ�ĸ��顣�����������ģ����Dz��ӵ�ָսԱ���DZ��������������ϣ��Բ�ϰ�ߡ�˯��ϰ�ߡ�������ϰ�ߣ�˵�ֻ����˲��١����綫���˿����ʱ˵������������������Ƥ���˲Σ������ݡ���ɽ���˿�����˵����ɽ������������С��عϡ�����ͷ�������������DZ����ˣ��������������������ϵģ�������������
������ΰ��ͳ�����һ��˵������������������ҩ����Ҷ���ն��衣������������
���������Ա������ͷ������սʿ����ɧʱȴ˵�������������������ӡ����ߡ�������������������������ɽ�����ھ����������ϻ���Ҫ���ˡ���˵���ӣ�����ͷ���л��ƣ����˿��ŵ�˵�������ӳ��˺��Ӻ�ͷ�����������ᷢű�������췢���գ�һ�췢�䣬���������û�á�����Ƕ��ߣ����ϵĶ���Ʒ���ر�ȫ��ʲôС�۾������۾������ߡ��岽�ߡ����ߡ�С���������ߡ������˵�ս�ľ����о����̣�˭���϶���˭��ù������Ҳһ���С��������˺��µĻ��Ǻ�������������ˮ����������߸ߵ����ϣ����������ĵصȴ��˵ĵ�����Ȼ����������������֪������������ñЬ��ķ�϶����������˵�Ѫ�����Ѱ����������˵�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