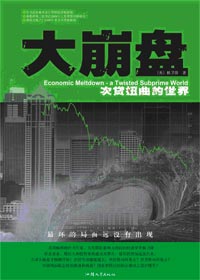平凡的世界(一)-第3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大院坝里空无一人。他很快蹲下来,慌得如同偷窃一般,用勺子把盆底上混合着雨水的剩
菜汤往自己的碗里舀。铁勺刮盆底的嘶啦声象炸弹的爆炸声一样令人惊心。血涌上了他黄瘦
的脸。一滴很大的檐水落在盆底,溅了他一脸菜汤。他闭住眼,紧接着,就见两颗泪珠慢慢
地从脸颊上滑落了下来——唉,我们姑且就认为这是他眼中溅进了辣子汤吧!
他站起来,用手抹了一把脸,端着半碗剩菜汤,来到西南拐角处的开水房前,在水房后
墙上伸出来的管子上给菜汤里搀了一些开水,然后把高粱面馍掰碎泡进去,就蹲在房檐下狼
吞虎咽地吃起来。
他突然停止了咀嚼,然后看着一位女生来到馍筐前,把剩下的那两个黑面馍拿走了。是
的,她也来了。他望着她离去的、穿破衣裳的背影,怔了好一会。
这几乎成了一个惯例:自从开学以来,每次吃饭的时候,班上总是他两个最后来,默默
地各自拿走自己的两个黑高粱面馍。这并不是约定的,他们实际上还并不熟悉,甚至连一句
话也没说过。他们都是刚刚从各公社中学毕业后,被推荐来县城上高中的。开学没有多少
天,班上大部分同学相互之间除过和同村同校来的同学熟悉外,生人之间还没有什么交往。
他蹲在房檐下,一边往嘴里扒拉饭,一边在心里猜测:她之所以也常常最后来取饭,原
因大概和他一样。是的,正是因为贫穷,因为吃不起好饭,因为年轻而敏感的自尊心,才使
他们躲避公众的目光来悄然地取走自己那两个不体面的黑家伙,以免遭受许多无言的耻笑!
但他对她的一切毫无所知。因为班上一天点一次名,他现在只知道她的名字叫郝红梅。
她大概也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孙少平吧?
第二章
孙少平上这学实在是太艰难了。象他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的年龄。可
是他每顿饭只能啃两个高粱面馍。以前他听父亲说过,旧社会地主喂牲口都不用高粱——这
是一种最没营养的粮食。可是就这高粱面他现在也并不充足。按他的饭量,他一顿至少需要
四五个这样的黑家伙。现在这一点吃食只是不至于把人饿死罢了。如果整天坐在教室里还勉
强能撑得住,可这年头“开门办学”,学生们除过一群一伙东跑西颠学工学农外,在学校里
也是半天学习,半天劳动。至于说到学习,其实根本就没有课本,都是地区发的油印教材,
课堂上主要是念报纸上的社论。开学这些天来,还没正经地上过什么课,全班天天在教室里
学习讨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当然发言的大部分是城里的学生,乡里来的除过个别胆大的
外,还没人敢说话。
每天的劳动可是雷打不动的,从下午两点一直要干到吃晚饭。这一段时间是孙少平最难
熬的。每当他从校门外的坡底下挑一担垃圾土,往学校后面山地里送的时候,只感到两眼冒
花,天旋地转,思维完全不存在了,只是吃力而机械地蠕动着两条打颤的腿一步步在山路上
爬蜒。
但是对孙少平来说,这些也许都还能忍受。他现在感到最痛苦的是由于贫困而给自尊心
所带来的伤害。他已经十七岁了,胸腔里跳动着一颗敏感而羞怯的心。他渴望穿一身体面的
衣裳站在女同学的面前;他愿自己每天排在买饭的队伍里,也能和别人一样领一份乙菜,并
且每顿饭能搭配一个白馍或者黄馍。这不仅是为了嘴馋,而是为了活得尊严。他并不奢望有
城里学生那样优越的条件,只是希望能象大部分乡里来的学生一样就心满意足了。
可是这绝对不可能。家里能让他这样一个大后生不挣工分白吃饭,让他到县城来上高
中,就实在不容易了。大哥当年为了让他和妹妹上学,十三岁高小毕业,连初中也没考,就
回家务了农。至于大姐,从小到大连一天书也没有念过。他现在除过深深地感激这些至亲至
爱的人们,怎么再能对他们有任何额外的要求呢?
少平知道,家里的光景现在已经临近崩溃。老祖母年近八十,半瘫在炕上;父母亲也一
大把岁数,老胳膊老腿的,挣不了几个工分;妹妹升入了公社初中,吃穿用度都增加了;姐
姐又寻了个不务正业的丈夫,一个人拉扯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他们家
经常接济一点救命的粮食——他父母心疼两个小外孙,还常常把他们接到家里来喂养。
家里实际上只有大哥一个全劳力——可他也才二十三岁啊!亲爱的大哥从十三岁起就担
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没有他,他们这家人不知还会破落到什么样的境地呢!
按说,这么几口人,父亲和哥哥两个人劳动,生活是应该能够维持的。但这多少年来,
庄稼人苦没少受,可年年下来常常两手空空。队里穷,家还能不穷吗?再说,父母亲一辈子
老实无能,老根子就已经穷到了骨头里。年年缺空,一年更比一年穷,而且看来再没有任何
好转的指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上到高中,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话说回来,就是家
里有点好吃的,好穿的,也要首先考虑年迈的祖母和年幼的妹妹;更何况还有姐姐的两个嗷
嗷待哺的小生命!
他在眼前的环境中是自卑的。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他比别人都低了一头。
而贫困又使他过分地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
内心中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就说现在吧,他对那个派头十足的班长顾养民,已经产生了
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每当他看见他站在讲台上,穿戴得时髦笔挺,一边优雅地点名,一边
扬起手腕看表的神态时,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胸膛里燃烧起来,压也压不住。点名的时候,
点到谁,谁就答个到。有一次点到他的时候,他故意没有吭声。班长瞪了他一眼,又喊了一
声他的名字,他还是没有吭声。如果在初中,这种情况说不定立即就会引起一场暴力性的冲
突。大概因为大家刚升入高中,相互不摸情况,班长对于他这种污辱性的轻蔑,采取了克制
的态度,接着去点别人的名了。
点完名散场后,他和他们村的金波一同走出教室。这家伙喜眉笑脸地对他悄悄伸出一个
大拇指,说:“好!”“我担心这小子要和我打架。”孙少平事后倒有点后悔他刚才的行为
了。
“他小子敢!”金波瞪起一双大花眼睛,拳头在空中晃了晃。
金波和他同龄,个子却比他矮一个头。他皮肤白晰,眉目清秀,长得象个女孩子。但这
人心却生硬,做什么事手脚非常麻利。平静时象个姑娘,动作时如同一只老虎。
金波他父亲是地区运输公司的汽车司机,家庭情况比孙少平要好一些,生活方面在班里
算是属于较高层次的。少平和这位“富翁”的关系倒特别要好。他和他从小一块耍大,玩性
很投合。以后又一直在一起上学。在村里,金波的父亲在门外工作,他家里少不了有些力气
活,也常是少平他父亲或哥哥去帮忙。另外,金波的妹妹也和他妹妹一块上学,两个孩子好
得形影不离。至于金波对他的帮助,那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在公社上初中时,离村十来里
路,为了省粮省钱,都是在家里吃饭——晚上回去,第二天早上到校,顺便带着一顿中午
饭。每天来回二十里路,与他一块上学的金波和大队书记田福堂的儿子润生都有自行车,只
有他是两条腿走路。金波就和他共骑一辆车子。两年下来,润生的车子还是新的,金波的车
子已经破烂不堪了。他父亲只好又给他买了一辆新的。现在到了县城,离家六、七十里路,
每星期六回家,他更是离不开金波的自行车了。另外,到这里来以后,金波还好几次给他塞
过白面票。不过,他推让着没有要——因为这年头谁的白面票也不宽裕;再说,几个白面馍
除顶不了什么事,还会惯坏他的胃口的……唉,尽管上这学是如此艰难,但孙少平内心深处
还是有一种说不出的高兴滋味。他现在已经从山乡圪崂里来到了一个大世界。对于一个贫困
农民的儿子来说,这本身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啊!
每天,只要学校没什么事,孙少平就一个人出去在城里的各种地方转:大街小巷,城里
城外,角角落落,反正没去过的地方都去。除过几个令人敬畏的机关——如县革委会、县武
装部和县公安局外,他差不多在许多机关的院子里都转过了——大多是假装上厕所而哄过门
房老头进去的。由于人生地不熟,他也不感到这身破衣服在公众场所中的寒酸,自由自在地
在这个城市的四面八方逛荡。他在这其间获得了无数新奇的印象,甚至觉得弥漫在城市上空
的炭烟味闻起来都是别具一格的。当然,许许多多新的所见所识他都还不能全部理解,但所
有的一切无疑都在他的精神上产生了影响。透过城市生活的镜面,他似乎更清楚地看见了他
已经生活过十几年的村庄——在那个位所熟悉的古老的世界里,原来许多有意义的东西,现
在看起来似乎有点平淡无奇了。而那里许多本来重要的事物过去他却并没有留心,现在倒突
然如此鲜活地来到了他的心间。
除过这种漫无目的的转悠,他现在还养成了一种看课外书的习惯。这习惯还是在上初中
的最后一年开始的。有一次他去润生家,发现他们家的箱盖上有一本他妈夹鞋样的厚书,名
字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起先他没在意——一本炼钢的书有什么意思呢?他随便翻了
翻,又觉得不对劲。明明是一本炼钢的书,可里面却不说炼钢炼铁,说的全是一个叫保
尔·柯察金的苏联人的长长短短。他突然对这本奇怪的书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他想看看这
本书倒究是怎么回事。润生说这书是他姐的——润生他姐在县城教书,很少回家来;这书是
润生他妈从城里拿回来夹鞋样的。
润生妈同意后,他就拿着这本书匆匆地回到家里,立刻看起来。
他一下子就被这书迷住了。记得第二天是星期天,本来往常他都要出山给家里砍一捆
柴;可是这天他哪里也没去,一个人躲在村子打麦场的麦秸垛后面,贪婪地赶天黑前看完了
这书。保尔·柯察金,这个普通外国人的故事,强烈地震撼了他幼小的心灵。
天黑严以后,他还没有回家。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禾场边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听着小
河水朗朗的流水声,陷入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思绪之中。这思绪是散乱而飘浮的,又是幽深而
莫测的。他突然感觉到,在他们这群山包围的双水村外面,有一个辽阔的大世界。而更重要
的是,他现在朦胧地意识到,不管什么样的人,或者说不管人在什么样的境况下,都可以活
得多么好啊!在那一瞬间,生活的诗情充满了他十六岁的胸膛。他的眼前不时浮现出保尔瘦
削的脸颊和他生机勃勃的身姿。他那双眼睛并没有失明,永远蓝莹莹地在遥远的地方兄弟般
地望着他。当然,他也永远不能忘记可爱的富人的女儿冬妮娅。她真好。她曾经那样地热爱
穷人的儿子保尔。少平直到最后也并不恨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