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捕系列_破神枪-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袭邪道:“下山的路都给我们封死了。”
铣手道:“下山有很多条路。”
袭邪道:“只要能下山的路,都有我们的人——要不然,也声相爷派来的高手。”
铁手皱起了铁眉:”蔡京的人也来了?”
袭邪道:“摇红本来迟有半个月就下嫁蔡家了。”
铁手道:“你们的人能截得往铁锈吗?”
袭邪道:“纵截不下,他若突围,也一定得悉;何况。他给堵死在一两处了。
铁手:“好极了,泰山太大,不好找,一定要有熟路的人”
猛禽道:“关东虽大,但我了如指掌。”
铁手:“你是熟路,还得熟人。”
袭邪:“我也会去。”
铁手:“你不是要坐镇大本营吗?”
袭邪似脸有忧色(还是惧色?):“我跟你们一道去,不热,恐怕堂主会亲自出马了。”
铁手:“听说孙子灰一早已率人卜山,围剿铁锈了?”
袭邪唇角牵动,也不知他是在冷笑,还是在不屑。
猛禽余怒未消:“为一个‘山枭’,一言堂可算是倾巢而出了,要还来个全军覆灭,那可真,嘿嘿铁锈带着那么个如花似玉的美人逃亡,也可谓是风光无限在险峰了”。
袭邪忽道:“你们应承明儿上泰山救人的事,我会禀报山君,这儿先行代谢。”
说罢,他向铁手拱手,看也不看猛禽就带着小红离开了“飞红居”。
小红走前,还看着铁手。
铁手微笑。
小红眨眼。
眼很灵。
猛禽却别首望着铜镜,目不转睛、
——也真奇怪,一个以他那么个长相的男子,理应不致如此喜欢揽镜自照的。
除非他以为自己很漂亮。
候袭邪等人一走,“一言堂”的副堂主“半边脸”孙家变便过来把铁手,猛禽二人,“请”出“飞红居”,离开“绯红轩”,安排往在“一盐院”的客房里。
铁手和猛禽也私下交换过一些意见:
“这儿既然啥都问不出来,不如还是上山救人来得有效。”这是猛禽的看法。
“还是问出了些端倪来了咱们也不算白跑这一趟。”
铁手则很满意。
不过他也有补充:”看来,一言堂里暗潮汹涌,内里的人事倾轧不少,孙疆为人又贪又狠,像头怒虎饿狼,只怕招他的忌的人都不好过,没好下场。”
猛禽冷笑道,“——不过,像这种贪似饿狼的家伙,一定会有不少人故意去犯他的忌。”
说着,他身上又充溢着极其浓烈的死味来。
铁手微微笑了,他发现,这年青人也有他可爱,激越的一面,所以他拍拍对方瘦窄的肩膊,说:”不过贪狼也有好处,一个人若不是又贪又狼,只怕还真做不了事,至少成不了大事。”他宽容的又追加了一句:
“不过,幸好你不是跟孙堂主做事。”
猛禽仍冷腔、冷颜,冷冰冰的说:“——那我宁可跟你一起办事。”
说完这句话,他脸上才有了笑意,终于有了笑意。
终于两人都笑了。
风过处,院子里的花颤着艳红。
然而,这长尾青年身上充溢的“死味”并未消散。
二、小红劫
越夜,死味就越浓。
——看来,这“一言堂”里平素是死的人多,大概是落难应共冤魂语、厉魄夜唱孙家诗吧,这儿虽软被厚枕,雅致富丽,但总令人感到鬼气森森,邪气侵入。
可能,只因长尾刑捕刘猛禽就在他房里之故,只要这个人在,死味儿就特别浓烈。
也许就因这缘故吧,所以铁手特别打了几个呵欠,舒了几次懒腰。
奇怪的是,猛禽原本对铁手就极之瞧下顺眼,但一路下来,似对铁游夏已渐改观而今一入一言堂,尤其是会过一言堂孙疆以降的第一号高手袭邪之后,对铁手仿佛就更具好感了,除了在餐膳后说过“去走一走,探探一言堂虚实,看它是不是真个龙潭虎穴”,就出去了片刻之外,其余时间。居然就在铁手房里闲聊了去,还探问铁手手上侦破的几件赫赫有名的案子,其中包括了铁手名震襄樊的一件大案:
“杀人王”陈海兽终于在铁手的铁怔如山。艰苦追缉下就逮伏法。
——陈海兽是个古怪的人,他犯法杀人,不为名,不为利,甚至也不为报仇雪恨。
他喜欢迫人自杀。
他一直在写一本书,书中记载的就是人各种各样的死法、死相,应怎死才最快,如何死才最轻松,怎样死才最痛苦,何种死法才不知不觉他就喜欢研究这个。
为了要“好好的”观察这个,他不惜常迫人自杀——用各种方式“杀兀自己”,包括用针刺耳膜、蚂蝗噬死、蜜蜂蜜死。甚至是一啖一啖的自食其肉,种下各种病毒让对方染病至死。
这一切,他都从旁细心观察,详加记载,竟视为平生乐事。
他是个胖子,可是武功极高,如果他要迫死那个人,那人也只好死了。
因为除死无他。
也因陈海兽的武功太高,而对武林中人抱待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态度,他迫死的多半是无告平民,所以一般武林人不愿惹他,官府里也没多少人敢出来治他——先得惹了他,反而变成了他笔下记录的“死者”之一。
可是,铁手就冲着这个,找上了他。
当然,铁手当时还年轻,要制裁这个人,也的确不容易:
但不容易的事就是有挑战的事。
——铁手本就喜欢做难做的事、惹难惹的人!
他惹上了“杀人王”。
制伏了陈海兽。
——此役不但使他名动襄樊,更使他获得同道百姓的景仰。
刘猛禽也听过此役,他央铁手说出追捕交战的始未,经不起猛禽的苦苦央求,铁手是追述了一些往事,这长毛尾青年也听得津津有味,死气四溢。
直至铁手呵欠懒腰,表示送客了,这猛禽一般的青年,总不能赖着不走,于是这才告辞,回到他的隔壁房去。
他一走,死味的确好似是消散了许多。
他这头才走,铁手立即长了灯蕊蜡焰,自襟里掏出一张纸:
一张字条。
字笺上有图。
字只有几个:
“小姐留下飘红小记给你。”
其他是图。
绘得极其草草。
铁手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绯红轩”的地图。
他很快的就找到了图上用朱笔圈了个围圆之所在:
那儿速写了两个字:
“紫微”!
——便是“满山红”旁、“绯红轩”前,那棵伤痕累累的紫微树下!
(那几埋了何物?)
(小红在大家都注视墙上挂画之际,把这字条递了给他。有什么用意?)
(“飘红小记”是什么东西?)
不管是什么事物,也不理是龙潭虎穴,铁手在决心以发现壁上美人图引开袭邪、猛禽等人注意力,取得这弱女子手上字条之际,已决心“查明这一言堂”中到底发生了的是什么事,解开他心中存疑已久之述。
他决心要跑这一趟。
生死不计。
月明。
风清。
铁手在洗手。
他很认真、仔细、温柔、顾惜地在水盆里于干净净的洗干净了他的手。
他的手本来不洗都很干净,干净得连只留半分的指甲也全无半点污垢,但他还是十分仔细、温柔、爱惜、谨慎的一再洗干净了他的一双手。
然后他又用一块干净的布,揩干净了他的手。
他打开了窗。
便看见了明月。
他长吸一口气,闻到了淡淡也郁郁的花香。
他忽然想起摇红:一向长住在“绯红轩”里的姑娘,岂不是常常嗅到这种花香,夜夜闻到这样飘忽的幽香?
——像这样一朵花般娇艳的女子,却落在禽兽一般的家伙手里,今夜,在泰山上的柔弱女子,恐怕不易渡过吧?
他这样想着时,已抹净了他的手。
房里只剩下了一盆清水。
他的人已不见。
窗台微晃。
房中的水仍清清。
直至水面上又晃现了一条人影:
这人在水面上一出现,仿佛连水都像是感染了他的黑,像一滴墨汁注入清水一般的“化”了开来。
水黑如夜。
水面上的人影一晃而过,他别过头去的时候仿佛还闪过了一条黑黝的虎尾。
房里的水仍很清。
清得像照向天庭的一面照妖镜。
一出房间,进入“一言堂”的布防的范围,铁手已躲过三路暗桩五处埋伏,就像黑夜里一棵会高速移动的树,分外感受到在这危机四伏的“一言堂”内杀机重重,步步惊心,甚至月为之寒。风为之厉。
但他仍坚持。坚定、坚毅地往“绯红轩”追潜过去。
——小姐留下飘红小记给你。
(什么叫“飘红小记”?)
(为什么要留给他?)
他一定要找到小红,或觅着小记,来弄清楚这件事:
再大的劫难他都不怕。
因为惟有苦难才能迫出伟大,愈是历劫的人生,愈见生存的意义。
他是个沉着稳定的人,但沉稳不代表他不敢冒险。
他的“沉”是在于他不急不嚣、不动声色;他“稳”是在于他胸有成竹、能当重往。
但他可不伯犯难,不怕历险,更不怕失败,所以他才从事捕快这吃力不讨好的行业,就算失败也更能衬托出成功的美。
——盖若以捕快衙差行仗义持正之事,要比江湖上任侠之上替天行道还多制时。更不易能有所为。
因而他才知易行难,偏选择了这要命的行业:
要不然,谁是侠?谁是盗?谁忠谁好?还有谁来主持公道!
——公道有时就像是一场忘情的花香,总要让懂得欣赏她的人才能分外体会那解人的香是来自花的心。
而今铁手却没有访花的心情。
他来探案。
——如果白天他是在明查,那么今晚的他则是在暗访。
他终于到了那棵紫微树下。
凭着花香。
花香为记。
凭着风声,他在黑夜里全无声息。
仗着月色,他发现树下有一处松士。
他立即往下挖掘:
在这当几,他似完全不再珍惜他那双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大大厚厚的手。
他的手仿佛比刀锄还有力。
更有劲。
他终于掘着了一件事物:
一本书。
他挖出了一本册子。
映着白色一照,只见沾满了泥块的册子对面上,写着几个端秀的字:
飘红小记
——飘红小记,所记何事?
趁着月色,他迅疾的揭了几页,第一页就写有几行娟秀的小字。
得志则寄情予雄图,得势自寄情于霸业;失望则寄情予山水,失意自寄情于文艺。惟我情意两失,寂寞无边;春去秋来,惊红片片。知音能谁报,生死两不知,故作飘红小记,余不一一。
孙摇红。
铁手只匆匆翻了几页,看数行字,已知此记事册内牵涉重大,略阅亦生抢然、正要把书册藏干襟里,忽然闻得一股死味。
他眉头一皱,很快的分辨了一下:
不,不是死味,而是极接近“死味儿”的血腥味。
幽静的月色下,满山红都成了惨绿、灰黑,风过去,兀自摇了几下,却晃不出白天所见那二身惊艳的休红来。
可是,地上却泊旧的流动着一股诡奇已极的红。
这红已静悄悄的流到铁手脚下,浸湿了他的鞋底:
这红比花还艳、幽静得像一个杀手,悄没声息地缠上了铁手,然后又喧哗的迅速染储了他下蹲时拖地的袍裙。
这红会动。
这红有感情。
这红色仿佛自有生命。
这是血
血当然是有生命的:因为准没有它就失去了性命。
——所以失去它的人便失去了生命。
因而一定有人己丧命:
因为谁也不能失去那么多的血!
当铁手发现这是血的时候,他就断定这是同一个人体内流出来的血。
他“认得”这些“血”。
他能凭这“血”追认它的”主人”。
他果然没有猜锗。’
他找到了死人:
就在树的后边。
一个女子,全身赤裸,给钉死在树干上,双脚离地约七尺。
她的小腹给一刀划开,然后贯穿透体钉在树上肠胰己溢出少许,但血就从那几流出来,沿着树干的疙瘩直淌,已流了很久很久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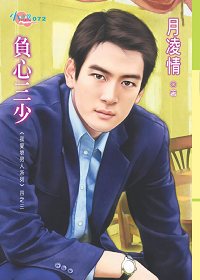



![实验的人生[法医馆系列]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1339.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