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高原-第11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一见岳父就赶紧上前一步,接着双腿并拢,“啪”地打了个敬礼。
岳父鼻子左侧的肌肉抽动了一下,松松垮垮地向对面的老者还了个敬礼。
我笑不出来,而且心情立刻变得肃穆了。我发现自己也像那个老者一样,不由自主地把脚跟并到了一起。
他们在沙发上坐下。
我想听他们说话,但待了一会儿又觉得不妥,就退到了一边。梅子小声说:“来的老人是父亲在部队时的一个警卫员,他刚在环保局副局长的位子上办了离休手续……父亲是他的老首长,他隔一段就要来一次……”
“‘首长’永远是‘首长’吗?”
“那当然了。当年父亲的一些部下如今很多都在这个城里工作,他们常常来玩,不过都不怎么打敬礼了,只有他还这样。多好的老同志啊。”
“打敬礼好,我就愿看他们打敬礼……”
梅子觉出了有什么不对劲儿,不跟我谈了。
老头走了。我发现岳父增添了一种不能抑制的兴奋。他把衣扣解开走到院门口,又站在小院里大口呼吸,望着远方。西南方有一朵红云,太阳就要落山了。岳母走过去,站在男人身边。岳父这样待了一会儿,转回身来长长叹息:
“老啦,我们都老了!剩下的事情要由你们去做喽。”
我神往地看着他。
“你那些东西,”他用食指指着我的衣袋,好像我衣袋里就装了什么东西似的。但我很快明白他是指我平常写的那些东西——“你那些东西,也该写一写我们的这位老同志。很勇敢的人嘛!出生入死。他腿上中过弹,那是一颗炸子儿,到现在还留下一块很大的疤瘌。”
我点着头,这时突然想起了什么,问:“您也受过伤吗?”
岳父好像不屑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一起回到了沙发上,“那一年我们被围在一个小山包上,小山包的下坡那儿有一个小村。我们从村里退出来,占领制高点。”岳父右手的食指在半空里点了一下。
4
与岳父在一起时,我珍惜每一次谈话机会。只要谈到了战争,我就忍不住好奇,越问越多:“那时母亲也和您在一块儿吗?”
岳父的思绪完全陷入了那场战斗,对我的询问充耳不闻。“我带着警卫员边打边撤。就是这个老同志,那时他年轻得很哩,就像你这么大年纪,一手好枪法。就是那一次突围中他受了伤……我怀疑我们那一次驻扎被人告了密。出了叛徒啊——我一直在怀疑一个人,那个人如果活着,大概至少也有九十多岁了……”
我最恨的就是背叛。这时我脱口而出:“那个人大概不会活着了……”
岳父一愣,木木的眼睛转向我:“你怎么知道?”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忆阿雅》(47)
我吞吞吐吐:“谁知道,反正……叛徒还能活那么大年纪吗?大概不会的,从心理与生理的角度看,叛徒们的一生总是被巨大的痛苦压迫着……他们要活过九十岁是很难很难的。”
岳父终于听明白了,失望地叹了一声。
而我毫无调侃之意。我在说这些时,甚至在心头涌起一股对叛徒的仇恨……记得很早以前了,我还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叛徒”的诗,其中有两句这样写道:“我是一个叛徒/所以我活不久/为了活得久/我才背叛/然而我是一个短命的叛徒……”
我随口念出了这么几句。岳父一开始听得很认真,后来又皱起了眉头。
梅子说:“什么啊……”
岳父接上被中断的话头:“那个人就在这片平原上活动,他常常进山。本来是我们的人,可是他的行为后来还是让人觉得可疑。他经常到海港上去,那时候你知道,海港可在敌人手里啊。他跟港上的人混得很熟。我曾经提醒过首长,可是首长不愿意谈这个。有一次我没经过首长的允许就一个人盯过他的梢。那天他一直在前边,化了装,扮了商人模样,戴了礼帽,穿了长衫,枪就掖在长衫下边。鬼精,走了没有二里多地他就发现了我。可他装着什么都不知道,拐过一个山尖嘴时一阵疾跑,人不见了!我就往前摸;刚刚摸了没有多远,他就从一边蹿出来,抬手给了我一枪。那一枪打在我的耳朵上面,只擦破了一点皮……”
我看看他的耳朵那儿,没有发现伤痕。
“嗯,”岳父在耳朵那儿伸手弹了一下,“我就掏出枪来,先找个地方隐藏好。我知道他早晚要从石头后面蹿出来。我等着,等了好久,一点儿声音都没有。这时我才知道上当了。我转到山石那儿一看,见下面有一条羊肠小道。原来他从那儿滑溜下去了。下面有绿腾腾的茅草、葛子、松树,他就攀着它们绕过了山涧,顺着河口跑了……再到后来我们还见过面。不过日子久了他认不出我来罢了。也许是一场误会,他还跟我握手!这人会讲一口流利的南方话。”
梅子在我旁边,脸色冷冷的,两眼一眨不眨盯着父亲。
“那时候很冷酷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梅子她妈十几岁就会打枪。她有一手好枪法,可是后来服从工作需要,当了护士。有一天战斗间隙里我去看她,她正好从帐篷出来,两手都是血,就带着两手的血,她抱住了我……”
岳母咳嗽着。
“她抱住了我。我身上也沾了血,可是我们顾不得那么多。整整一年多没有见面了……”
岳母听到这里不咳了,眼圈红了:“那是什么日子啊,什么日子啊!”她的眼睛在那一瞬间变得火辣辣的,直直地望着自己的男人。
岳父站起来,手在胸口那儿抚摸着。这时我不由得想到:那个扮了商人的家伙如果枪法再稍微准一点儿,那么就没有眼前的岳父了,当然也就没有我的梅子了——也没有了我们的小窝——更不会有眼下的这个小院……一切都将完全不同——可见只差那么一点点,我的生活就将全部改变。看来很多事情完全出于偶然,一切都只差那么一点点。历史正是如此,往往就是在一瞬间里被决定和改变的……后来我又反过来想:如果岳父当年打死了那个人呢?如果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他的子弹又落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罪愆的人身上,那么眼前的这个人不就成了一个杀人犯吗?那个扮作商人模样的人就因为遭到了盯梢才向他射击——而岳父有什么理由去盯梢一个无辜的人呢?就因为一点点怀疑吗?这种盯梢显然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而且一旦有了那个可怕的结局,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场谋杀:于是对方也就有理由用枪射击……这种道理也许在血与火的时代已经讲不通了,也许岳父做得才是对的。当然,从哪一方面讲,他今天也都不必埋怨那颗射来的子弹了……当时他如果被击中,那也丝毫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也不必吃惊,因为在战争年代发生什么都是完全可能的、合情合理的。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忆阿雅》(48)
关于粥的谈话
1
不知怎么,周末与岳父的那场谈话总是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我从头至尾回忆着他讲述的那个追踪和对射的场景,后来竟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我突然记起了母亲和外祖母讲过的父亲:当年他就常常扮作商人,来往于山区和海港之间;而且,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南方话!天哪,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
我开始设想那个被岳父追赶盯梢的人与我的生活一定有什么更密切的关系。无可怀疑的是,我的父亲的确在战争年代里扮过商人,而且他的个人经历与岳父的叙述简直相差无几——这当然也极有可能是幼稚的联想,因为我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依据,但我总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过去的年代里遭遇过,我有一种强烈的直感……
有一天晚上临睡前,我竟糊糊涂涂对梅子说了句:“你的父亲用枪打过我的父亲……”
梅子把灯按亮,直看了我十多分钟。大概后来她把这当成了一句玩笑,转过脸去继续睡了。
我却执拗地说:“我父亲也曾经扮过一个商人,也曾经在山区和那个海港之间蹿来走去。你怎么敢保证你父亲就不是用枪打了我的父亲呢?”
梅子笑了。可我没有笑。当然这种可能性也许只是一种想象、一种虚构,但是谁也不能完全将其排除吧。
那天我与梅子就宿在她原来的房间里。第二天,起床后我发现岳父显得很疲惫。显然他夜间没有休息好。我想这一切都坏在那个随便打敬礼的瘦老头身上。果然,岳父仍然沉浸在昨天的情绪里,早饭后沏了一杯茶,一边喝一边讲起了战斗故事。
他说他认识一位连长,双手打枪,打得准极了,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零零碎碎击毙了二十多个敌人,“营里给他开庆功会。那一年正好我们要转到地方休整,临走时,大家把他放到一头骡子上,胸口挂了一朵大花。我拉着骡子,我们在街口上转,老乡放鞭炮,给他茶蛋吃……”
这样谈了一会儿,岳母也走过来听。后来岳父终于疲惫了,就闭了嘴巴。他把目光转向我,好像我也该谈点儿什么——他们平时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海边林子里的事儿,因为他们当年随队伍在那儿活动过。
我说:“……我们那儿有个卢叔,战争年代给队伍喂过马。他常拉着一头大青骡子在园子里走。卢叔退伍以后就做了饲养员。他把我放在骡子背上,牵着骡子吆吆喝喝到处走……”
岳父闭上了眼睛。我认为他是在专心听我讲。
“卢叔是个猎人,单身汉。他枪打得好,心非常狠。他早年当兵时可能不光做饲养员,有时也要打枪吧?也有人说他做过伙夫。他的那个屋子围了小院,离我们的那片林子算是最近的了……我小时候常去他那儿玩,可是他并没怎么讲在山区和平原打仗的事儿……”
岳父干咳了两声。
岳母两手合在胸前,“你爸在山区和平原都打过游击。他对芦青河口那儿也熟得不能再熟了。”
岳父眼睛仍然闭着,点点头:“我在那里任过支队长,和北海银行的同志很熟噢。那个战时银行了不起啊!我在那里住过一年的光景,那儿的人会熬一种春米粥,好喝着哩。现在没有种春谷的了,都是夏谷——夏谷,没有油性,做粥不好喝。战争年代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春米粥……”
我说:“那里的林子很密,林子南边的空地上种满了谷子,都是春谷。河口那里的谷子长得最旺盛,到了秋末简直是一片金黄,叶子卷起来,太阳一照金闪闪的。野兔很多,在谷地里蹿来蹿去。天上的老鹰瞅准了就一个猛子扎下来。老鹰有时一动不动,像在天上放了一个风筝……大多数时候它们逮不住兔子,因为兔子活动的地方总离自己的洞穴不远,再加上特别灵巧。它可以跟鹰在谷棵和草丛里斗智,鹰盯住它,它就躲到密密的谷棵下面,有时候还躲到荆棵里。鹰钻不进去……”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忆阿雅》(49)
岳母觉得有趣,看着我,微微含笑。
我顿了顿又说:“林子里每天都有很多动物在闹,有的动物……”
岳父一声不吭,他睁开眼又闭上,把脸转到一边。
2
我不管不顾地说下去,因为一说到过去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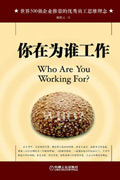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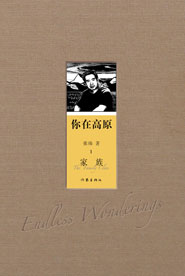





![[综漫]爸爸,你在哪里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9/1950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