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在高原-第10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忆阿雅》(15)
这会儿,她很快让我明白,她请我来的目的十分单纯,不过是出于怀旧和惊喜。“你前些天,就是刚走的那天晚上,我哭了。”她说。我对她的话并无怀疑,虽然那天我一点儿都没有哭。她留恋过去的时光,这一点人人一样。她现在可能是一个富婆,钱对她来说完全不是什么问题,但时光和青春这一类东西对她仍然是最大的问题。“我真是老了,看看,你当年吸过的*都拉耷下来了。那时你的小手……”她声音蔫蔫的,眼皮也蔫蔫的,显然并没有什么*的兴致。她不过是在一种特殊的职业中变得更加质朴了而已。不过我的脸却像被开水烫了一下似的,照照镜子肯定是红的。看来我仍然不行,在某些方面仍然要处于她的下风。这是迫不得已的一种情形,令我很不舒服,甚至让我因此而厌恶自己。她像是随便地、极不情愿地瞥了我一眼,而后吐出一句:“就那样,我那天晚上糊糊涂涂地被你要了。”
我心底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在反抗,我想大声警告对方一句:不,你那时绝对不是一个受害者,而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是对于一个少年可怕的、一生难忘的伤害……但这句话只是在心里翻腾着,并没有说出来。可是我脖子上的青筋已经暴了起来,这是我完全感觉得到的。我的拳头攥了攥,又张开十指轻轻叩着桌面,发出笃笃的声音,那仿佛在悄声质问:是吗?这是你说的吗?她又重新点上一支烟,声音更加懒散散的了:“你当时怎么知道,我那时还是一个黄花少女啊!”我抬起眼睛看她,她却一直耷着眼皮。我差点跳了起来。但我按捺着,紧咬牙关。我遇到了一个来自老家的、不可战胜的老江湖。
她让我待下来的理由,真是复杂到了极点。我对这个城市的夜晚有一种忍受的极限,我对她所代表的昨天有一种不可摆脱的依赖。这是毫不夸张的一个说法:依赖。一个人就像一棵树,他真的有根须,很深很深的根须。我的根须扎在那片海滩平原上,那儿关乎我的生死存亡。而面前这个人不管是邪恶的还是庸常的,她确凿无疑地将我一把拉回了昨天,让我不得不品味那个致命的时刻,那个让我心惊肉跳又是无比留恋的少年时代。
4
我已经神差鬼使地来了阿蕴庄三次。一切都是瞒着梅子进行的——其实并没有“进行”什么,我来这儿只是与她待一会儿,听她絮叨一会儿往事。她现在竟然有了一个特殊的爱好,就是虚拟自己的昨天,虚拟一些细节。如果这种虚拟关乎我们两人之间,她的话就不可遏止地多起来。她现在说话的声调永远是懒洋洋的,这不由得使我想到,她的生命激情真的已经在独特的生涯中用尽了,以至于在这种时刻无论如何都提不起神来。她身上时刻不离一个步话机,这可以让她随时随地控制整个地盘。这里的一些神秘事情已经无法瞒我,看来她也无心瞒我。对她来说,我是一个城市异数,一个完全不需要提防的角色。用她的话来说就是:你是谁呀?尽管我们这么多年没见,可是一见了就连血带肉一样亲!世道再乱,女人在风尘里打滚,她的第一个到死都不能忘!她这样说时,当然是一次次强调我们两人所谓的昨天。我却一次都没有戳破她的公然说谎。我心里清楚地记得真正的事实不过是:一、我十多年前严格讲并没有与之真正发生那种事;二、她当时绝不是一个初次经历男人的女人。我极不情愿却又不得不沉入的回忆,是我最难以启齿的那一段——那时她极力诱导我,让我一起加入那种恐惧的游戏,可最终还是不行。是的,我的浑身都被她弄湿了,她也忘情地骑在了我的身上。我用尽全力地掀她、掀她,甚至想揪她的头发。可她依仗着年龄的优势,闭上眼睛不管不顾地压住了我,那会儿不得不让我想到了“蹂躏”两个字。她嚎叫的声音像猫一样,是春天爬上树梢或屋顶尖叫的那种猫。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忆阿雅》(16)
我的回忆终于引出了愤愤的回击。我扔下一句:“一切都是无稽之谈!我那时候还什么都谈不上……”她第一次笑得这么灿烂,可是照旧耷着眼皮不看我,说:“当然了,你还那么小,用书上的话说就是‘聊胜于无’。不过这对我已经足够了。我很幸福,我那一次很幸福。”
她的这种概括和回应真是可怕。这甚至让我一时没了主意,只好愤怒无比甚至有些绝望地看着她。她还是不太在意我的表情,懒懒散散说着:“算了,别想那么细发了,想得太细发咱俩都会受不住的。因为我也不是七老八十的年纪,你也别*了我。”她丢了烟蒂,去近处的小卫生间,门也不关就哗啦啦撒起了尿。她一边提着裤子一边往外走,咕哝:“我是胖了。你还记得那时候吧,我的屁股像小瓷钵子一样,又圆又滑。现在不行了。你不洗个澡?”我不洗。“那我洗了,你自己看看电视什么的。你要不见外就进来说说话,我泡我的。”我没有理她。她去那个大浴室了。
我站在窗前看着这个阿蕴庄,这儿一切都尽收眼底。我发现夜深之时,这个院落原来是如此热闹,这与平时、与夜色初降时分大为不同。一些轿车无声地开进来,它们一辆辆泊在车位上,整整齐齐,使人想到这里的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那些小姐们纷纷出来迎客,毫不扭捏地挽上车中出来的男人。有一个剃了秃头的中年人好像有点儿眼熟,他跨出车门就让我一惊,接着往窗前靠近了一步。可惜只一闪他就转过身去。我在心里说这不可能,因为一方面他在很远的那个城市居住,另一方面他绝不会到这样的地方来吧。门廊的红灯悬挂起来,血一样红。庭院里其他的灯都暗暗的,惟有这血红成了主要的色调。安静的红色笼罩着一地绿草,反射出一种暧昧,一种温煦中透着腐臭的气息。
我正在窗前看着,突然有一只湿漉漉的手按在了我的肩上。她只披了一条大浴巾站在我的身后,我一回头给吓了一跳。她浑身上下滴着水珠,一个刺目的*,肉滚滚的。她几乎没怎么耽搁就转身去取烟,又用什么东西在身上搽了搽。我只一瞥就发现了她的前胸那儿有一道短短的伤疤,极有可能是刀伤。她搓一下那个疤痕说:“不用看,这里十年前被戳了一刀。都是小意思。”她像佩戴了一枚军功章一样骄傲,见我背过身去,就故意转到我的对面。她小腹那儿的毛发竟然在灯光下变得金灿灿的,这真是奇怪到了极点。我不得不克服难言的羞涩和越来越强的屈辱感,仔细看了一眼。不错,是一种金色。她大笑:“这回算让你见见世面!这就叫‘深度化妆’。什么描描眉、染染脚指甲呀,那不过是小意思……”
不行,我得走了。我往门那儿跨了一步。
“走吗?走就走吧。记住,这里就好比你的家,你随时想来就来。”
5
这些天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整理起屋角里的背囊,用刷子清除上面的落尘。梅子看在眼里,终于忍不住问了一句:“又要出去吗?”
我没吭声。因为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呢。她直盯盯地看着我,后来扯走了我手里的背囊,一下把它扔到了屋角。我真想告诉她:我快四十岁了,这个年纪的人就是要四下里走走,要到外面去,他的这份自由谁也不能剥夺;他要抓住自己所剩无几的一点点机会……我特别想说的是,我在遇到你之前就已经历尽了艰辛,双脚满是血口——难道我连出差、到山里去一趟的权利都没有了吗?难道因为你是我的妻子,你就有权任意摆布我、胡乱扔我用了十几年的背囊吗?要知道那里面可装满了一个中年人的辛酸……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忆阿雅》(17)
她出门以后,我用了好长时间来平静自己。我把那个背囊拾起,折叠好,重新放好。
这是一个周末,梅子的弟弟小鹿来了。这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小伙子,眼下正在市体工队集训。他长得很高,是体工队里才有的那种长腿小帅哥。他的到来使小屋里的一切惆怅一扫而光。我从心里喜欢这个内弟,一直觉得他是这个城市所能生出的最好的一个小伙子了,高爽,清澈,多么纯洁。他的眼睛里没有一丝惆怅,永远像漾着一汪清水。他在这儿玩了一会儿才流露真实的意图:邀请我们一起回爸爸妈妈那儿。平时我不愿到梅子家去——那个宽敞的小院尽管有一棵迷人的大橡树,有精心培植的花草,可对我还是没有什么吸引力。可是现在,这会儿,我却无力拒绝。当我一口答应到他们那儿去时,小鹿跳了起来,梅子也立刻变得高兴了。
老远就望到那棵大橡树了。橡树之家啊,你本来应该是最好的去处……岳母长得胖胖的,皮肤白皙,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小得多。我和梅子每次回去她都高兴得很,为我们张罗好吃的。岳父不苟言笑,十分沉稳,在我的印象中,任何时候他都在思索,都在工作。我这会儿在院子里稍一停留,然后径直走到了他的书桌前——他离休后搬弄了各种各样的书来看,一有时间就读,摆出一副继续办公的架势——这会儿他刚刚离开了书桌,桌上有一本摊开的大字印刷的书籍,中间正放着一支红笔。我瞥了一眼,正好看到了上面用红笔划过的一句话: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岳父进来,我也就站得离书桌远一点。
我们的交谈总是十分简单。他说话时有许多的“唔”、“嗯”、“很好啊”。这使我无法畅所欲言。我甚至无法呼出“父亲”两个字。我心里明白,我自小被这两个字所伤。
梅子的弟弟正在院里玩,我就找个机会离开岳父,也加入到院子那一伙去。接下来的时间我差不多都和这个小伙子在一起。他和我比赛弹跳力。他每跳一下,都在能够触摸到的大橡树干上用粉笔划一道白线。我发觉他的弹跳力可以比我超出半米。这就是个体差异啊。
这个周末过得还算愉快。傍晚,梅子从外边捎回一件裘皮大衣。我们花不起这笔钱,这肯定是岳母给买的。一种金黄色的毛皮,黄得让人都有点儿害怕。我不能不想到那是从可爱的小动物身上剥制的……梅子多么高兴,她大概在想象冬天,想象那时走在雪地上会有多么快活。为了搭配这件衣服,她甚至顺路买了一双漂亮的高筒皮靴。
就在她喜气洋洋欣赏裘衣的这个夜晚,我终于提出:咱们一块儿回我的老家一次吧,到芦青河湾,特别是到那片大山里去转转——“你能和我一起吗?”
梅子的脸色冷了一下。她以前到过那儿,以前我们真的有过一次浪漫而难忘的山区之行。她大概想问:你在那里已经没有一个亲人了,为什么还要频频地、一再地跑向那片大山?
我心底里有个声音在奋力作出解释。我想说,在这座燃烧着的城市里,我已经被烘烤得快要枯干了。我发现先是头发开始失去光泽——而原来它是浓密油亮的,现在真的像一撮枯草了,再有不久就要一把把脱落了。我知道任何植物都要选择一块土壤,如果硬要把它移栽到一个贫瘠的地方,那么等待它的只有衰败和死亡。这就是我阵阵不安、急于离开这座城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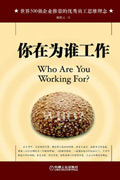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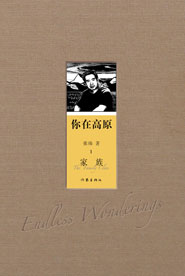





![[综漫]爸爸,你在哪里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9/1950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