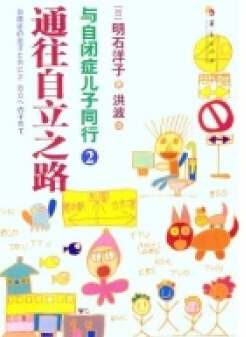燕歌行2-第1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汗水,留下我无数回忆的土地,我大概,是再也回不去了……
一股难言的酸涩突然不受控制地涌上心头,让我的喉咙突然哽咽。
那场宫变到现在已有半年。在过去的每一个辗转难眠的漫漫长夜里,我都在努力地对自己说:忘
记,忘记……忘掉过去的所有一切,让自己在这里重新活过,不管怎样。
我以为自己可以做到的,但是现在我才知道,忘却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一件事。
当你千方百计想要忘记一个人一件事的时候,总会有什么东西猛然间涌到你的眼前,揭开你的伤
口,击破你的防卫,让你重新记起过往的一切。
而你却无法回避。
……
“喂!你怎么了?”雷鸣奇怪地推推我的肩膀。
“哦,没什么,又有点困了。”我恍然收回飘远的心神,有点勉强地笑了笑,随口搪塞道。
“真是服了你!”雷鸣信以为真,很是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一天要睡多少时候才会够!”
我耸耸肩,无意中对上易天的眼神。他正静静地凝视着我,温和的目光中隐含着几分关切的味道
,显然是看出我有些不对劲,只是很体贴地没有发问。
没事。我感激地回他一个灿烂的笑脸。比起缺心少肺大而化之的傻小子雷鸣,易天实在是善解人
意得多了。他总是那么温柔含蓄地淡淡笑着,不动声色地关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默默地为你做
着一切,甚至在你开口之前就已经送上了他的支持。这样的好男人现在是越来越少见了。如果我
有个亲妹妹,就算死磨活赖也得把她嫁给易天。
不过这并不代表我打算让易天知道我的心事。
是的。我感激易天的细心和体贴,欣赏他的沉稳内敛和温柔含蓄,也喜欢雷鸣的爽朗率真的阳光
与活力。如果是在一年前,我一定会和他们成为无话不谈、可托心腹的莫逆之交,可是现在……
我们大概只能是朋友,互相欣赏互相尊重的君子之交。我想我已经失去了彻底敞开心怀与人相交
的信心和能力。
祁烈给我留下的这个印痕,也许我永生都无法磨灭。
说话之间,西秦使节的车队渐渐近了。我拉着雷鸣和易天向后退了几步,顺便不露痕迹地把自己
隐藏在雷鸣的身后。不知道西秦这次派出的使节是谁,但无论是谁,他都大有可能曾经在朝上见
过我。在这里被人认出是件麻烦事。尽管我的样子比起以前已变了很多,可还是谨慎点比较好。
站在路边的人群中,我就象一名普通的北燕百姓一样,漠然地看着西秦的车队从面前驶过。
目光所及,一抹刺目的浓黑陡然跳进了我的眼帘。
什么?!我不敢相信地揉了揉眼睛,仔细再看,终于确定我的眼睛并没有出错。
没错,是黑色。马颈上的簪缨,车厢上的垂饰,还有……看到每个人衣襟袖口的黑色滚边和腰带
,我心头巨震,脸色在刹那间白了一白。
按西秦礼仪,这是国主大丧才有的装束,难道祁烈……
怎么可能?!祁烈他怎么可能会死!!!
我闭上眼,想让自己平静下来,脑中却轰然乱作一团,心中更浪涛翻滚,说不清究竟是何滋味。
祁烈现在是我的敌人了。他背叛我,夺走原本属于我的一切,追杀我,并且一步步将我逼到死地
。他死了我应该高兴的,但是并不。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并没有一丝一毫感到痛快,反而有些惘
然若失,甚而有几分异样的感觉。
当然,毫无疑问我恨他,在内心深处我也许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背叛。可是那并不代表我希望他
去死!
小烈,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既然从我手中夺走了这片江山,就应该做得比我更好,更成功,才不
枉了你处心积虑的一番背叛。你又怎么能随随便便地就这样死掉,随随便便就抛下一切?这样子
你又能对得起谁?
不知为什么我的眼睛竟有些酸涩。不不不,我是不会为他流泪的,那个冷酷无情的狠心小子,一
定不会。
可是心里却茫茫然乱成一片……
直到车队全部过完我仍然呆呆地站在街边,被雷鸣大声叫了好几次才回过神来。
“喂,你今天是怎么了?老是神不守舍的!少睡一会儿觉就困成这样?”
“……没什么。”我努力维持住平静的表情,故做轻松地随口道,“这次西秦派出的使节是谁啊
?”
“我怎么知道!”
我立刻把目光转向易天。易天的消息一向灵通,什么事情都很难逃过他的耳目。但这次他也摊了
摊手,表示自己一无所知。
我皱皱眉,不说话了。不管来的是谁,我都得想法打听一下西秦现在的情形才行。我不相信祁烈
就这样死了,怎么都无法相信。他是那么的年轻,精力旺盛身手矫健,象一只猎豹般充满力量,
又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死呢?”我不知道自己已经自言自语地问出了声,“这么年轻……”
“这并不奇怪。”易天听到了我的话,淡淡地说,“政变哪有不死人的?就算是亲兄弟也是一样
。隔这么久才听到祁越的死讯,我已经觉得很意外了。”
“什么?”我一怔,以为自己不小心听错。“谁的死讯?”
“祁越啊,西秦的前任国主,也是现任国主的亲哥哥,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
这一次,我才彻底地呆住了。
听过易天详细的讲述我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他们的服丧并不是为了祁烈,而是为了我——
七天前祁烈终于下诏宣布了我的死亡,并且以国主之礼为我落葬,从而正式结束了我的朝代。
代而起之的是“承天”这一个崭新的年号,一位更强硬更有力的铁腕君主,以及一班趁时而起的
朝中新贵。
不知道是否念及旧情,祁烈并没有象通常的政变成功者那样,彻底地抹煞我的地位。但是这又有
什么意义?我死了。举世皆知。尽管我现在仍然生存,却再也不能以祁越的身份在人前出现。祁
烈更不会容许我的存在。他轻飘飘的一道诏书,便彻底断绝了我恢复身份重回故国的所有可能,
断绝了许多人恢复旧朝的指望,更巩固了他根基未稳的统治地位。
很必要也很有效的一个手段,其实他早就该做的,我不知道他是因为什么才拖了这么久。
但是我知道,这道诏书一下,就算是正式地割断了我们两人的兄弟之情。我亦再也无法逃避这个
冰冷的现实:小烈,我最疼爱也最信任的兄弟,愿意把一切都与他分享的那个人,他是真真正正
地要我死。
其实早就知道这个事实,心里也早已痛到麻木,然而此刻重新回首,才发现伤口仍旧鲜血淋漓,
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静静地腐烂。
今夜,大概是又要终宵不寐了。
****************************************************************
深夜。没有月亮。夜风清冷。
我独自坐在一个僻静的小山丘上喝酒。
我的酒量并不好,象手中这样的烈酒一喝就醉,可是我想醉。 醉了可以忘记很多事。那些事我
并不想再记起,然而它们却始终顽固地在我的脑海中往复盘旋,挥之不去。
比如第一次见到小烈。当时才只有半岁的他还站都站不稳,却偏要挣脱嬷嬷的手,跌跌撞撞地自
己乱走,结果一跤便跌进了我的怀里。好象就是从那以后小烈便粘住了我,总是哭着闹着一定要
我抱,让我怎么都摆脱不开。
那时候,我也还只是个孩子呢……
还有,第一次教小烈认字。那时他两岁,精力旺盛得象只小猴子,整天在宫里四处乱跑,只有在
我抱着他的时候才会稍稍地安静下来,老老实实地坐在我怀里看我读书写字。我坐在桌前读战国
策,他就时不时伸出小手指着一个字,问:哥哥,这个应该怎么念?而我,就耐心地笑着,一个
字一个字地慢慢教他读出来。
一个站起来还没凳子高的小小学生,坐在同样是未脱稚气的小小老师怀里,两个人都是一本正经
地一教一学,实在是有点好笑的一个场面,过往的宫女看到了,无不偷偷地掩口窃笑。可是那一
段时光,也实在是很让人怀念……
还记得第一次教小烈骑马的时候,五岁的小烈才到我胸口那么高,踮起了脚尖还摸不到马鞍。我
心爱的‘追云’对他而言简直是个可怕的庞然大物。他心里明明害怕,却硬是咬着牙往马背上爬
,怎么劝他都不肯罢休。最后我只好把他抱在怀里,手把手地教他如何坐稳,如何握缰,如何控
马,带着他在城外四处奔弛,走遍了京城内外的大小山峦。小烈乖乖地依在我怀里,清脆的童稚
笑声洒得漫山都是……
从那以后小烈就爱上了骑马。一年后他已经可以娴熟自若地纵马飞奔。我把伴我多年的“追云”
送给了他,虽然自己心里也不舍得很……
还有,第一次带小烈出门远行,第一次把他带上朝堂,第一次把权力和信任交到他手里……小烈
有太多的第一次都是与我共同经历的,最后的一次就是那场宫变。象以前的无数个第一次一样,
他完成得干净漂亮。
小烈他……从来都是个聪明绝顶的学生呢。可是我又几时教过他背叛?我苦笑着举起手中的酒坛
,仰头痛饮,让火辣辣的烈酒冲淡口中的苦味。然而一口酒直冲入喉,苦味没有丝毫减淡,我的
眼泪却被激辣的酒气呛了出来。
这酒,真的是很烈啊……
背后响起轻轻的足音,在安静的夜风中清晰无比。
你来了?我懒洋洋地问,头也不回地向后扬了扬酒坛。
是拓拔弘,不用回头我也知道。
不是我神机妙算未卜先知,而是这些天来,我早已习惯了他神出鬼没的突然出现。
只要我独自在街上信步闲逛,十九会与他狭路相逢;而我若跟着雷鸣易天去喝酒散心,更是永远
会同他不期而遇。每一次所谓的‘偶遇’,拓拔弘的态度都自然得很,一副若无其事理所当然的
寻常表情。可如果这些都是巧合,那世上的巧合也未免太多了一点。
不能不佩服他‘巧合’的本事。今夜我原本不想见人的,只想抱着只酒坛躲起来一个人喝酒,而
且都躲到这里来了,他居然还能找得到。
真好奇他是不是长了一只狗鼻子。
只是这一次他出现的时机赶得正好。我已经半醉,脑中一片昏昏沉沉,整个人反而出奇的放松,
忘记掉与他针锋相对。
“真巧!居然会在这里碰到你。”我靠着身后的大树,笑嘻嘻地抢先替他说出那句用得烂掉的开
场白。
饶是他脸皮再厚,也被我似嘲似谑似笑非笑的调侃弄得脸色微红,尴尬地停住了脚,站在我身前
一尺之外。
看到他的样子我忍不住轻笑出声。其实我没有多少难为他的意思。不知为什么,虽然我本来只希
望独处,但是却并不讨厌他的到来。不管怎么说他都是我在北燕最熟悉的一个人,经过这么长时
间的朝夕相处,再讨厌的人都会变得有几分亲切。更何况拓拔弘这个人还不算坏,虽然有时候脾
气有点古怪别扭,让人觉得很难伺候,但在他没有存心整人的时候,倒也算得上是个酒中良伴。
“请坐请坐。何必客气?”我拍拍身边的草地,“来来来,我们喝酒。如此良辰,怎能不来个尽
情一醉?”
拓拔弘皱眉,盯着我上下看了两眼,依言在我身边坐下,却按住了我手中半空的酒坛。
“你已经醉了。”他沉声道。
我失笑,一把推开他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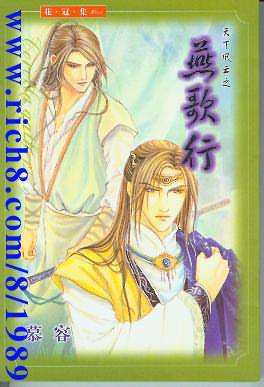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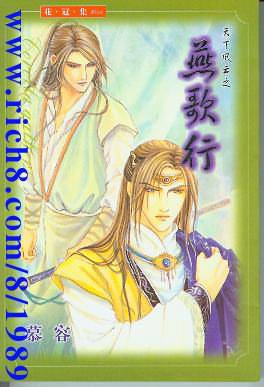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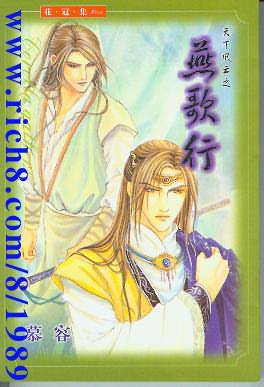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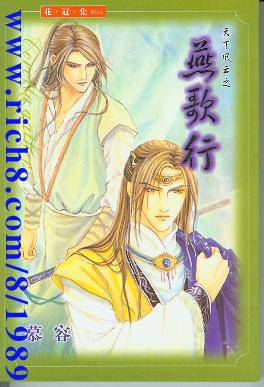

![燕歌行(出书版) 作者:慕容[四册]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