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歌行4-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上乘,即便我不是囚犯而是位客人,也找不出什么可挑剔的。
但是除出物质以外,我的生活却贫乏枯燥一如沙漠,孤寂得令人难以忍耐。
不得不怀疑这是否祁烈刻意安排的精神折磨。如果是,那么祁烈的心机与对我的恨意已远远超出
我的估计。
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四肢被沉重的钢圈牢牢禁锢在床板上,令整个身体无法移动分毫,逐
日逐夜,我只能静静地躺在床上,除了眼睛,只有大脑可以自由地活动。狭小的石室没有窗子,
只要关上厚重的铁门,屋子里就是一片全然的黑暗,没有一丝光亮也没有一点声音,宛如一个死
寂的世界。
几乎令人发疯的死寂和黑暗。
我的忍耐力和意志受到前所未有的巨大考验。
每天早晚两次,那块木头会来为我疗伤涂药,喂药喂食。他的动作机械而有效,表情也一如既往
地平板如石,每次都是安静地来,沉默地走。不管我怎么引逗他开口,始终都不跟我说一句话,
甚至连正眼都不看我一下。
可就连这么古板乏味的一个人,也成了我每天期盼的两个对象之一。
另一个自然就是祁烈。
祁烈和那块木头不同,来来去去从没有半点规律。让人摸不清他会在什么时候突然出现,会呆多
久,又会在什么时候突然离开。
他来的并不频繁,最多每天一次,停留的时间也从不会太久。态度总是骄傲冷淡,鲜少给我什么
好脸色。
可尽管如此,在漫无边际的黑暗和寂寞中,每次看到祁烈冷冰冰的英俊面孔,我仍会不由自主地
眼睛一亮。
没办法。不管祁烈的态度有多冷淡,至少他还肯开口说话,肯理会我漫无目的的回忆、闲聊和偶
尔的提问。在眼下,他已是我唯一可以与之交谈的一个人,也是我获得外界消息的唯一途径,自
然在我心目中身价百倍。
祁烈口中漏出的消息通常只是一鳞半爪,对我却已经弥足珍贵。
只可惜要从他嘴里挖点什么有用的东西实在是困难。
祁烈聪明敏锐,心思缜密,反应快捷且警觉极高,与口无遮拦的乐言可说是天差地别。我常常需
要花上好半天工夫跟他闲扯,甚至要放软了态度小心翼翼地哄他开心,才能偶尔从他嘴里骗出几
句零零星星的消息,其辛苦程度远胜于与敌国的使者大开谈判。
至少那还是摆明车马直来直去,这却要迂回婉转不露痕迹,以免给祁烈看穿我的用心,连这点可
怜的机会都失掉。
有时候甚至要故意装得兴致缺缺,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
“那个东齐的储君直到现在还下落不明,说不定已经淹死在河里了。”
“哦,是吗?那倒是白费了我一番力气……”
……
“萧代向北燕指控你劫持萧冉,朝中闹得沸沸扬扬,北燕王气得下旨严令禁军在全城搜捕你呢。
”
“啊?哦……我才不怕。北燕禁军的本事可比你差得远了。想当初,你满城追拿我的时候啊,那
才是……”
……
“北燕王因病三日不朝。听说他这次病得不轻。到了关键时刻,他这三个儿子争得越发厉害,大
概是快要撕破脸了。”
“是么?那不正是你的机会?你既然来了,怎么也不能空跑一趟吧……”
……
只有一次,祁烈的话终于令我动容。
“听说拓拔弘每晚都会一个人离府外出,莫名其妙地在城里四处乱转。结果被对头抓住机会,在
一处僻静的角落里偷袭得手……”
“什么?!”惊呼出口,我才意识到自己失态地打断了祁烈的话头,连忙换回漠然的表情,轻描
淡写地道,“哦,死了么?”
祁烈不说话,只是冷冷地望着我,目光寒如冰雪。
“终于有让你失控的消息了?拓、拔、弘。看来在你的心目中,他的分量果然重得很。”
“……”我沉默。过了良久,才抬头对上祁烈的眼睛,缓缓道:“绕了半天圈子,你想探听的就
是这个?为什么不索性直接问我,何必要费这么大力气?”
我毕竟还是低估了祁烈。早就该想到,以他的聪明与心机,再加上多年来对我的了解,就算我再
小心谨慎,他又怎么会一直看不出我的意图?怪不得一直都觉得祁烈的口风守得极紧,每次都只
是轻飘飘地一句话点到即止,关键处从来滴水不漏,让人探不到半点机密。
祁烈牵牵唇角,扯出一个微带讥嘲的笑容。
“我看你天天躺在这里也无聊得很,反正闲着没事,何妨陪着你玩玩心思,也免得你脑筋闲久了
会生锈。”
我怔住,一口气差点没呛在喉咙里。原来祁烈耐心地陪着我耗了这么久,根本是一直在存心戏弄
我。他明知道我心急想知道外面的情形,却故意吊着我胃口,时不时漏出只言片语引我上钩,他
好看着我绞尽脑汁的样子自己开心!
也罢。既然一时不慎落于人手,又怎能不任人占尽上风?
只是,我也不能太示弱了。
“是么?”我笑了笑,不紧不慢地道。“难为你煞费苦心地安排了半天,把我放在一间与世隔绝
的屋子里,让我整天与黑暗和寂静为伍,除了你和那块木头就再也接触不到任何人,就只是为了
让我玩得投入一点?我还以为你是为了逼出我的弱点和破绽,好给你造成可乘之机,探听到你想
要的秘密呢。”
祁烈的脸色微微一变,马上又慢慢冷了下来。
“你以为我想探听什么?”
“你说呢?”我静静抬眼,不避不让地看着他。
“且不论合法传承还是篡位,你既然已当上了西秦国主,这传国之秘也不妨让你知道。其实我本
就打算告诉你的,可是现在,我却偏偏不肯说了。”
祁烈的眼神一冷。“为什么?”
“因为……”我一字一字地缓缓道。“要我说出秘密,可以。但必须是我自己心甘情愿。必须是
在彼此对等的关系下,而不是受制于人地被迫说出来!”
我扬一扬眉,丝毫不掩饰自己眼中的坚持与骄傲。
“小烈,你或许有你的手段和办法,我却也有我的原则和尊严。你可以抢走我的王位,也可以拿
走我的性命,可是要让我屈服认输任你摆布,却也没有那么容易。你要想拿到传国玉,想知道西
秦的镇国之秘,除非是在我自由之后。如果你不服气,那也不妨来严刑逼供地试试看!”
祁烈紧紧抿着双唇,修眉微蹙,黑亮的眼中光芒闪动,仿佛有无数纷杂的思绪飞速闪过。他一言
不发地凝视我良久,才极慢极慢地点了点头,道:
“好!不愧是我自小佩服崇拜的大哥,纵然是处境已到了如此地步,依旧不减当年气慨。你既然
把话说到了这个份上,我若是再使出什么狠辣手段来逼你开口,未免让你小看了我。我不会苛待
你,不会对你严刑逼供,可是也绝不会放你自由。咱们不妨便这样慢慢耗着,且看看最后谁先会
低头!至于那些秘密,你不肯说也没关系。我既然能抢得这个位子,便自然有本领坐得稳,守得
住,就算是没有传国玉又怎么样?”
看着祁烈钢铁般坚定无回的决然目光,我心中一凛,不由叹道:
“小烈,你就永远也忘不了跟我赌一口气?你不杀我,又不放我,宁可不要玉不问机密也要硬生
生跟我纠缠上一辈子,这又何苦呢?”
祁烈紧紧凝视着我,闭口不语。过了好一会儿,才道:
“你说我这样对你是为了逼你说出心中的秘密?没错!可是你只猜对了一半。还有另外一样东西
,是我更在意,更想从你身上逼出来的。”
“什么?”我愕然问道。
祁烈不答,目光却始终不离我的脸。优美的双唇紧紧地抿着,深黑的眼睛中神情复杂,看不透其
中隐藏的秘密。
“等到我成功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了。”
直到他起身将要离开的时候,祁烈才淡淡告诉我。
他要的究竟是什么呢?我双眉微蹙,有些困惑地想。我保有的秘密并不多,除去有关王位传承的
那些,真的已不剩下什么了。还有什么珍贵的东西值得祁烈大费周章地逼出来?
眼看着祁烈就要迈出房门,一个在我脑中被压抑了半天的问题终于还是不屈不挠地跳了出来,令
我本能地冲口叫住了他。
“祁烈!”
祁烈停下脚,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顿了一下,突然又迟疑着把那个问题咽回了腹中。
……
祁烈的目光微微一闪,唇边突然浮起一丝难以解读的复杂笑容。
他转过身,不再停留地离开屋子,却在铁门闭拢的前一刻淡淡地丢下一句话。
“放心。他没有死。”
第五章
真应该感谢祁烈的骄傲。
自从他说过那番话后,我的待遇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他果然命人打开了紧紧禁锢我手足的粗重钢
圈,让我终于摆脱了重重桎梏,有机会伸展一下僵硬的肢体。
不知是否因为躺得太久,还是因为受伤未愈,刚一试着起身活动,我只觉全身上下的各处关节酸
痛不已,身子更是软软的不听使唤,竟要扶着床栏才能勉强坐起,更加没力气下床行走了。
当然,祁烈给我的自由极为有限。即便我有力气下床,也走不出这间小小的石室。一根粗大的铁
链仍牢牢地锁在我的左脚上,另一端深深地钉入石墙,将我的活动范围严格地限制在石室之内。
与之相应的是另一副结实沉重的精钢手铐,时时刻刻地束缚着我的双手,就连吃饭睡觉时都从不
摘下来。
我苦笑,一边拨弄着腕间叮当作响的锁链,一边无奈地摇头轻叹。
祁烈总是喜欢高估我,宁可浪费十倍的力气重重防范,也不肯对我稍有放松。难得他这么看得起
我,我真该受宠若惊才是。
其实以那位‘三绝神医’的眼光和本领,肯定能看得出我脉象的异常。拜祁烈的‘蚀骨销魂散’
所赐,我此时的内力还不到正常时的一成,连一个寻常的侍卫都比不上。再加上全身的关节受创
不轻,又曾在重伤之余大量失血,身体的状况可说是糟糕之极。连随便做一点轻微的活动都要喘
息半天,哪里还会有力气逃走?祁烈给我加上这重重束缚,实实在在是多余得很。
幼时的祁烈曾经天真地认为我如神仙般飞天遁地无所不能,该不会他直到现在还保留着这个荒谬
的想法吧?
不过也应该知足了。这副手铐虽然给我的行动带来许多不便,但总比以前那种连动都无法动弹的
处境要强得多。除此之外,祁烈给我的待遇并不刻薄,每日送来的各色用品一应俱全,几乎满足
了我正常生活中的一切所需,包括阅读和娱乐。
除了不能自由行动,我现在的生活几乎与以前在西秦时差不多了。狭小的石室虽不见天日,但是
床头有书,几上有茶,案上有琴,壁间甚至还挂了几幅名家的书画。长日无聊,我至少可以看看
书,下下棋,还可以在养足体力后下床慢慢地散一会儿步,日子倒也过得颇为闲适。如果不是手
脚上有一堆叮当作响的东西时刻提醒着我,我几乎都要忘记掉自己是祈烈的阶下之囚,倒要以为
自己是一位暂时居留的客人呢。
祁烈仍然每天都出现,还是一样的行踪不定,来去如风。从那天之后,他不再提起我们之间的矛
盾与相持,不再对我说起外面的事,更绝口不再提拓拔弘。每次来时,只是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
自若神情,淡淡地与我信口闲谈,偶尔下一局棋,或是聊一聊我手中正读的书卷。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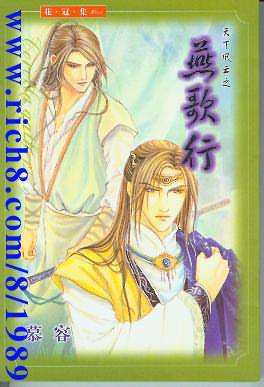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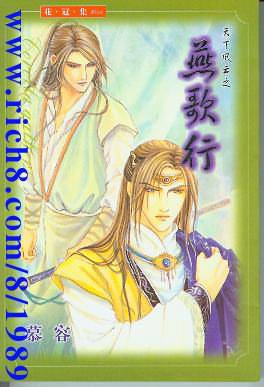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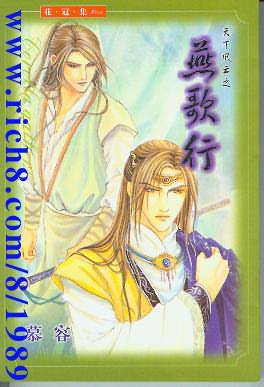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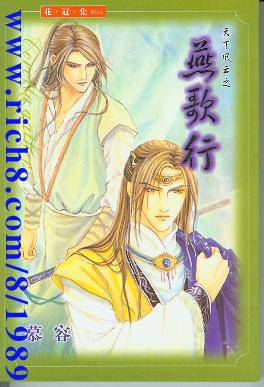

![燕歌行(出书版) 作者:慕容[四册]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