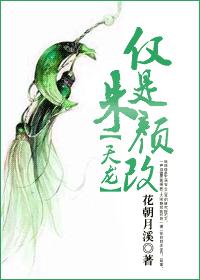凤归云 (天朝女提刑,完结)-第2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臣名在孙山之后,只得奋发图强,二年之后得以应缺崇文馆直学士,充为太子属官。全赖涂大人指引之恩,臣得近太子殿下,臣感激涕零。其后涂大人以太子洗马调任刑部员外郎,外放扬州,臣亦亦步亦趋,得充任一方县令……”
整理一下他的这番话,本朝十五年,应该就是七年前的事情。之后涂某人和他先后入了东宫府,而他又在这位同年的引荐下,确立了“为太子效忠”的伟大理想。而作为主君的太子也给了他们丰厚的回报。
按照碧落官制,明法科与进士科不能同一而论,明法科出身的官员,按照碧落朝惯例,不能充任正五品以上的“高级官员”。涂大人七年之间,从一个正七品上的长史,一直做到从五品上的一州要员,以他的出身而言,已经达到了他权力人生的顶端。冯大人的那个从六品上的京口县令,也算是破格提拔,而且以这上升的势头而言,前途颇为可观。
他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明示我们,涂大人事业上的成功,与他“太子党”的出身密不可分;而这兵器弊案,与涂大人身后的太子,也就密不可分。
我瞄了睿王一眼,他依旧是一派不动如山,绝对当得起我初次见面“神人”二字考语。那冯大人跪在地上,情绪已经平稳了很多,介绍完了相关的背景之后,也终于来到了正题。
“那日涂大人只身到了京口县,他知罪臣与王兄亲厚,王兄为避他们所害,必会投奔于臣,而不会远赴六合。便命臣在他饮食之中,投放此物,一了百了。”冯大人说道:“臣自是不肯,可涂大人向臣示下太傅手令,许他便宜行事之权,臣不能不从。”
“不能不从?他命你伤天害理,你也扑嚎从之?”程潜挑眉,追问道。
“臣投身科考,只望匡世济人,光耀门楣。然东宫蛰伏一年,见太子殿下一面不得。”他抬起头,直视着我们:“臣亦有碧血满腔,如何受得了这般蹉跎?太子殿下乃国之储君,身为人臣者,效力人主,天经地义之事。太子殿下对臣恩重如山,臣三代单传,膝下唯有一子,幸得太子詹事大人提拔,选入太学读书,如此恩德,臣便是粉身碎骨,亦不能报于万一。太子有命,臣自当戮力以赴,不敢有丝毫懈怠。”
果然啊,是个男人,心中都藏着权力欲,而知识分子此心更甚,历经宦海沉寂之后,升迁的机会,就成了不能抗拒的诱惑。这份诱惑,使得他以自己的儿子为质,宁愿受制于人,以良心换取闻达天下的机会。
这真是个不错的故事,让人不得不相信它的真实性。
“酒宴之上,王兄心事重重,酒酣之后,只说回得金陵便去谢府,不能有亏圣恩云云。臣便知道,王兄致仕,实为舍身取义,臣唯有敬之重之,岂忍其为人所害!”他说道:“何况王兄于臣全然信任,若臣加害于他,与禽兽何异?臣痛定思痛,决定以及身维护王兄安危,却不想王兄还是难逃恶人魔掌。”
“于兵器弊案,王兵曹都说过什么?”程潜打断他的话。
“王兄并未说于臣听,想是顾虑臣之安危。毕竟太子殿下——”
“一派胡言,太子殿下乃国之储君,边防事重,他岂有不知,怎能允许此等禄蠹噬我国之根本!”一直沉默着,让程潜代表发言的睿王终于发了话。
“新罗诸镇内附以来,虽有数次谋反之行,然我皇朝之师威武,所到之处,逆贼无不束手。尤其这十年以来,新罗之师,纯备而不用。若非其次突发吐蕃之乱,想必此批辎重已平安过海,为新罗之师所用。”程潜分析道,这段话并未提到那太子殿下半个字,含义却很明显,他也是相信了,这兵器弊案与太子有关。
“这,太子殿下天潢贵胄,臣亦以为,此事定位他人拨弄,与太子殿下无关。只是涂大人手持太子太傅大人手令,却是臣亲眼所见。臣若有半句欺瞒,粉身碎骨。”
他没说的,比说了还厉害。此案凡是他涉及到的人,皆与太子有关。涂大人与他结交,始于太子府中,他儿子的就学问题解决人是太子詹事,他效忠的对象是太子,而涂大人出示的手令,则来自太子太傅——太子的舅父大人。
这细细密密的一张网,太子完全脱不得干系。
“王兄之死,太过蹊跷。臣无能,无法探的王兄死因,便是探得,亦无处可诉。只好将验殓之事草草处置了,并在王兄的鼻中,插了一根铁钉。上呈扬州府的公文,并无漏洞;然在京口县刑房的存证,却是十分潦草。只想着为将来为王兄翻案,埋此伏笔。臣便是死,亦可有颜面去见地下的王兄了。”
说到此处,他再次“动情”哽咽。
这是我迄今为止,听到的条理最清楚,说理最完满的一份供词。栽在这样的人手中,扬州府也不需要喊冤了。
那位冯长史,以一句“臣所述不敢有半句虚言,恳祈殿下明鉴”结束了他的解说。我和程潜都看着睿王,一面是数万将士的死,一面是贵为一国储君的“嫌疑人”,现在的情况,“兹事体大”四个字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
“一派胡言!”睿王说道:“你言下之意,为求功名独子尚可抵京为质,你要本王如何相信,如此不仁之人,肯为朋友之义,将与你有助益诸人,一一出卖?你且告诉本王,如此不仁不义之人,所述种种,如何取信于人?”
对于他所说的一切,睿王并未做任何真伪判断,却指向了对其人格的质疑。这一招指南打北,着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看了一眼程潜,他低着头搬弄着手中的折扇,好像在钻研着那扇骨上的纹路,然而从我这角度看过去,他的唇角微挑,含义暧昧,似有所得。
人精的世界着实让人费解,我的大脑转得发疼,他们却好像什么都知道了。我虽然没明白,但是那位跪着的冯长史,想必是已经心领神会了。他磕了一个头,道:“臣也是个人,如何没有怜子之情,没有自保之心?然而臣自幼读书,亦知春秋大义。臣妻儿身家是小,碧落天下是大,自王兄舍身之后,臣苟活至今,只为将王兄大义,向查案之人和盘托出,如今心愿已了,死而无憾矣!”
说完便洒然起身,飞身向左侧刻着楹联的檀木柱子撞去,肉与实木相碰,发出了沉闷的声音,他身上挂着的玉佩随着身体一起仆倒在地,落在大理石的地板上,让人毛骨悚然的清脆。
睿王没动,程潜亦没有动,他们都有那个本事拦下他,可是不约而同,都坐在原地,无动于衷地看着这一幕上演。他们怀揣着自己的心思,无声的厮杀,小人物的生死,对于他们而言不过是名利场外,上不得台面的游戏罢了。
大朵的血花从他的额头溢出,在我眼前,弥漫成令人窒息的红雾。我从座位上冲下去,按住他的颞浅动脉,然后喊道:
“取干净的软布来,一坛烧酒,越烈越好。”
无论怎么压迫动脉,血还是争先恐后地从我的指缝间溢出来。我万万没想到,他这次的自尽并不是做戏,撞得这么重,脑内伤出血在所难免,以古代的医学设备,就算是最优秀的脑外科专家到此,也只有束手无策,何况半吊子如我!
我的急救还没来得及展开,他便无声无息地咽下最后一口气。就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还是斗不过死神的镰刀。这便是天命吗?
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明明他就是杀死王兵曹的凶手,明明他——难道真的是我看错了人,他竟然以这种玉石俱焚的方式。来捍卫自己最后的真实!又有什么样的剖白,比这一腔碧血更有说服力?真的是我错了吗?
我跪坐在地上,低头看着自己鲜血淋漓的双手。我从来不曾冤枉过任何一个人,这是第一次,我凭借着自己的推理寻找凶嫌却错了方向,本已愧对于他,却到最后也救不了这个被我贴上了罪犯标签的无辜之人!
作者有话要说:谢谢大家的生日祝福,我非常感动,窝心啊。
这个案子很快就告一段落,不能算是不了了之,大家也知道,牵涉到皇储问题的时候,这一整个故事,其实也只是下一个故事的一个大的布石而已。
所以,会有更多的炸弹陆续埋下,陆续引爆,大家期待吧~~
更新完
昨儿和人讨论,被人批评说偶滴文有点太自得其乐了,缺乏和读者之间的互动,会让读者很难进入这个故事。我深刻反省了,可能是和法医的题材和一些审案的手段有关系,一弄上技术流的东西,我就很难把线索全部摆出来,让大家去猜测案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的错,我知道,可是乃们不要因为这样的原因就不爱我了,不要bw我,不要bw我,不要bw我~~
双声子
冯长史的“以身自证”,使得接下来的审案,一路顺风顺水。早被林冲送到行在的现任扬州兵曹亦出庭作证,加上王兵曹以性命保下来的书面证据,一条完整的证据链就此形成。
涂大人见抵赖不得,便以他的如数招供,换取全家人免死。毕竟他在兵器上偷工减料的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碧落刑律中三个株连刑种的一个——“谋叛”,如果一旦定罪,他全家都要陪死。
睿王爽快地和他定下了这个交易。不过那个涂长史也是个乖觉的人,他死活也不肯将话题引到太子身上。据他的说法,这制造伪劣兵器的想法,是出自于他与滕大人。不过为了打通中央确保兵器的流向万无一失,他向太子詹事行贿,求他在中央那边打通关节,至于那份太子太傅的手令,他也一并交了出来,不过他也同时招认,这份手令是太子太傅有私事吩咐他去办,他拿来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
最重要的是,这一切与太子并无关系。
涂大人现在已经升到了五品,也就是说,他已经达到了明法科出身官员的极限。权力上不可能再有进展,他也就把目光转向了如何赚钱这个方面。自古而言,权钱就是一家人,有权这钱自然就来得快了。涂大人需要钱保障他退休后的生活,滕大人需要钱为他的仕途做敲门砖,两人一拍即合,也就有了接下来的一整个计划。
兵器案牵涉到了太子,也就只能止步扬州府,顶多捎上那位太子詹事,再想往下挖掘,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储君是国之根本,既然是根本,就没有那么容易动摇。睿王如果处理不好,反而偷鸡不成蚀把米,这么亏本的生意,腹黑如他,如何肯做!
挖掘这条线,不如跟上滕大人那边钱的流向,说不准能另辟蹊径。只是这一切都不关我的事了,可笑我以法医技术自许,到最后却也不过是指鹿为马罢了。
案件告一段落,我回到行在里自己的房间,洗去一身的血腥,我躺在床上,懒懒的没有半丝力气,连晚餐都是阿恒为我端进来的。
相比前两日,他的脚步轻快了许多,应该是父亲的案子得以突破的关系。虽然他并不知晓事情的真相,好在杀他父亲的主谋已经落网,那具体执行之人,想必在细节上稍加审理,很快便会水落石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