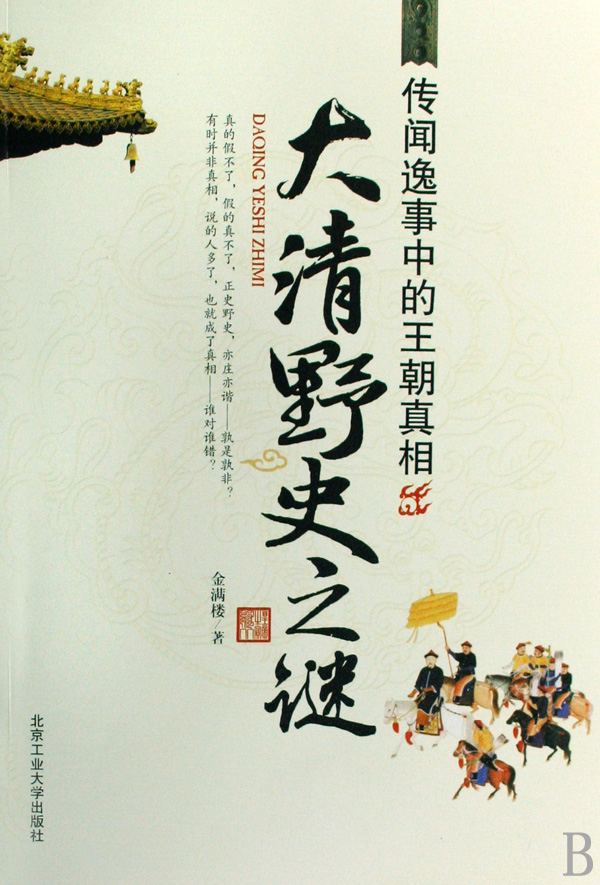����������(�ص��幬)-��4����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Ҵ�Ȥ����������Ҫ���ң���һ����һ������ѩ�ӹ�ȥ�������������ţ�һ���Ϻȣ���һ��ȥ������û�й�أ���һ�����ж�״��̫��ݺݵذ����Ƶ�һ�ߣ����������������ͻ�ع��£����缪�飡����̧ͷһ������������λ��������˧���ɵ���ֻ��һ��ѻ��ɫ���ӣ����ִ�����ӣ����������������������������Σ����ߵ������ص������ף���һ˫�ڶб�Ь����������죬��û��ñ�ӡ��������������Ѳ���Ҫ��ֻ�������������ѵߵ����������������ܼ����ֲ���������Ĵ���ʿ���ն��������ݿ�����˵�����Ǹ������ӣ��ֲŻ����磬�����������������¡������ĵ����̲�ס���������ʡ����������˻��գ��Ͻ������½ţ��Żع�������æ������һ�㸣�¼���
�������Լ�Ǽ���������һ������ˮ���ʵĻ���Ů�������Ŀ���������ֻһɨ����Ȼ�������˵�����㻹�����������˵����ҡ��������������ˣ���������Ҳ��Ҫ���ˣ�����æһ������ȥ��������һ������Ϊ����˭����������òʤ�˰����Ŵ�û���������Ů�˼�������˫���Ҷ������Һô����ִ�ȥ�ģ�����û��������������ֻ������еĺ�����������Ҳ�Ǽ�����������������ô�����𣿴�Լ�ҵIJ�м���������ϣ������ɫһ�䣬����û�뵽��Ȼ��С��Ů��������ֱ���ɡ��һ�æ����ͷ������ֻ��ģ����ˣ������Ĵ�����ŭ�����һ��뱣סС�������������̫���ء�����������Ȼ�к��ڱ�����������ʱ��·���˺ܾã���ʵֻ��һ˲���絭Ȼ��������ȥ�ɡ��������ɴ��������ҵ��ܿ�������ɨѩʱ�һ�أ�Բ������������Ϊ����һ�����û�ȥ�����ѣ��ɰ������������
������һҹ˯����̤ʵ�������ǰ���ɨѩ���ˣ�һ����������ⶼ���ˡ�����������Ȼ�μ����ˣ�������ò����Ů����ռ�ȶ��ģ��ֲ���������ô����ȥ���ݡ�ֻ����ƽͷ�����ȱ�˵��һӡ��ò��ã�ֻ��ӡ����û�ж��ѽ�������������������ǣ��Ǻǣ������һ��������Ů���ģ���������������Ҳ�����á��������벻����ӡ���ѡ���ϧ��������ʲôϸ�ڶ����ǵ��ˣ�ֻ��ϡ����ô����Ӱ��ģ���úܡ�
�����������ڴ�����˰�����ϸ���Լ��⼸������Щ�����ģ�ԭ������һ��̫�����������廨��ͷ������ô�������ˣ���Ȼ��Ū��һ��˯�����ﶼ�����ˡ���״�����Ǻǣ���Ȼ�͡���¥�Ρ���д�������������ɣ���Ҳ̫�������㲢û��ʲô�뷨�����������е���ң����������������ƺ����е���ң��������壬��Ȼ���ҵ�ɨ�����Ķ����ò�ʹ�졣��һ�������ţ�����ν��������Ů���˰�������������������ʲô�����⼸�꾹��˼ά��ʽ������Ŵ���Ӱ���ˣ�ֻ��û�����챳����Ů��������Ů��֮��ġ�
��������˼�����ţ������ˮ���������һ�ɵ�������Ƕ���Ц������������ˣ�ƽ�ն������һ�̲ŻŻ�������������ᵹ�����������ⷢ����ǰ��ˮ����˵�㵹����һ��������ֳ�ʲô���ˣ���
���������¡�������������ϡ�㰵��
����������ʵʵ�������ȥɨ�أ�Ŭ���ظ���Լ����ٺ�˼�����ˣ��ú����Ը������°ɣ����ҹ�ʹ��������ͷ��������͵�ʲô��������������ʲô����ȥ�룬���ٿ��Եõ�һʱ������̫ƽ��
��������ƽ���ع��ţ�������ǧ���ټƵ�Ҫ�����ǵĴ̣����ǽ�С���ؾ����������ƣ����ľ�ƣ�������ҵ����ʱ��������Ҳ�¾��������֣���Ȼ�㲻����ô�õ�Ҳ���г�����һ��С�������ܼ����ˡ������ʱΪ˽�Դ��Ż������ù�һ�ٺ��������������������ʮ�ֻ������������Ƿ�����ҷ����Ŵ�ʹ���ڷ����֡�ͬʱ���������֮����Ҳ֪������¶����������ߣ����жԲߵģ����粻��˽�ഫ�ݣ�������ɵ����ô��Ŀ�ŵ�������Ҹ��˾������Ϣ����������������ߣ�һ���ؿ������⻥ͨ��
��������һ�������ͨ�����ֹ�ϵ���Ҵ����˵�����Ϣ������������ܲ����һ��Ϊ����ʵ�����������ѹ�������õ�������������ᣬ���´�ͨ��ֻ�����бܲ���������֮�֡�����������С���ң�������ʲô�취�أ���ʵ���DZƵ��������������ɣ��������������ķ��ǣ����˲��ð������⼸����Ҳû����˼���ˣ�����ֻ�������ټ��·��������ǿ���������ʳ��Ҫ�����ڵ����һ���
�������ղ�¯���ϲ����ҵİ࣬���û���ɨ���أ������ܵ��������·������������ǰ���ʮ���������Ҳ�벻�������������⳯�������кεº��ܿ���ȥӰ�졢ȥ�ı䣬��Ը�ĸ��Ȼ�Ӵ���ʱ�䲢���������Ҷ��������������أ�����������������ȴһ��æ���ﲻ�ϣ��⼸���Ҷ�û˯�ã������ܵ������¡�
������һ�������ϴ�ư�棬����һ�أ����ø������һ�һ�أ�����ȥȥ����ôһ�䡰ȴ�������ø�������Ÿ�ĸ������ô�ã����������е�ʲô�����̶̵��£����������Դ����������Ų���һ������̾���������˰��գ��ȶ����ˣ�����������ȥ�ŷ��ֺ���Ļ��������˸��ˣ�ȴ��ǰ����ʶ���Ǹ�Ӧ�ӡ�
��������������Ц��������������ˣ������㷴�����ǡ�Ϊ����ʫǿ˵���СС��ͣ�����ô���̾�ģ������Ǹ�������Ϊ�����ˣ�����������û�õ��ˣ������������������������ĵ�٩��ֱ����֦�ӵ�����ǰ��������С����ʲô����������������������ǰ���־��������ʣ���˭��С���������ˣ���
������һ�������������ҵıǼ⣬���ŵõ���һ������������������һ�����Ŵ��Ƶ����ҵ���ǰ��ԭ����û����ϸ���������ŷ�������Ȳ��ϴ����ǿ����������ȴ�����㣬ü�������һ�η�ǡ����������Ǹ�ʱ������ʵ��ʮ���꣬������ôҲ��ʮ���˰ɣ��Ҳ�����ͷ����������Ҳ������˼�������൹��һ����û���һ��Ż����ŵ�˵�������ٸÿ��˰ɣ������ҿ�һ�ۻ���������δ�����Ļ�ѩ�̲�ס��Ц�������������أ���Ҫ�ȵ�ĺ���ɡ�����һ�����Σ�ֻ��������������Ŀ�����ǣ��ǣ���õ�ʢ�IJſ��ú��ء����ҵ���������ν�������ٹ���ľ����������������ʱ�����ء�����ͻ��һ����Ц��������Ҷ��������������ˡ�����Ȼû������
������֪���ڴ�Ȥ�ң�Ҳû�����������ֻ���ȱ����£���һ��ûһ�µ����ŻҺ�ɫ�����پ��������Ҳ�˵����Ҳվ�����ʣ���ÿ�μ��㶼��дд�����ģ��������ɣ��������ǽ�����ڶ����������Ҷ�����£������������ƵĻ�æ����û����飬ֻ�ִ�ʶ�ü����֡�����ֻ���ú�Ц�����㲻���µģ���ʵʶ��Ҳûʲô���ã���ɵɵ�����IJ��鷳�ء����ֵ����������Ǽ��������ģ�������˵���ҵ�ʹ�����뵽�����Ϸ��Ҳ���������Ȧ����Ȼ���Dz�������������ĸ�������Ǹ�ʱ������Ҳֻ�����������˰������ɵó��������˵���������������ŭ�ݣ����������þ����ҵ�����˽���ˣ���˵ã���һ�������ŵ���̬������˼��������
������ʱ���һ����Ѱ�ң������ƾ��ѹ�������ȥ�ˡ�������������ʣ�������˭��������һ�߸���������һ�ߵ������Ǹ�������ˡ������Խ������ȥ���Ǹ��������ֿ�������̾�����������Ȼ�Dz�ͬ�������˶������������������Ǹ����ƣ�ֻ��Ѱ����үҲ�Ȳ���ȥ��������������ͷ�ϵ�һ�£����ֻ�˵�գ�����������������ļ����ˡ���
����������һ���������������£�һ�߸������Ǽ���������ˮ��һ�����ϵõ�С̫���ܹ�������������ͩ�ɡ�����ãȻ�ص��ͷ�������������ң����������û�£����²�����ˣ�ԭ��ԩ���ġ���˵����ܿ��ˡ�
�����Ҿ�ϲ���ӣ�����������£����ر���һ����Ϥ���������������ɲ�����������ˮ�ģ������㷢�ʱ�ͽ����ˣ�����������������������ͷһ������Ӧ�ӣ������������֣����߹�ȥ����Ц�ţ���֪�����ⶬ���¶ȵͣ�ʪ���ִ��Dz��Ҷཽˮ�ģ�һʱ�����ˣ����ִ�Ȥ�ҡ�����Ц����������ô���ֿ���Ц�ģ�������ʱ������һ��ʯͷ��أ�������ã�һʱ����ץ�����ˣ�����������ɩ������·�����ȥ��߶߶�������Լ���������˼�ˣ�˵�����㷳�˰ɡ���̧ͷһ�ƣ������������۵ij谮�����۹�������һ�����������������ߣ���һʱ��Щʧ���ˡ�����ô��Ŀ��ԣ��·��кܶ���ַ·�ʲô������˵��
������֪�����˶�ã�Ҳ��ֻ��һ˲�������Ǹ�̫��������������������ү����һʱ�������龰�е��Ȼ���������߽������ǧ��������������˵�˾�ʲô������Żع��������q��������ͷȫȻ���ҿ����������������������ˣ������������㡣��
�����ڰ��¡������ϴ���������
����Ӧ�����ߺ�Զ���һ�����Ƕ�������أ������������ֹ��ֱ����������ҡ���ԶԶ�ľͿ�ʼ��Թ������ô˵ȥ���������վͲ�����Ӱ�ˣ���ȥ�����ټ���Ҳ�Ҳ��ţ�����Է��أ��ֶ㵽������ˡ����߽����Ƽ���ֻ��һ������ѽ������ô��ô�졣���������������̰����Dz��������ˣ��ҿ����⼸�ն������ڣ����շ����������̾�ģ�Ҫ��ʵʵ���ڵ��Ҹ�������ơ���������һ����ף�ȷʵ���������̡�����ֻ˵û�£��Ժ������ȥ�Է���������ˮ���������ҵIJ������������������������ˣ����������Ǵβ���������һ��ð������գ����յ�������������
������һ������˼����ǧ����˯���ر�̤ʵ�������½�����Һ��Ǹ��ˣ������ȥ�������ϣ�����ͩ�����ǽ�����ʮ�����Ů������Ҫ�������ˣ���������ϣ�����ž۵ġ�Ӧ��Ҳ����˼ǰ�������Ŀ������д�����������ʧ���ҰѴӵ�һ�μ������������ϸϸ����һ����һ�Σ����о������������ۣ���12�µĺ�ҹ����ů���ҡ�
�������վ�˵�˰������������������ߺ�����������ã���ϼ����������ȥ���������ʹ������ȥ�������˵�������������ˣ����ܲ��ܴ����ƴ��ӡ��ҳ�����·�����ߵ�С���ſڣ�б��������������һ����ԭ����Ӧ�ӡ�����һ��ź��ɫ�Ŀ������ӣ�����ɫб�����ף����������Ű˱��Ż��İ��ƣ��������������һ�㣬վ������ǰֻ��ɵ�㶵�Ц��
�����Ҽ���һ�����ż��ں�Ƥ���֣�һ�ֱ��ں��棬�������������������ģ�ָ����һ�����Ҫ��ѩ�����ˣ��㵹���˶��֡�����������˼���������ȴ��ŵģ��������һ·�������˲��ѵġ���Ȼ�����������ܴ������ó�����ͭɫ����������е����������ϡ�������ơ����þ�û��������Ķ����ˣ���һ�ѽӹ����Ϻ÷�����һ��Сҹ���ƴӺ������ʳ���һ�㣬��ô��������ְ��������Ļ�ϲ̧ͷȴ���������ɵ�Ŀ�⣺������ô������������Ҳ�Ū�ź��ӱߵİ��֣����У�����˭����ģ���
�������ų����ұ���������ˣ�����300����ǰ���������й�Ȼ�Ǹ���ϡ������������ֲ���Ӧ�������ı��顣���������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