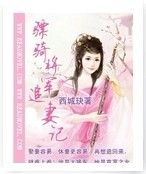骠骑行,霍去病-第8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离乱之苦的人,才能唱出这震魂摄魄的曲子。
古代的三秦大地,北有匈奴、南有强国,历来就是兵家战乱频多之处。
秦腔是这里受尽苦难的人们为抒郁解愤而创作出来的乐曲,这种曲调压抑着千年的悲,万年的苦,声声调调都是在乱风中吼出来地,所以。秦腔又叫“乱吼”。
陈大娘在寂静的山顶哀声咏唱:“……残月冷勾卷旌旗,朔漠静云凝如磐……”
随着那气韵深长的一拍三叹,我眼前地宁静月色渐渐褪去。河西草原的记忆浓浓而来。
霜动飞星恨,云沉万里平。我仿佛又看到了河西草原上千里红绸。万乘铁骑。残缺地月光在空中闪烁,寂冷的星空下,是汉家男儿那如山气概,催动得红绸战旗飘飘不止。
盔甲下,战士们的脸面五官是模糊的。他们的表情又是如此清晰而肯定,那就是踏破强虏、开拓疆土地万丈豪情。
那乱吼的秦腔之声沙哑而不低沉,铿锵有力的声音,一句句描述着河西大漠上最雄伟的黑鹰,最骄傲的军队。
“铁弩钢刀战马动,三军齐喝列阵前。
怒箭骄马奔雷霆,匈奴弯刀尽等闲。
汉家猛士群如麻哪——万里奔驰杀声一动破长天!”
这三句秦腔一句比一句高昂,最后一句嘹亮高亢,浑如利剑横荡苍穹。我听到无数夜林惊鸟扑簌簌地从安歇的树林子里飞奔出来,将这平静的夜晚泼溅出绚烂浓烈的光彩。
我好似置身在期门军那数千铁骑中间,以训练了无数次的简单而有力地动作。一遍又一遍冲垮敌人的如山壁垒,如水凶潮。
不知何时。我的手与去病地手又握在了一处。我的手指不由自主握紧了,仿佛握紧地不是他地手。而是战马上那厚沉的马缰绳。
我地内心听得气血翻涌,无法自持,只恨不能再次回到千军万马之中,用自己的双手操纵着胯下的战马,将那些敌寇的生命尽数践踏在脚下!置身这样的队伍,再冰冷的血脉也会炙热,再胆怯的心灵也会坚强无比,军功与胜利是一切辉煌的源泉,是一切荣耀的象征,是一切人生追求的宏伟目标!
正当我热血沸腾的时候,忽然,那乱吼的声音窒然一低,化作黑暗沉底的“苦调”。这突如其来的苦调长得令人哀伤,长得让我满眼酸痛,恨意衔喉,凄苦难言。
我的满腔豪情顿时被这秦腔苦调滞压得喘不过气来,如同在翻腾的热血上陡然压下一块巨冰。
那陈大娘用这样的调子,苦苦唱道:
“扶杖久立城墙上,儿可知?为娘我散发披头霜满肩。
不求功名与高官,只盼着,我儿征途一路走平川……走平川呀……春夜寒水浸冷骨,征衣薄厚牵住了娘心肝。
东家买线西家借梭,织衣坐在了家门槛。”
苦调又长又哀,气噎声断,歌声中,我仿佛看到那老母亲的白发已经枯白凌乱地无法梳理光滑,她的眼睛早已红丝密布,无法看清近处的东西。可是她依然要为自己的孩子一针一线密密缝织出一件征衣。多钉一针,她的孩儿便多一份温暖,多打一个结,她的孩儿便多一份牢固。
她一心盼着,自己的针线活儿保佑着她的孩子,莫要被冰冷的焉支山春水冻着。
那陈大娘的声音一字一句,如嘱如诉,仿佛豆灯下一个扶摇的孤苦身影。耳中,那秦腔苦调变成了平缓的述说。
“陇西捷报,喜讯传。
都说是,将军运兵神无敌。
红旗曼舞战鼓擂。
谁看见,豆灯如泪银针穿?”
我的心中松了口气,战事结束了。这述说平静如水,如涓涓细流,如淡淡轻云,“将军运兵神无敌”,“陇西”?
我感到了霍去病的手掌紧紧地握成一团。我放松自己的手掌,任他将我的手握得生疼,一种不祥的预感渐渐升上心头。我这才听出,那慢板述说的声音,仿佛一团即将熊熊燃烧的闷火,正在酝酿着最灿烂的爆炸。
果然!音域突然拔高——
直惊九霄云外!
“泣望西北,留不住啊——
亲子骨血葬入了弱水边!
扪干老泪,滴滴化血渗灰棉。
枯手握梭,缝成儿衣声声唤啊。”一声声长嚎几欲撕裂长空,仿佛一枚箭头射穿了天幕,我只觉得心口似乎被划了条口子,说不出是疼还是烫。
苍天哪,你睁睁眼,你看到没有?她辛苦织成了征衣,却再也没有人来穿!大地哪,你抬抬眼,你看到没有?她辛苦编织出了温暖,却连儿子的一把寒骨也无法摸到。
她的声音已经拉扯到最高音,我几乎以为她的声音就要撕破了……她已经不能再让声音高拔起来了……
可是——
我、错、了!
那陈大娘的声音毫无顾忌地高高拔起,何止要将天幕撕裂,她是在将自己的心肺一起撕裂啊!
“秦关旧月今又返照渭水边,
娘的儿呀,你的魂灵莫要停留在天山!
万军西出只见千军回长安,娘的儿呀,你的魂灵是否跟回了黄河岸?”
她的声音如同披头散发的厉鬼,撕心裂胆地站在满月下嚎叫。她仿佛在招魂,仿佛在哭灵,更仿佛在控诉生命的无常,战争的残酷。她就这样,一声声呼唤着那远去的亲人灵魂,一遍又一遍。
唤魂的声音重复着,让老母亲的悲痛不断深化,犹如锋利的刀刃,穿透了听者的耳膜,也穿透了听者的心灵。
那呼唤在空中痛苦着,挣扎着,慢慢停止了。
于是,四野寂静,万山无言。那寂静令人双目发黑,我的心如同被砸出一个大洞,大洞又深又黑,却没有鲜血流出……
过了许久,那高高的山顶上,陈大娘仿佛幽灵重生一般,又骤然爆发出一声哭喊——“十八句秦腔句句乱吼,吼破了喉咙换不来儿平安!
十八句秦腔声声乱吼,吼断了肝肠换不来儿平安!……
这硬生生的吼叫,将一切全部重新牢牢揪死了!这哭喊声已然声嘶力竭,已然痛哀到了骨头里。
“十八句秦腔句句乱吼,吼破了喉咙换不来儿平安!
十八句秦腔声声乱吼,吼断了肝肠换不来儿平安!……”
这哭喊声山谷回荡,大音流淌,撞出如波的回声……
“……十八句秦腔句句乱吼,吼破了喉咙换不来儿平安!
十八句秦腔声声乱吼,吼断了肝肠换不来儿平安……”
这哭声终于渐哀渐远,与空谷回音融合在一处,终于,化入群山消失在了这个滚滚红尘中。
我的想象中再也没有了热血沸滚的激血豪情,再也没有了胜利欢呼的连绵旌旗,再也没有了大鼓擂动的欢庆战歌。
我的面前,只剩下了绡冰般的冷月。
冷月下,是一个踽踽独行的苍老妇人。她浑身素缟,满身的凄凉。她心血已经泣干,泪水已经流完,一条喉咙也在乱吼的秦腔中间撕得沙哑。
她撒手站在人间,她已经一无所有了。她如同一张挂在人间的纸符,随便什么风都能将她吹散。可是,她站在那里,什么文治武功,什么千年霸业,它们都在这年迈的老母亲面前,在这份破裂的亲情面前黯然失色,裂成碎片,仿佛一片片暗灰的纸蝶在空中飘舞。
这,才是战争最真实的面目。
这,就是生命最原始的控诉!面对着这些发自肺腑的苦苦呐喊,踏破祁连的功名算什么?一统江山的豪情算什么?
问长天逆海,
生命沉浮,孰轻孰重?
番外(第二部完结)
长安城外,一片梧桐黄叶飘飘荡荡而起,从长乐宫的耿耿灯火前掠过,悄然划入重楼蔓宇的北阙高台。
黄叶一路无声,轻入芙蓉暖帐下,随风打一个半旋,停落在一双描朱木屐旁。
“来人,关窗。”皇帝刘彻威严的声音从柔软的寝帐中传来,立刻有小黄门碎步上前,轻轻拉起窗棂,无声地合上窗闸。外面更鼓响过,是上早朝的时间了。
刘彻翻开锦浪,站起来。
李夫人随他站了起来,她只着薄纱,娇妍动人的身体在那蝉翼般的轻纱下尤显婉转妩媚。
一行宫女走上前来服侍,皇上穿上了高贵的天子之服衮。
日月星辰的刺绣因他的威武双眉而沾染灵气;金丝风革带在他的腰间,如初生之日一般光辉四射;李夫人亲自为他戴上冠冕,那十二真珠在他宽阔的额前晃荡,他气霸天下的锋芒因此略有收敛……
李夫人忽然感到自己的美色似乎尚不能与这身皇冕贵服相媲美,她侧过头,在烛光照耀的铜镜中略看了看自己的鬓发是否蓬松。
这个男子,江山美人是他心中从不须作迟疑的选择。她的手中握着哥哥广利请官书,昨日李广利在建章营的骑射赛中拔了头筹,希望在期门军中找一个事情做。
可是,现在,河西的“那个人”如今锋芒四射,其光彩无人能够抢夺。李夫人缓缓捏紧了手中的竹简,她昨日权衡了一夜。还是决定这个事情暂时压下去。
“皇上,今晚臣妾在此为您备香茶。”言外之意,皇上今晚再来她的宫殿中。宠幸如她。恩爱如斯,对于下一个夜晚。也只能是谨慎无痕的暗示。
“哦。”皇帝淡淡说完,走出去了。
“皇上——摆驾未央宫——”小黄门那阉人特有地公鸭嗓子响起,一声声传出长乐宫,金碧辉煌的龙辇已经来到了十二汉白玉的台阶前。
刘彻遥望宫殿地西北角,河西的战报已经到了长安。他终于又一次赌赢了河西此战。子之赢,满盘皆活,刘彻地眉宇间拧出一份带着杀气的坚定:“漠北……”
李夫人目送那缠金龙绕璧兽的宽长龙辇离开了视线,宫女将她扶起。回到了长乐殿,她转过身屏退左右:“长门宫的那个女子……真的是……”
“回夫人,确实是废后陈娇。”一名穿黑纱地执事宦官轻声回禀。
“公主,仲卿要出发了。”卫将军金冠束发,铁甲为锁、连云结绕,红底滚黑水纹边的披风服帖地贴在身上。
平阳掠起一丝长发。靠在滚金濯云绣的锦垫上:“知道了。”
今日,卫青轮到去长安城外的虎贲营执勤,要有一个来月不会回家。大汉朝边关事急。将领们很少呆在家中的。
卫青站起来,他非常注意地趋步后退。到了门口才慢慢转过来。有使女上前打开门帘。
一阵初秋的凉风带着长安城的落叶吹入卧房,丹枫画屏微微颤动。
“仲卿!”平阳叫住了他。“公主。什么事情?”卫青立刻回过身,头微微低着,细心地提示使女合上门帘。
平阳公主似乎有话要说,双目盈盈欲滴了许久,吐出一口气:“去病……什么时候回朝?”
“最多十天。”
“仲卿,我们结为夫妻多少年了。”
卫青困惑地抬起头,平阳叹了一声:“快些去军营吧,在这样下去,去病怕会将你的风光都夺去了呢。”
“是。”
“是,是,是!你只会说是吗?!”公主忽然发怒了。
卫青站直身躯,自元朔五年在三军阵前,长安城外被皇上亲封为大将军之后,便被这位曾经的故主平阳公主择为夫婿。他对这位公主尊敬有加,爱护也有加,可是,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