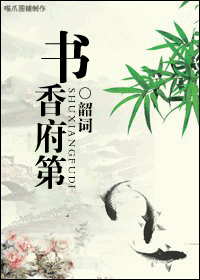书香府第-第8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店家,钱在桌上,替我在你爷爷坟上上柱香,我们走了!”张三听到声音,走回前店,只见桌上竟立着一枚银锭,掂掂分量,足有一两重,抵了一百碗的豆腐脑还不止,张三有些结巴,小本经营,他没钱找啊!
“客,客人……我,我没零钱啊……”张三赶忙探出身去,朝店外看去,可眼前街上空无一人,哪还有老两口的影子。张三揉了揉眼睛,再仔细一看,没错,银子还是银子,难道爷爷显灵,天上掉馅饼了?
谢老爷子夫妻俩背着个小布包,不带一人,轻装出了京城,城门在“吱呀”声中缓缓大开,老爷子拉着老夫人的手,两人一步一步走出城门。
老夫人回过头,深深看了一眼待了数十年的京城,将那砖墙青瓦、巍峨城楼一一映入心底,老爷子紧了紧握着她的手,眼里不乏忧虑,老夫人笑了笑,指着城楼说道,“四十年前你带着我就是打这扇门进的城,今个儿这扇门又见证了我们出城,可算是有始有终了。”
老爷子笑着拉住老夫人的手,两人相视而笑,一同往着远处走去。四十年前,青春年华,夫妻同心;四十年后,岁月静好,白首不离。
约莫半个时辰后,街上渐渐有了些人影,张三赚了笔大生意,逢人便露出笑脸,心情大好。这会儿他正舀着豆腐脑呢,街上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张三好奇的探出脑袋向外张望,一大早的哪家姑娘又私奔了,如今府里家丁寻人来了?
不远处几匹骏马奔驰而来,为首的是一位穿宝蓝色直裰的贵族少爷,他神色慌张,急急勒住了马匹,翻身下马朝着街上唯一开门的张记走来。
“打扰了店家,请问你见过我家老爷太太么?一对约莫七十许的老夫妻,老爷子这般高,人挺精神,老太太微胖,人很和蔼。”谢尚翊朝张三比划了一阵,紧张的看向店家。
张三一下就想到早上的财神爷,忙不迭的点头,并指明了方向,谢尚翊拱手相谢,翻上马,朝城外飞驰而去。
张三疑惑的摸了摸下巴,朝周围人问道,“这是哪家的公子,这般客气?”
店里一客人瞅了一眼,喝着豆腐脑含糊的说道,“这不是前几天被圣上削成三等伯的平鎏侯府小公子么?”老百姓喊了几十年平鎏侯,那些子书级官位他们懒得搭理,按着习惯继续管谢家叫平鎏侯。
张三嘴巴都合不拢了,没听错的话那小公子打听的人是他家老爷和太太,那不就是——平鎏侯夫妇么?侯爷和夫人吃了他做的豆腐脑?!娘类,我是不是烧糊涂了……
纵是谢尚翊策马狂追,可谢老爷子行伍出身,过的桥比孙子走的路还多,反追踪技术那是杠杠的,谢尚翊追了一整天都没找到祖父祖母,一脸气馁的回了伯爵府。府里的那些密探他指使不动,平素交好的那些公子少爷自从平鎏侯府落了难,不落井下石就是厚道了,雪中送炭简直就是白日做梦。谢尚翊此刻才觉得自己往日里错的有多离谱,剥去了侯府世孙的身份,没了权势的护航,他什么都不是!
谢尚翊心里千般痛苦,万般焦心,祖父和祖母信上说是故地重游,可那故地却是西北边关战乱之地,七十岁的老人,且不说刀剑无眼的战场,就是这一路长途跋涉的劳苦随时都能要了两老的性命!明眼人都清楚,这是拿自己的命为谢家换忠臣之名!
垂垂老矣的祖父母仍在为谢家付出一切,而他一个男子汉却龟缩府中无能为力,这种一无是处的感受凌迟着谢尚翊的心,祖父母生死不明,爹娘流放千里,妹妹孤若无依,他必须打起精神,鼓起勇气,撑起这个摇摇欲坠的家!
“少爷,少爷……”谢尚翊刚回伯爵府,一名小厮便急急跑了出来,他上气不接下气的喘道,“长信伯派了人来……说,说要推迟大小姐的婚事,冰人正在堂里候着呢。”
谢尚翊一个咀咧,险些站不稳,他牢牢扶着一旁的门柱站直了身子,死死盯着那小厮问道,“你说什么?!”
那小厮抖着嗓子又说了一遍,谢尚翊只觉天旋地转,他咬紧牙关,条理清晰,一条一条吩咐道,“去,让那冰人候着,说我一会儿就到。吩咐人去长信伯家打听清楚,别是传错了消息。再使人去孟家请姑母前来,务必要请姑母亲自前来!快去!”
小厮连连答应,弓着身子刚要往外头走,谢尚翊又喊住他,“这事儿,大小姐知道了么?”
小厮眼神躲闪,支支吾吾的回道,“大小姐亲自接待的冰人……”
谢尚翊最后一丝希望也落了空,他无力的挥挥手,让小厮退下,转身便往同璧屋里走去。他轻轻敲了敲门,却无人应声,尚翊推开屋门,往里头走去,却见妹妹斜靠在美人榻上,眼神木然,脸上泪痕斑驳。
“同璧。”谢尚翊放轻了声音喊她,谢同壁愣愣地抬起眼看着哥哥,眼里倒影着谢尚翊的身影,仿佛这是她最后的希望。
谢尚翊心头一酸,他的妹妹自小千疼万宠的长大,何尝受过此等委屈,他吸了吸鼻子,把同璧搂到怀里,安慰道,“同璧不怕,有哥哥在,谁也欺负不得你去。”
谢同壁靠在哥哥怀中泪水一行一行滑落,她哽咽着问道,“哥,我们做错了什么,上天要这样惩罚我们?哥……”
谢尚翊不知该如何回答,他只得搂紧了妹妹,咬牙发誓,“若真有报应真有惩罚,我谢尚翊一人担了就是,谁也害不得我妹妹!”
宜珈接到谢家的求救信,心里蓦地一凉,世事无常,世态炎凉,这句话她在短短几月内竟经历了数次!她折好信,略整衣冠,便往谢氏院子走去,路上眼泪不听使唤的滴落下来。外祖母的笑容她还记忆深刻,她明明说过,会和外公一道儿看她长大成人,儿孙满堂,一转眼却背上行囊独自离去。宜珈心里知道,战死沙场、马革裹尸是谢湛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她也知道,一个为国为民而死的祖辈的分量和名望对于谢湛的子孙来说,远远高于一个破败伯爵府安享天年的伯爵。谢家倒了,谢湛便用鲜血和性命重新把这个家个扶起来,他要给子孙后代一个荣耀骄傲的身份!知道这一切才更令宜珈悲痛,她不愿自己未来的幸福建立在祖父母的牺牲之上!
谢氏静静的听完了一切,冷静的吩咐下人为她换上衣衫,带上宜珈和一众丫鬟浩浩汤汤往谢家前去。一路上,谢氏沉默寡言,宜珈紧紧握着母亲的手,谢氏身子仍未大好,宜珈心里既牵挂着祖父母,又担心谢氏的身体,两番交割万分难受。
伯爵府正堂里,冰人刘婆子正和谢尚翊唇枪舌剑,谢尚翊不过一个温润书生,很快便不敌脸皮赛过城墙的刘婆子,气得尚翊脸色发白,话都说不出来。
“哎呦,我说谢家小公子呐,这婚姻大事,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一没娶亲的公子哥跟着瞎掺乎什么劲?!”
刘婆子朝尚翊挥着帕子,嘲笑道。全京城的人都知道谢家父母流放伊犁,这会儿不知在哪条路上走着呢,恰巧老爷子夫妇也不在,如今谢家一盘散沙,又有长信伯在背后支持,刘婆子胆子大了去了。
谢尚翊气得发抖,骂道,“无知妇人,你难道不知长兄如父么?”
刘婆子斜眼腻了他一眼,嗤笑道,“婆子我是没读过什么书,但也知道这话说的是没了爹妈的孩子,莫不是谢公子在咒自家老子娘?哎呦喂,难怪谢家现在没人咯,当年平鎏侯府多大的名头哦,说出去谁不敬三分,如今,啧啧啧……”刘婆子配合的上上下下扫了谢尚翊几眼,一脸鄙夷的神情只有好不是睁眼瞎谁都一目了然。
“谁说谢家没人了?!”沉重的女声从刘婆子身后传来,刘婆子转过身,笑容还来不及撤去,只见门口离着位锦衣贵妇,那贵妇不怒而自威,一个眼神斜来竟叫刘婆子不自主地抖了抖。
刘婆子眼前闪过长信伯的重金酬谢,又想到谢家早已无人,她挺了挺胸,质问道,“尔等何人?这是长信伯郑家和三等伯谢家的家事,无关人等速速退去。”
谢氏冷哼了一声,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裳,根本不去搭理刘婆子,刘婆子恼羞成怒,挽起袖子就要上前理论,还未走到谢氏跟前,便叫耿妈妈一胳膊推了出去,一个不留神栽倒在地上。
耿妈妈俯视地上的刘婆子,正声说道,“我们太太乃平鎏侯谢湛嫡出长女、孟子六十一代孙嫡妻、镇西将军符纪霖岳母、新科探花郎生母、谢家小姐嫡亲姑母是也。如何不能理谢家之事?!”
82生无缘
“谢家的事,我们太太如何不能管?”耿妈妈目光直向刘婆子刺去,刘婆子嘴皮子开了又合,终是没说出个不字。
宜珈搀着谢氏步入正堂,谢氏挨了左首第一个位置坐下,宜珈退一步站在她身后,母女俩并一众奴仆竟是一眼都没瞅那刘婆子,谢尚翊兄妹有了主心骨,也默默挨着宜珈站到谢氏身后。
刘婆子见谢氏气势十足,心头萎了一萎,陪笑着说道,“原来夫人是自家人,婆子我有眼不识泰山,夫人别见怪,别见怪啊。”
谢氏自管自喝着茶,并不理她,刘婆子又闹了个没脸,再厚的脸皮也经不住烧起来,瞟了一眼一旁的妇人,示意她出面。
那妇人便是长信伯夫人的得力心腹周妈妈,贯会察言观色,是以她一见谢氏出面,便知这事要坏。周妈妈恭敬的给谢氏行了礼,谢氏听她自称长信伯内管家,终于抬头看了她一眼,却照旧没搭理她,周妈妈也不尴尬,半跪着继续给谢氏行礼,刘婆子努了努嘴,不情不愿的也跟着半蹲了下来。
谢氏下马威给足了,准了她起身,周妈妈站地笔直,丝毫不显落魄,谢氏心里暗暗点头,郑家规矩倒也不错,刘婆子暗暗揉着酸疼的腿脚,心里一通咒骂,两人倒成了鲜明的对照组。
谢氏放下茶盏,眼神直直看向周妈妈,正声问道,“长信伯派人前来,不知所谓何事?”
周妈妈叫谢氏的眼神看的全身一凛,回禀道,“回太太的话,我们夫人沉疴冗疾多年,近日来病情愈加沉重,怕是难以操持三个月后的婚礼,故派老奴来与贵府商议,不知可否将婚事推迟个……一年半载,待夫人身子痊愈后再行大办。”
谢同壁脸色煞白,手指蜷曲发抖,长信伯三年守丧,她如今已满十八,旁人这年纪早已生儿育女,她却仍待字闺中,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姑娘”。若再等上个一年半载,且不说到时候是否能真嫁过去,即便郑家信守诺言娶她过门,恐怕庶子庶女也都能开口喊人了,年华老去的她如何能在郑家立稳脚跟?如何能获丈夫欢心,得公婆青眼?
谢氏听了周妈妈的话,嘲讽般笑了一声,说道,“女子年华拢共不过那么几年,我侄女替你们老太太守丧三年那是孝道,可如今要她替你们‘健在’的夫人也守个一年半载,这算哪门子的道理?”
周妈妈垂了眼,不敢接口,谢氏也不理她,接着说下去,“若贵府夫人当真重病在身,这民间也有个土方子,叫‘冲喜’。我侄女虽是金枝玉叶,高门贵女,可孝字为先,为了婆婆的安康,早些嫁入伯爵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