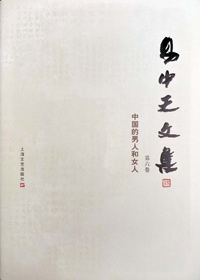宝珠鬼话第六话-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的形状,只留一层枯黄色的皮松垮垮覆盖着那堆骨头,在车身的震动中微微颤抖。
我呆看着这一整个过程在我眼皮子底下无声无息地发生。
脑子里有那么片刻是一片空白,随着列车忽然间一阵有点强烈的晃荡,冷不丁想起了什么,我整个人电击般朝后紧贴到了门背上。
我突然想起来所谓的“走尸人”是什么了……而这同时我明白过来我可能做了件多么愚蠢的事情,愚蠢到致命。
从遇到这两个男人那刻起到现在,这么一段时间,我从最初的嫌恶,到后来的怀疑,再到后来的恐惧……一直以来我所怀疑和恐惧的对象,都始终只是那个看上去邋遢而诡异的老头。即使是刚才男人突然死而复生并用那种极端手法杀掉了他,我所感觉到的也只是震惊。
都说人是以貌取人的,这话不断被人拿来说着别人,却又不断印证在说的人自己身上。
从第一眼看到时起,我一直就在害怕着那个老头,后来几乎已经把恐惧直接套用到了现实,全因他的长相和他诡异的行为。可仔细想想,其实这个男人和他一样可疑的不是吗,只是在恐惧面前我压倒性地把所有的怀疑都倾斜到了最直接影响着我的老头身上,而忽略了同样的威胁,它还可能存在于这个被用那么可怕的方式折磨着的男人身上。
普通的人怎么可能承受两颗钉子这么赤裸裸地钉在头上还能若无其事到处走动?任谁都能看出那方法不是通过医疗手段做出来的,而能承受住这样的折磨的他,即非人,也非鬼,那他到底是什么。
真可笑,我居然一直一直都没有正视过这个曾在我脑子里短暂出现过的怀疑。
而直到这男人嘴里那三个字被像他手里那枚钉子似的硬生生敲进我的头,我才刚刚省悟,一直一直地要求我拔掉他头上的钉子,我在被老头的到来吓得最终听了这男人的话为他拔掉之后,到底我为此得到了一个怎样的后果。
可能根本不是我所要的结果,可能是比之前更加糟糕的结果。
因为“走尸人”……
虽然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把这个有点离奇又有点荒诞的乡土传说当真过。
“走尸人”是个古老的职业。
据说在殷商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有过鼎盛,后在满人入关后开始逐渐迅速衰败,是种至今应该已经失传了几百年的传统。现今除了居住在当年盛行着这种职业的部族附近那些村庄以外,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曾经的存在。而在千年之前,这种职业因为它的独特性和一些相当诡异的能力,曾经是被当作一种精神象征而在某些土著里盛行一时的。
众所周知,湘西有“赶尸”这一自古流传至今的古老职业。传说担任这个职业的赶尸人能通过某种方式让尸体直立起来跟着他行走,因为看上去就像是趋赶尸体,所以人们叫它“赶尸”。这个职业的存在是为了把不幸客死异乡的人的尸体运送回家,不过听说真正的“赶尸人”现在也已经失传了,到现在还在做这一行当的,多数都是跟过去老师傅学了点皮毛装装样子的江湖骗子。
“走尸人”有着和这种古老职业极类似的名字,连形式都相似——
通过某种方法让尸体自己站起来行走,以达到趋尸的目的。但除此之外,它又是种和“赶尸人”完全不同的职业。它更类似于一些不太能被人们所接受并且相信的东西,比如巫术。
据说它曾经盛行在北方某个自明清时期就已经消失了的部族的群落里,部落很闭塞,除了必要的交换几乎不涉足外面的社会,而他们一代一代传承居住着的地方靠近长白山,是个被长白山山脉附近的一些山包围绕着的生活在寒泽地里的部落群。
读书那会儿我有个同学老家就在长白山,暑假里经常会来我家串门,关于“走尸人”的事,就是她告诉我的。
她说那个部落住的地方以前曾被叫做走尸地,是南来北往一些和他们接触过的猎户商贩们给叫开的。有点岁数的老人们常说,那地方在靠近山包口,过去曾有条小路直通那个部落。就是几十年前还曾经见到过一两个人从那里出来,不过后来渐渐就没了,路本来不宽,被野藤类的一长就完全没了踪迹,估计里面的人也早就死绝了,封闭就代表落后,落后就很难不被自然所淘汰。
只是一直到今天,靠近那地方的猎户们还是很忌讳那片曾被称作是走尸地的区域,可能是因为从小到大被灌输着的那些思想作祟。
都说那地方是诅咒人的,生在那里的人不怕,就像蛇不畏惧蛇毒,而旁人要是不小心进到了那里是会被诅咒的,诅咒者是千百年来被那地方的巫师们所操纵和镇压着的死人。
所谓“走尸人”,就是用某种不为常人所知的巫术去制约死者的尸体,并达到操纵他们为己所用的人。资历浅的在师傅的指导下操纵新尸,而那些有了几十年甚至百年经验的,便能操纵老尸——一些虽然已经死了很多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但因为保存得相当好而完全没有腐烂的尸体。也因此部落里的人为了供给这些巫师们所需要的“原料”,常会出山盗尸。
这是很缺德的,先不说很多尸体是被他们挖开了坟墓硬盗来的,单说一旦被他们操纵,那些死人就处在活不活死不死的边缘,即不能往生,灵魂也不得自由,对死人来说相当的悲惨。于是那地方怨念极重,重到部落周围一片片浓得散不去的寒气,看上去就像沼泽里生出来的雾。
但操纵死人是有代价的,以一种代价来换取另一种代价,是人包括自然所默认的共通潜规则,即使你拥有操控和改变自然的能力。
操纵死人的代价是反噬,反噬的后果是操纵者的生不如死。
很多巫师,尤其是年龄越大经验越丰富的巫师,随着岁月的逝去他们开始不满足于单纯驾驭那些纯粹的尸体,他们会寻求一些更难控制的东西以图这个部落里无可取代的显赫位置——走尸王。
于是他们会冒险尝试一些在这行当里所被禁止碰触的东西——一些死因蹊跷的尸体,一些被用特别的方式埋葬的尸体。那种尸体通常是有危险性的,有些年岁老的甚至连同棺木一起化成了丧尸或者厉鬼,如果用了这样的尸体,一旦控制不当,那么遵循这种巫术的代价,走尸人会烂心烂肺化干了身体里的一切,再被原本所操纵的尸体由其被操纵的方式将他控制。所谓的生不如死,就像那具被他所操纵的尸体曾经所经受的。因为即使是被弄成那种样子,这个走尸人本身还是活着的,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那具操纵他的尸体不毁,他将被那具曾被他操纵着的尸体操纵到完全腐烂化尘为止。
这就是我对“走尸人”这一称谓所了解的全部。
本来是早就忘了的,因为从小到大,对种种类似的传闻听得多,忘得快,从来不长记性去特别记上一些的,这大该同我天生能见到一些别人所看不到的东西的体质有关。往往看得越多,人就越现实了吧。所以一直都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乡野故事来看待的。
只是这次被这一连串的经历一刺激,那些东西全都在我脑子里浮出来了,也正因为此,我的脚一软,在那男人站起身的时候竟恐惧得朝地上瘫坐了下去。
怪不得从他们进包厢之后就一直冷一直冷……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鬼,这个女人般美丽的男人,他是个活死人啊……
脑子里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还在风车般转动着,男人一脚跨过地上的尸体已经走到我面前。只是一双眼睛并没有看着我。手指在自己头发上一下一下耙着,慢慢将那把低垂在脸侧的长发整理到脑后,他低头看着地上那具在短暂的颤抖过后再次静止下来的尸体。
显然我并不是他注意所集中的目标。意识到这一点,手脚突然来了点力气,趁他将视线转到尸体的头颅上若有所思盯着那枚钉子看的时候,我脚一撑一下子从地上站起来,转身一把抓住门把手猛地它朝边上一扯。
咔啦一声脆响,很大的声音,惊得我不由自主朝后看了一眼。就见那男人一双黑锃锃的眸子蓦地转向我,而我面前这扇门却纹丝不动。
头皮一阵发麻。
赶紧低头去检查门有没有被上锁,可心急慌忙间一时根本找不到门锁在哪儿,这当口脚脖子上突然冰冷冷什么东西轻轻一触,下意识低头,一眼清楚脚下的东西,我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气。
脚下一团桃红色的身影。身影紧挨着我的腿在地上匐着,一只手拿着根棒棒糖,一只手抓着我的脚脖子。在我低头看想她的时候她也正抬头盯着我看,听见我的吸气声,她忽然笑了,笑的时候额头微微皱起,上面那颗钉子在灯光下闪着明晃晃的光。
“给我……你的身体……”耳边再次响起那男人的声音。抬头就看到他一步跨过地上的尸体朝我走了过来,边走边解着身上那件黑色衬衣的扣子,扣子打开露出里头的皮肤,乍然袒露在我面前,激得我全身一个哆嗦。
同脸和手脚的皮肤不一样,那大片的肌肤是淡紫色的,青和紫的交错。从胸口到小腹那一大块地方向下凹去,那块地方的皮肤都已经烂透了,露出里面苍白的骨头,在一些不停生出又不停消失着的皮肉下隐隐泛光。
“给我……”又道。轻轻丢开手里的衣服,那个美丽却腐烂着的男人冰冷的手指触到了我的脖子上。
冰冷冷地一划:“你的身体……”
我眼前一阵发黑。
“嘭!嘭嘭!”正在这时候背后的门突然一阵震动。
回过神全身猛一阵颤抖,一声尖叫从嘴里我脱口而出。随即身后突然一空,整个人促不及防地仰天朝后直栽了下去。
却并没有倒地,因为被身后一只手一把抓住了我的衣领。
回头就撞上一双烟熏似的黑眼圈,探头朝我包厢里看了看,他又转头看看边上的门牌。似乎对包厢里那一片血肉模糊的狼籍以及我面前这个赤裸的男人视而不见,半晌低头看向我,挠了挠自己的头:“请问……08号床是不是在这里。”
第九章
话音落,没等我反应过来,人已经自顾着朝包厢里走了进去,那个在酒吧里自称是个术士的少年。
我呆看着他一脚踏上那片被血浸透了的地毯。
地毯早就被血泡松了,一踩嗤咔一阵轻响,而他对此完全没有任何知觉,若无其事踩过尸体斜在门边的腿,又踩过尸体佝偻成一团的身体。车身摇摇晃晃,喝多了似的,他的身子在包厢狭窄的空间里也摇摇晃晃。
摇到男人的身边一个趔趄,眼看着肩膀要撞到男人身上,他一伸手,手指贴着男人的鼻梁搭在了他脸侧的床铺边。又晃了两下,站稳,少年回过头看了看我:“不进来?”
我扭头就朝走廊里冲。
没跑出半步突然头像是撞到了一堵结实的墙上,我只觉得凭空脑袋上一记震荡,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眼一黑人就朝着包厢里直跌了进去。连颠几下一屁股坐到地板中间那具尸体上。心说不好,可人再也站不起来了,地上粘糊糊的,一踩一个滑,挣扎了半天只弄得自己更加狼狈,而就在身下,尸体那张被血糊得五官模糊的脸正对着我,嘴张得很大,像是在冲着我嘿嘿地笑。
心一寒,手脚匆匆地朝后缩了缩,这时候忽然耳边又响起那少年的话音:“啧,好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