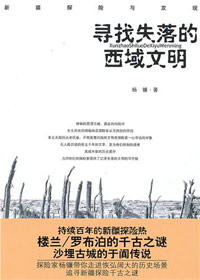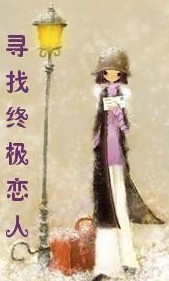寻找巴金的黛莉-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束采访之际,赵老艰难地站起身来,要给我找出一样东西,说:“这东西,可能你能用上哇!”
就是这样东西,让我们看到了确凿的希望。
赵老颤巍巍地挪动脚步,来客急忙让开。他打开靠墙老柜子,探进一只胳膊,弯腰在柜子底部耐心地抓挖着。柜门里头黑暗杂乱,我什么也看不清。他摸索这样东西,大伙儿全都闭了气,没有言语。
老人直起腰来,把十几页有些残破的打印稿,郑重交给树森。王树森双手接过,又默默地交给我看——这是一种非常简易的《家谱》。封皮上打印了一个标题《山西宁武赵氏家族成员谱》,下面印有时间,为“公元二〇〇〇年五月二十日”。撰者在《后记》中写道:“二十世纪中叶,自日寇侵华,中国社会即入多事之秋。国人生存尚自难保,修谱之事亦中断数十春秋。现今重事整理,拾遗补缺,时犹未晚。”相问后得知,这一册简易家谱的撰者,是赵家流落广西柳州的第九代人赵柱先生,依据当年匆匆带走的老谱整续而来。这位赵柱老人生于1930年,为黄埔军校第22期毕业生,是赵瑾老人的堂弟,后在柳州一家工厂做厂长。赵柱之父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赵廷畴。1998年前后,赵柱先生把这份新修家谱转交给留居北京的第八代前辈赵廷助,再做补充核对。赵廷助老人即命其侄孙第十代人赵霭龄当此重任。赵霭龄生于1939年,曾任吉林辽源矿务局高级工程师,后居北京。赵霭龄在赵柱修谱基础上,广为调查落实,尽可能地补充了赵家后两代人简况,终成此谱,计28页。如果赵梅生果真是赵黛莉的话,她应该忝列于赵家第九代人当中,和赵瑾老人一样。
我手持此谱,凑近了小屋半空里那只昏黄灯泡,检看其中第九代人。在第15页中,我看到两行字:
赵梅生,生于1920年,居西安。先后供职于西安交大、建设银行等。任会计。退休。
嗣一女:赵健,居西安,任职建设银行会计、处长。适河南籍周明东。
很短,没了。
然而这却是许久以来我所得到的最为直接、最为可靠的一条信息。此后开展工作,凭的就是这几句话。
感谢赵瑾老人,祝他健康长寿。
出于对树森先生的信赖,赵老特许我们上街复印此件。
张发兄、树森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一趟宁武冰雪路,没有白来,最是关键。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十六 在西安会晤赵健女士
从宁武回到太原,又到北京,已是2009年3月上旬了。我反复研究《赵氏家族成员谱》,特别关注赵梅生名下的那两行文字,仿佛看到一个大家族的成员们,挥泪奔逃的仓皇情景……问题是:此谱修成于2000年之前,上说赵梅生已在西安退休,而光阴如梭,又有十载春秋逝去,这位梅生老人,她依然健在吗?此外,在“赵梅生”名下,为何仅有一女赵健及其女婿,却在其丈夫一栏中不着一字?与谱中其他人相对照,如此空缺,尤为明显。
庆幸的是,已知其女赵健“居西安,任职建设银行”,有了这一条,便足以推进调查进程。
古城西安,有一些朋友在。还是老办法,首先应该通过友人先期查找赵健女士,取得初步联系后,再赴西安细访不迟。只是西安朋友多多,要选出一位可拜托的合适人选,又颇费思量。弄不好,哪个冒失鬼将把赵家母女吓一大跳,陕西话会说:这是查啥呢?咱老赵家复杂得很!
著名文学评论家李炳银先生,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这位老大哥倾力关注当代纪实创作,理论著述颇多。我们之间保持着多年交往。他正是陕西临潼人,这一日,我将前面的故事向他细叙一遍,从发现巴金七封信,一直说到西安赵梅生、赵健母女俩。炳银兄越听越激动,凭着经验,他一口断定赵梅生就是黛莉无疑。我向他请教,西安哪位朋友适合于开展前期查找工作?炳银兄不假思索,举荐一人:李彬!李彬热心、细心,能行。
炳银兄亲自给李彬打了电话,我继而向他说清了要找赵健女士的缘由。至于她是哪一处“建设银行”的人,则需要辛苦查问。取得联系办法后,暂时不必多说什么,只待我择时前去,从容采访。
李彬在电话里热情地说:没问题,你们放心吧。
4月春将尽,西安消息来。李彬贤弟动用层层关系,终于在银行系统找到了赵健其人,并且与这位退休女士通了话。李彬确认赵家正是山西宁武人,然后非常礼貌地相告,可能会有作家前来请教几个问题,只是关于上一代知识女性读书的事。好比说,你母亲那一代人,是不是特别喜欢巴金作品呀?还可能与巴金通过信件吧?反正没有什么别的意思,万勿推辞云云。
赵健女士欣然接受了李彬这番话,对作家前来访问表示欢迎。
李彬担心多说不准确,也就没有深谈。
李彬说,从通话中分析,赵健母亲赵梅生,很可能还活在世上哩!
我很振奋,又很急切,手中长篇哪里写得下去。
5月18日,我下了飞机,站定在西安大地上。李彬来车,接我入城。更令人愉快者,李炳银先生正好也在西安。痛快!三人聚合,八仙桌上举杯,把各种情况交流一番,觉得今日之事简直不可思议。
次日午后,李彬成功地部署我与赵健会谈。
赵健女士年过六旬,容面大方,身体健康。她稳坐在茶室竹椅上,神情安泰,修养甚好。李彬考虑到,赵女士可能并不乐意一下子就把我们领到家中去,因此,双方不妨先在茶舍见个面,饮一杯清茶,做个初步接触,人家心理上便会踏实许多。如此安排,稳妥而又礼貌,是周全的。下一步采访尽可酌情商量。果然,赵健女士十分满意这样的做法。
不难想见,赵健女士首先会生出一串问题:为什么一个外埠作家,大老远跑来专程访问我们家?作家为什么关心我母亲?我家的事情很复杂,作家能够给予多大程度的理解呢?你们到底想知道些什么呢?
我这边,胸中也揣着一大堆问题:赵梅生老人是否还活着?她是不是赵黛莉?
大家坐下来,李彬把我做了简单介绍,赵健女士便直率地开口道:不瞒你们说,我感到奇怪呀,真的,赵作家为啥来找我家?您想了解我妈妈什么事?
我说,我将细细告诉您我的来意。只是首先问候您母亲,老人家身体还好吗?
赵健略作迟疑,轻声回答:她年纪大了,晚上睡不着,每天总是到午后才醒来。过会儿我得回去,招呼她吃饭。
此言如雷贯耳!
赵黛莉——如果没有弄错,她还活在人间。
接下来,谈话步步深入,又处处顺利。
前些天,李彬与赵健联系时,曾谈及老母亲年轻时爱读巴金作品,赵健便就此问过母亲,问她是否与巴金有过交往。老人说,抗战以前,确与巴金多次通信,而且清楚地记得,离家时,她把一些书和这包信件,安放在太原家中顶棚上了。这个家,便是坡子街20号大院。
一切都对上号了!赵梅生,应是赵黛莉。
老人现在脑子如何?赵健说,还好,记得许多人和事,夜里睡得较晚,仍然看书读报,最爱看《参考消息》,平时喜欢独处,不爱热闹;常常提起年轻时,与姥爷闹了意见,离家出走,到处漂泊;既没有投身国民党,也没有找到共产党,嫁人又极不如意;1950年以后大吃苦头,总被怀疑为“女特务”,“*”中更有受不完的罪;一生命运坎坷……就连这位女儿赵健,一生也没有见过亲生父亲。而这一切,还要她自己才能讲得明白。
——现在,赵健必须回家去,照顾老人用餐。用她的话说:我就是我妈妈的保姆。我提出,希望近日能与老人相见。赵健表示回家后,与老人慢慢地说清原委,一旦征得她同意,即电话告知我们。
我说,非常感谢,明天最好,但要依照老人意见办,不可太急。
说是不急,其实我心中甚急。90岁的老人,身心脆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争取早日进行采访,便是对历史真相实施抢救。
耐心等着吧。
晚饭,李彬请吃羊肉泡馍。众皆沉默。只因赵健那边没来消息,便觉得这泡馍不及往日可口。
正思量处,赵健电话到:明日午后,可来家中一叙——这泡馍顿时香气四溢,将人吃出细汗来。
十七 战争也没有毁掉它们(1)
我们终于就要见到赵黛莉了。
老人和女儿一家住在市内一片楼区中。我在附近花店为她们购得两束鲜花,一束大些,给黛莉,一束小些,给赵健。店员也是年轻女士,问及送花对象的年龄,我说一位90了,一位60了,加起来150岁了,你要扎得好看些。店员闻言,选花、扎花格外用心。一时间,我想到了许多人和事。所有这一切,到底为了什么?我们究竟在寻找什么?
自推翻帝制以来,百年中国从未停息血火厮杀,正所谓救亡压倒启蒙,反帝反侵略与反对封建糟粕混作一团。在无情的暴力革命和土地战争面前,封建传统历史性地崩塌了,又似乎依然存活无碍,并没有真正崩溃!我们推崇背叛,包括推崇革命先驱们对无数家庭的背叛,这一切,又似乎根本不可能。传统家庭就像一条河流仍在奔腾向前,而我们不过是这条滔滔大河中一粒黄沙碎砾……
我又一次想到了《夜未央》当中革命青年的爱与死,又一次想到易卜生名剧《娜拉》和更多的质问:娜拉走后又怎样?
也许,我们想在黛莉后半生那坎坷人生当中,寻找并且证明些什么——要国?要家?要民族解放、个人自由?这些概念是分裂的还是统一的?我们怎样看待巴金和他的《家?春?秋》?事到如今,我们对于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主旨,又将如何评说?现当代文学之间是什么关系?作家、作品与痴心读者之间,在历史上又产生了怎样的作用……
上得楼来,李彬兄弟轻轻叩门。
赵梅生女士拄着一只拐杖,站立于厅堂中间,并无须赵健搀扶。她用典雅的微笑迎接盛开的鲜花。
一个漫长而又隆重的午后。
追访历史,晚辈唯余敬畏。
谈话从名字开始。小问题,易轻松,却极是关键。
我需要再一次验证,眼前这位梅生老人,是不是当年那位赵黛莉?
李彬搀扶老人坐定。
“老人家,您还记得黛莉这个名字吧?”
赵梅生老人腰背端直,面容方正,戴一副方框眼镜,保持着一种非凡的气度。她毫不迟疑,并且有些欢快地回忆道:那时我在太原女师读书,有几个同学很要好,都嫌原先名字土气,一个胡同学起了新名叫燕莉,很好听,我就叫了黛莉,还有一个杜同学,想了半天起不好,我们就叫她黑莉,说黑色跟黛色反正差不多呀!她也认了,另一位好朋友,叫文彩霞,起个啥莉她都不满意,就还叫文彩霞吧。彩霞住在上马街,我家住在坡子街,关系特别好。
她确实就是赵黛莉啊!老人脑子清楚,我很庆幸。
接下来谈读书,以便接近巴金。
黛莉老人——现在终于可以确认这个称谓了,她用那种非常熟悉的山西普通话来表述历史,因而让我感到这历史很近很近,并不遥远。她清楚地记得那些革命理论家的名字: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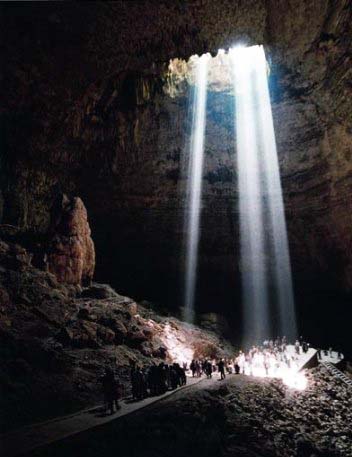
![[剑网三]寻找帮主夫人大作战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1/165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