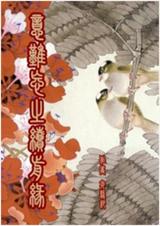意难忘之续前缘-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大口子,里面白生生的胸脯和肚皮,在人前坦然相承。众人皆是一愣,随即便是拍桌子跺脚的大笑起来。 飞雨抱着酒壶笑道:“了不得了,这身子全让他看见了,只好嫁与他做浑家罢了。”南朝在那厢拍着胸脯儿道:“甚好甚好,我这里与你们主婚便是。”东城早松开了手,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想说话却开不得口。跟露桥的厮儿强忍着笑,将外头的衣服与他穿好。尚未退去,却见那位有着琥珀眼的小公子,端了酒杯走过来。朝着自家衙内,梨涡浅笑的轻轻道:“二嫂,请饮了小弟这杯酒吧?”露桥不曾料到,他竟会出来调笑自家。转瞬又明白了,芳华定是恼自己,将他当作了娈童一流。又兼之方才,自己要拿大海杯罚他哥哥的酒。一时恼又恼不得,笑又笑不出,睁着元宵似的双眼,张口结舌地望着他。众人一发的大笑起来。便是那咏歌也笑出了声,望着芳华的眼神意味莫名。 东城叫了声“好兄弟”,故意乜斜着眼道:“娘子,你叔叔敬的酒但饮无妨。”露桥微微一笑,接了芳华的酒杯。肥腰慢摆,莲步轻移,柔若无骨的靠在了东城肩头。叫了声嫡嫡亲亲的心肝儿肉,含了口酒,伸手搂着他的脖子,照着嘴便狠狠的吻了下去。那东城岂料他来真的,吓得脑子一片空白,僵着身子竟忘了躲闪。露桥也不过是想吓唬他,见了他这个呆样儿,先自忍不住大笑起来,一口酒全喷在了东城的脸上。众人顿时绝倒,个个抱着肚子笑岔了气儿。东城此时才回醒过来,拿衣袖胡乱的抹着脸,追着露桥骂道:“臭猪,你敢是骚劲儿大发了不成?”露桥扯了芳华挡在身前道:“死贼,还想占我的便宜,活该!”又尖着嗓子道:“官人,奴家这酒香是不香啊?”众人一听越发的狂笑不止了。连那些在一侧侍立的下人们,也都笑得蹲在了地上。采茗素日也算稳重的,这会子笑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 芳华被适才那幕吓得有些蒙了,好容易脱开身,便想到外头疏散疏散。谢了咏歌的好意相陪,只推说要去净手,自行出房去了。采茗在那厢看见了也跟了出来。 芳华净手出来,在廊上的窗前站定。深深的吸了口气,忽听得“吧嗒”一声响。低头看时,原来腰间所挂,双剑玉佩的带子断了。芳华慌得俯身拾起一看,见玉佩并无损伤,这才拍着胸口道:“去年过生日三哥才送我的,若是摔坏了,岂不要辜负他一片心吗?”忽然便想起昨晚的事来,拿着玉佩只管呆看。 也不知是哪间雅座吃醉的客人,被家人扶着左脚踩右脚的去出恭。那走廊本不甚宽敞,他又东倒西歪的,正撞在芳华的肩头上。一个没拿稳,玉佩顺着他的手滑了下去。芳华一声惊叫,伸着手猛地往前一扑,想要抓住玉佩。谁料那窗台有些偏矮,他的力道有太大,一时哪里收得住脚?采茗眼睁睁的看着芳华,如狂风吹落的花朵,朝楼下坠去。 芳华但闻耳畔一片惊呼之声。正盘算着跌在地上会有多疼?身子忽然变了方向,横着飞了出去。在一片喝彩声中,感觉有一股熟悉的气息向自己围拢过来。忽然之间,芳华的心突突直跳,没来由的一阵悲从中来。不自觉的将那人死死的抱住,仿佛此刻便是天塌地陷,也休想让他松开。 耳边听那清澈的声音对自己连连呼唤,芳华却不愿有所回应,只想在那人怀中多呆一刻是一刻。若不是感到,那温暖的手抚在自己胸口上,芳华是不会睁开双眸的。泪眼模糊间,望着那有着月光般温柔的眼睛,他已深深的沉醉其中。半响,嘴里轻轻的唤了声“泊然”。不想那人满脸惊讶,急急的问道:“你说什么?”
☆、第六回匆别过芳华意缠绵 兄弟会时翔露端倪
房内众人,猛听得门外尖利异常的一声惨叫,几乎将耳膜刺破,尚未回过神来,便见采茗跌跌撞撞的跑进来哭道:“四公子坠楼了!”咏歌当先冲了出去。东城只觉得,脑袋让人拿大锤狠狠地砸了一下,一第六回匆别过芳华意缠绵 兄弟会时翔露端倪头栽倒在地。寄优扶着桌子起了两次,皆因腿抖得厉害竟没站起来。
等一群人冲下楼去后,便看见芳华毫发无损的,被一同龄的少年抱在怀内。二人不知何故,正四目相对的互相呆看。
但见那少年穿着时新的,象牙白收腰窄袖宝相花纹罗袍。足登水蓝缎面薄底靴,头裹素色软巾,两根飘带上缀着龙眼大的珠子。果真是貌似谪仙降凡尘,气若芝兰贵自华。
咏歌心下可惜道:“哼,倒让他捡了便宜,做了回好人。”一面拱手笑道:“原来是凤弦啊。多亏你出手相救,不然芳华岂不性命堪忧了。”又与众人引荐道:“这位是子叔丞相的次子,太子伴读子叔凤弦。这二位公子是升平郡王的次子与四子,左东城,左芳华。”东城与寄优听罢,慌得上前连连作揖道谢不迭。凤弦扶着芳华站稳道:“兄台可有摔坏哪里不曾?”芳华不及擦拭脸上的泪痕,忙还礼道:“多谢子叔兄相救,小弟并无大碍,不知兄台方才接住我时,有无伤到哪里?”凤弦含笑摇了摇头。
东城拉着芳华,转着圈儿的看了一遍道:“四郎,你……你怎的便从窗户上跌下来了?”回头冲着采茗吼道:“狗才,我只道你有多细心服侍主子了,你当的什么差?”那采茗此刻已被吓的,只剩下半条命了。跪伏于地浑身抖得如同筛糠,口内不断的抽着气,一个字也答不上来。芳华晓得,他回府必被时鸣重罚,心中颇为不忍。上前亲自拉他了起来,对东城道出事情的缘由。东城见他手上,竟然还握着那块玉佩,不由得邪火儿直往上撞,一把夺了狠狠的便往地上砸去,骂道:“什么劳什子玩意儿,竟比你的命还值钱不成?”芳华大惊失色的伸手去接,却早被凤弦一把抢在手中,芳华脚步踉跄的撞进他的怀里。凤弦及时的将他抱住立稳,把玉佩递还与他。
芳华攥紧了玉佩对东城嗔道:“二哥哥这是做什么?”东城又是后怕又是生气,见了那玉佩便觉得牙痒痒儿的,只恨不能要砸碎了才消气。寄优拉了他一把,朝着凤弦拱手道:“今日全仗衙内出手,救了他便是救了我们。无论如何请到寒舍一聚,容我们再行谢过。”芳华道:“这位是小弟的舅舅,请子叔兄切莫推辞才好。”凤弦方才听他唤自己“泊然”,想着日前做的那个奇怪的梦,心下早已是惊疑不定。待要细问又委实不便,横竖是知道他们的身份了,还怕不能再见面吗?何况太子尚在宫中等候,只得推辞道:“路遇危机焉有不救之理?不值一谢的。小弟还要入宫去,这便告辞了。”芳华一把扯住他道:“小弟明日要往尊府上拜谢,不知在哪条街上?”凤弦微微有些脸红,低垂了眼帘道:“在,在西城香冬坊。”芳华这才松开了手,目送凤弦上马而去。
东城此时兴致全无,辞别了众兄弟,攥紧芳华的手,径自往家而去。那芳华一步一蹭,不时回首凤弦远去的方向张望。眼中有一丝莫名的情绪,被立在阶上的咏歌,不动声色的尽收眼底。
却说那时鸣,在他兄弟府上等了有半个时辰,也不见人影。正自焦躁,忽见一卷画轴慢慢地伸至眼前,在自家下颌一挑,紧接着被人在耳边吹了口气,“嗤”地一声轻笑。时鸣心中暗骂一句“混账”,冷冷的转过脸,盯着眼前之人开口道:“你要做什么?”只见那人三十二三岁,极斯文极雅致的容貌,做儒生打扮。方才有些轻佻的笑容已凝固在了脸上。讪讪的往后退了几步,拱手道:“大哥安好。”时鸣最不耐他这般称呼自己,横了一眼道:“你好歹是宫中从五品的官儿,我不过郡王府小小的管事,如何当得起?”原来,此人便是林溪说的,与廉松风相仿,官家面前的红人儿,内克典使和忆昔。
忆昔扬眉挑眼的看了看,时鸣左侧脖颈处,绿豆大的红痣,暗道一声“晦气”,却又不得不赔着笑脸道:“哥哥与时翔并非孪生兄弟,却长得着实太像了。若非那颗痣,可叫人怎么分辨呢?”时鸣皮笑肉不笑的讽刺道:“你与他常在宫中见面,又……”方说到这里,脸上变现了怒容。狠剜了忆昔一眼,见他正毕恭毕敬的坐在那儿,讨好儿的冲自家笑着,便越发的来气,几乎是咬着牙道:“又……又与他相交数年,竟然连他的容貌也分辨不出吗?亏你还口口声声的说,将他放在心上,真是活打了嘴!”忆昔放下画轴,面带微笑直视着时鸣的双眼道:“小弟与时翔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他晓得我对他的心。因此,哥哥当初百般的阻拦,甚至要与他断绝兄弟情义,他也没有一丝动摇过。”时鸣冷笑几声道:“你好得意呀!”忆昔道:“哥哥再多一个兄弟不好吗?”时鸣重重的哼了一声转身便走。
恰在此刻,门外赶进一个容貌与他有七八分像之人,伸手将他好歹拦住了。细看时,那眼神却没有他犀利。此人便是时鸣的兄弟,入内内侍省副都知井时翔。忆昔忙上前握了他的手道:“哥哥等了许久了。”时翔见兄长脸色难看,不动声色的躲开忆昔的手,拉了他坐下,又令女使重新上了茶,这才横了一眼忆昔道:“你又惹哥哥生气了?”忆昔连连摇首笑道:“不敢不敢,我正在聆听哥哥的教诲。怎的才回来?”一面说,一面将茶捧到他手上。时翔接过慢慢呷了一口,笑道:“临时有些事给绊住了。”时鸣道:“你唤我来究竟何事?”时翔笑道:“哥哥年纪也不小了。律法有定,凡宦者年四十皆可收养子,以供老来侍奉。哥哥心里有人选了吗?可要我与你寻一个来?”时鸣略微沉吟道:“此事尚不急,待过些日子在说吧。”时翔望了忆昔一眼道:“想是四公子一刻也离不得哥哥,不如我替你寻个合适的……”时鸣不待他讲完,便挥手打断道:“我且不急,你倒急得什么?你只管好好的在宫中当差,我的事不必操心了。”时翔还要再劝,时鸣便要告辞回去了。
时翔心中一急,上前扯住道:“无论你喜欢他还是可怜他,他终究不能成为你的孩子。总骂我行事糊涂,我看你比谁都要糊涂!他现下就算不是官……”时鸣一把捂住了他的嘴,忆昔不急不慢的走到门边,目光向外打量片刻,确定无人方才退回来。时翔虽脸色有些发白,却依然抓着兄长不放,压低了声音道:“他对你再好你们也是主仆的名份。你莫不是指望着他床前尽孝,养老送终不成?哥哥你,你……你果然糊涂得紧呢!他是郡王的公子,你又是什么身份?”忆昔见时翔越说越激动,忙上前劝道:“有什么话,兄弟坐在一处慢慢的说,你这是做什么?”
不等时翔开口,一个家人跑进来道:“回阿郎,方才听外头回来的人讲,升平郡王的四公子不知何故,打雅风楼上跌下来了。”三人一听大惊失色。时鸣几乎栽倒,只觉心都要跳出来了。时翔与忆昔及时的将他左右扶住。时鸣白着一张脸尖声喝问道:“人了,可有救下?”家人回说,子叔丞相的二衙内从楼下经过,将四公子接住了。时鸣不等他说完,甩开二人的手拔足狂奔而去。
忆昔向前撵了两步又停了下来,时翔急问缘故。忆昔道:“他去是理所当然,我若跟去必惹人议论,倘或走漏了风声,那可不是耍的。”一面说,一面挽了他的手坐下道:“当日那孩子小的可怜,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