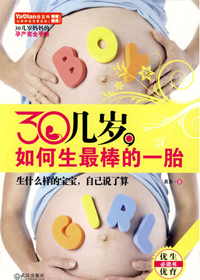文坛巨匠的一生:鲁迅画传-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杂感》等几篇文章,做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等数次讲演,以革命和文学互相印证,互相发明,这倒是很特别的一种方法。 以革命的眼光看文学,于是有了“文学无用”论。一者,权力可以打杀文学。他说:“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有实力的人并不开口,就杀人,被压迫的人讲几句话,写几个字,就要被杀;即使幸而不被杀,但天天呐喊,叫苦鸣不平,而有实力的人仍然压迫,虐待,杀戮,没有办法对付他们,这文学于人们又有什么益处呢?”二者,革命也可以成为一种霸权,迫使文学起宣传的作用而取消了审美的功能。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因此,如果要说革命对文学的关系,首先就是对人的影响,使之成为“革命人”。他说:“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在谈到文学时,他多次强调写作的真诚,这种自然流露的文学是一民族的文化的表现,但于革命,却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力。在这里,他是一个艺术本体论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惟美倾向。 倘以文学的眼光看革命,他认为,叫苦鸣不平的文学对革命没有什么影响,有影响的是怒吼的文学,复仇的文学。但是,这也是革命前的文学现象,及至大革命的时代就没有文学了。因为文学创作是需要余裕的。革命成功以后,有两种文学,一是歌颂革命的,是新制度的讴歌,再就是旧制度的挽歌。而现在是既没有对新的讴歌,也没有对旧的挽歌,由此他就证明中国社会没有改变,广东仍然是十年前的广东。 什么叫革命呢?在鲁迅看来,革命可以有“小革命”和“大革命”之分。所谓“小革命”是指一般的改革,渐进的改革;而“大革命”则是矛盾激化的产物,是弱小者对于压迫者势不可遏的反抗。其次,革命并不排除暴力,但是仅仅逞使武力不足以言革命,仍须包括思想文化方面的变革,而且这是更长久更艰难的工作。三、革命是自觉的社会行为,“奉旨革命”是不能算作革命的。四、革命是以革命者对革命的信仰为基础的,但是革命愈到后来,往往愈不革命;因为当队伍变得浩浩荡荡的时候,革命精神便将转为浮滑,稀薄,或者竟至于消亡,再下去便是复旧了。鲁迅以佛教中的小乘大乘为例,他是以坚苦的小乘教为真正的佛教的。革命也一样,坚苦的进击者是很少的,广大的已经革命的地方,即使显出革命者的色彩,其实和革命毫不相干。五、革命必然有牺牲,害怕牺牲的革命者是可疑的。六、但当为革命牺牲的真正的革命者已为大家所忘却时,革命时代已经过去了。革命无止境,是因为革命精神在未来的时间中,得以不断的延续。可是,精神是需要培养的,而且在生长的途中,不能耽于玩赏而攀摘它的花果。然而,他在革命策源地所见的恰恰如此。所以他很感慨地说:“久受压制的人们,被压制时只能忍苦,幸而解放了便只知道作乐,悲壮剧是不能久留在记忆里的。” '返回目录'
革命策源地(2)
总之,他认为,革命策源地也很容易变成反革命的策源地的,正如他在《在沪宁克复的那一边》这个著名的讲演中所说。 对于过去的论敌,走狗文人,正人君子,现代评论派的南下,鲁迅是耿耿于怀的,总认为是革命的不吉的征兆。其中,尤其是顾颉刚到中大任教,是他所不能接受的。在这期间,他写了一个小说《眉间尺》,开篇就让一只被击落水的老鼠露出它的红鼻子。“红鼻”在他的信中,正是顾颉刚的别号。在他获悉顾颉刚前来的信息之后,当即确定“鼻来我走”的方针,并及时通知校方。小说的主题是复仇,而黑色人则分明带有自况的味道。通篇燃烧着一种战斗的激情,它表明,在这个不公的世界上,是必须有人不惜任何代价,甚至牺牲了自己,去替弱势者复仇的。 大约为了随时可以因此辞职离校,故而同许寿裳、许广平一起,租赁了白云楼26号2楼的一组房间,及时搬出了中大的宿舍大钟楼。 '返回目录'
被梦境放逐的人(1)
国共合作破裂。 4月12日,大奢杀——鲁迅称作“血的游戏”——开始了。北伐军到达上海以后,蒋介石在白崇禧部队的支持下,纠集当地###组织的人物,以“上海工人联合总会”的名义袭击工人纠察队,占领上海总工会,疯狂捕杀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接着下令禁止罢工和游行,解散工会,取缔一切革命组织。从12日到15日,上海有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此外还有500多人失踪。在4月15日当天,广州的李济深等也采取了大规模的清洗运动;出动军警包围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办事处,省港罢工委员会和东山苏联顾问住宅;解散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查封工会、农会、###、妇联等团体,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2000多人,杀害100多人。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一方面发布命令“清党”,清除异端,一方面建立“###”的极权统治。 凌晨。中山大学被包围。宿舍楼的每一层,都有“树的派”的头目带领武装把守,搜查,捕人。气氛十分恐怖。 鲁迅闻讯,匆匆冒雨赶来参加紧急会议。 在会议上,鲁迅郑重表明,对于学生的被捕,学校是负有责任的,希望能够出面担保他们。而且,人被抓走也总应该知道原委,他们犯了什么罪?仅仅宣布一个事实是不行的。他向主持校务的朱家骅建议,找李济深出个布告,不准搜查教授宿舍。对于如何处理学生被捕问题,他与朱家骅的意见是对立的。朱家骅认为,学校是“党校”,因此应当服从党的决定,不要干预政府干的事情。这样的结论当然是鲁迅所不能接受的。他提起五四运动,质问道:当时为了营救学生,不惜发动全国工商界罢工罢市。而这种情况,朱家骅、傅斯年、何思源等参加过运动的人都是了解的。作为过来人,为什么到今天会把这些全给忘了?为什么成百成千个学生被抓走,我们又不营救了呢?朱家骅辩解说,因为时局不同,当时反对的是北洋军阀。如此一来,有何话说呢?他只能说:现在就是要防止新的军阀统治,不能再走老路。 在座的各位主任噤口不言,没有反应。鲁迅再次重复了一通“应该对学生负责”之类的话,而会议也就匆匆结束了。 回到白云楼,悲愤之余,他决定辞职。 4月21日,鲁迅向中山大学正式提出辞呈,与此同时,许寿裳和许广平也一起辞去了各自的职务。 关于辞职,与顾颉刚来中大不无关系。汉口《中央日报》副刊发表编者孙伏园的文章;其中引用了鲁迅和谢玉生给编者的信;透露了这一消息,结果引出顾颉刚写信提出打官司的事。鲁迅认为这是利用“党国所治”的一种恐吓;于是复了一信,因为顾颉刚未曾实行,结果不了了之。后来编杂文集子时;他仍然把信件加了一个《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的题目插了进去。大约因为这是与“现代派”斗争的一段故事;所以不愿轻易从此遗忘的罢。 辞职之后,鲁迅更是深居简出,简直成了现时代的一名隐者。所谓“大隐隐于市”,表面上看来,他也确乎算得是“大隐”了,然而竟没有一点隐者的超然的心思,只有搅缠在一起的痛苦,愤怒,焦灼和无耐。当此时刻,他想离开这个血泊而不能;只好暂且整理一下旧稿,借以排解内心的芜杂。 一是《野草》。编完后,他写了一篇恰如地火般蜿蜒奔突的《题辞》。“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临到结末,则有一种决死的悲壮与昂扬;像这种情辞激切的文字,在他的个人写作史上是不多见的: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就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去罢,野草,连着的我的题辞。 二是《旧事重提》,编集时;改作《朝花夕拾》。大约涉及回忆的缘故,写的《小引》有点悲凉,说是:“看看绿叶,编编旧稿,总算也在做一点事。做着这等事,真是虽生之日,犹死之年,很可以驱除炎热的。”随身带来的旧稿,还有德国童话《小约翰》,待整理完毕,再作《引言》时,那不屈的反抗的意志又在阴郁中涌动起来了。他写道,所在这楼外的世界与童话中的风景是不同的,有着大都市中的悲欢,“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的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他对大屠杀的暴露是明白的。这场“血的游戏”对他的刺戟实在太大了,扩大的血泊,使他根本无法绕开。然而,他说:“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 果然,在几部旧稿整理完毕之后,他一气写了系列新的杂感,就像一道拉开的闸门,简直倾泄一般写作,有时竟多达一天数篇,表现了一个老战士的强旺的生命力。 '返回目录' 。 最好的txt下载网
被梦境放逐的人(2)
这些杂文不同于《华盖集》及其续篇那种私人论战的文字,但是,他抨击的对象仍然是具体的,仍然是主人及其叭儿。他指出,这是“青年遭劫时期”,“是青年特别容易死掉的年头。”而可死之罪呢?都是随意强加的,“凡为当局诛者皆有罪。”在《扣丝杂感》中,有一段“包围新论”,论及权力者即“猛人”和包围者的关系,并由此推及中国历史的恒在的循环,是十分精到的。他说,无论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身边总有几个人把他围得水泄不通。那结果,在内使猛人变得日渐昏庸,成为傀儡;在外则使别人看不到猛人的本相,而只能经过包围者的歪曲的反映。中国之所以这样走老路,原因盖在于包围:不管猛人如何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包围的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于是统统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直到“龙驭上宾于天”,这时,包围者便离开这株已倒的大树,另寻别一个新猛人。至于民众,又如何呢?他在《答有恒先生》里写道:“民众的罚恶之心,并不下于学者和军阀。近来我悟到凡带一点改革性的主张,倘于社会无涉,才可以作为‘废话’而存留;万一见效;提倡者即大概不免吃苦或杀身之祸。古今中外,其揆一也。”在一个未经理性启蒙的社会里;群众的作用是可疑的。而中外的大独裁者,恰恰利用了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