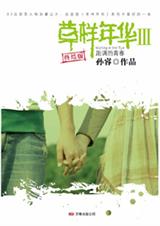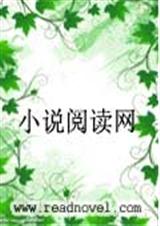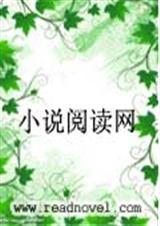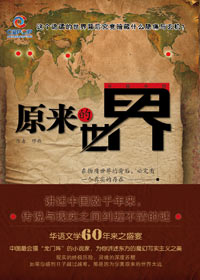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第1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偷搅肆硪煌罚诘厣献诺却蠡锕础�
可“七尺灰”一来我们就得受死。他精瘦精瘦的,平时不干活,养足了劲儿,偶尔到地里来,还常常是我们干了半天他才到,一来就腰也不直地锄地,他腿长,大步流星,你还得跟上。到快晌午的时候,肚子饿得咕噜咕噜叫。如果出早工的话,清早就开始干活了,早饭是担到地里吃的。我们知青的早饭还有干的,通常是一个玉茭窝窝,老乡就是稀薄的玉茭糊糊,里面能放几块山药就很不错了,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还吃野菜团子。到了中午大伙儿都饿得前胸贴后胸了。别的队都回家了,从我们地头经过时,“七尺灰”好像没看见,我们只好继续干。这时候我觉得太阳特别毒,地头特别长,肚子特别空。四周安静极了,只有我们7队社员在默默地“受”。
“七尺灰”每隔一段时间就这么整我们一次。我们队的社员都恨死他了,背后把他骂得狗血喷头,可没有一个人敢当面顶撞他,大家都怕他。他虽然年纪也就是30多岁,可是辈分不低。他能这样为所欲为,在大队里一定有靠山。他每次整我们,我都气得浑身冒火,在心里狠狠地骂他,反复说,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你不能这样对待我们。这句话就在嘴边,但我从来没有说出口来。作为知青,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负疚感,觉得对不起我们队老乡。
马:如果你当面顶撞他,他会不会因此压你,不许你回城,不让你上大学?
叶:我没想过。我想他没有那么大权力。可是我即使当面顶他,也不会起什么作用,他不会把我当回事儿。当然这样解释是为自己开脱。我觉得负疚是因为我连说话的勇气都没有。从小咱们受的教育是要敢于和恶势力作斗争,但在实际生活中我却这么软弱。
我做过一阵大队“电磨”的会计,“电磨”就是粮食加工厂。大概因为前几任会计手脚不干净,大队就让知青去管账。我每天在机器轰鸣的屋子里开关机器,称粮食收钱,一天下来,浑身上下都是粮食粉末,头发全是白的。在“电磨”的日子里,我开始明白“走后门”是怎么回事。常有干部、有时包括公社干部拿自家粮食来,放在一边,什么话也不说就走人了。你给不给他们加工?加了工收不收钱?就算我不给他们加工,和我一起干活的一个老乡早就把他们的粮食加工好了。有时快下班的时候几个干部一起来了,拿了粮食就走,没有二话。很快我就明白,他们是不会给钱的。跟我关系好的老乡,有的也把粮食悄悄放下,跟我点点头就走了。
渐渐地,我学会了判断每一种情况,不在加工厂我不会知道这中间的“学问”。干部的钱你是收不到的,只好认账,但是大部分人的钱你必须得收,否则加工厂就没收入了。在哪儿划一道线呢?对大部分老乡朋友,我只能管他们要钱,要不然我这个营生没法干。只有高典老汉,我就不收钱了。他实在太困难了,因为身体有病干不了重活,工分挣得少,家里负担又重。每天下班后结账时点着花花的票子,我的感觉很复杂:我实际上是给干部们走后门做了同谋,又不能帮助队里那些也很困难的乡亲们。至于收入上缴之后大队是怎么花的,有没有贪污,我就都不知道了。在加工厂干了几个月我就不干了,又回到队里去锄田。
无形的墙(1)
叶: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小后生经常问我们:“你们在城里看电影吧?溜马路吗?”想象城市的生活是他们永不疲倦的话题。他们想象城里人吃饱饭了没事干,穿得干干净净的,男男女女挎着胳膊,在大街上走来走去。这就是农村青年心目中的城市生活:“体面”,有闲。年纪大一些的老乡只是听,什么也不说,他们似乎已经不向往什么。我不记得我是怎么回答的,可是小后生们想象的城市生活画面留在了我的记忆里。每天顶着太阳弯着腰、锄着叶子已经开始剌人的玉茭,城市生活距离我也很遥远了。
马:城乡差别大概是我们每一个插队的人最强烈和最直接的感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农村会这样穷?
叶:我有好多疑惑:为什么老乡不热爱集体,反倒老想办法占集体的便宜,干活的时候能偷懒就偷懒;为什么越干越穷?“受”了一年,还是吃不饱穿不好?为什么干部和群众的对立情绪那么大?我已经感到公社制度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但是对这些问题,我没有去深想。当时听说有些爱思考问题的知青冬天回到北京,凑在一起,交流各地的情况,讨论这些问题,他们还看些理论方面的书籍,形成了自发的“地下沙龙”,这些都成为后来中国农村改革的种子。我很敬佩他们,但是我们村知青中没有这样的人。
马:听你讲起来,你们和老乡的关系还不错啊。
叶:个人都还可以,每个知青在村里都有自己的“朋友户”,逢年过节老乡到知青院叫我们去“吃请”的喊声此起彼伏。很多知青都学会了讲当地话,我说得最不好。刚去的时候我大概只能听懂60%左右的话,还得连猜带蒙。后来大家都学,成了风气,我们全县都是这样。前些年,我跟几个知青回村,在村口遇到第一个村里的人,他问我们是什么人,一个女生脱口用雁北话说:“忘球啦?”(把我们忘了?)我听了又想笑又想哭,当年的感觉一下子就回来了。
但是作为一个群体,我们和老乡之间存在着一道无形的墙。去山阴县插队的学生是女附中和男四中的——当年北京两所最好的中学。我们村的知青里不但干部子弟集中,而且高干子弟集中。有人开玩笑说在我们同学的家长中,能找到中共从一大到八大的中央委员,就是没有九大的。老乡们知道我们的家庭情况后说:“净是大疙旦”(大官)。我不喜欢这样一个组合,我那时已经十分不认同干部子弟那一套了。
马:那你怎么跟着这些人去了?
叶:是学校分的,除了一个“老初三”的,我和别人都不认识。下乡的高干子弟都是家里有问题的,没问题的很多都去当兵了。我们村一开始去了20多个知青,后来陆续又有来投亲靠友的,最多的时候有30几个人,其中好几个是“弟弟”。那时候一个家庭分散在几处太平常了,有的家长就尽可能让孩子们到同一个地方去插队,好互相照应。我弟弟的学校是去晋南,我爸爸妈妈让他跟我到雁北。有一阵我们家5口人在3个地方:我和弟弟在雁北,我爸爸在山西南部永济的新华社“五七干校”,我妈妈和我妹妹在北京。当时中国城市几乎家家“四分五裂”。我妈妈因为腿残废,没去干校,在北京给我们保住了个“窝”。我们村里有些同学在北京就没家了,还有的同学家长被关起来,多年没有音讯,生死不知。我们插队那几年,有个男生的父亲在干校突然死亡,至今闹不清是自杀还是他杀。我爸爸在干校打井,几乎被突然倒下的井杆砸死。这就是当年中国城市家庭的写照。由于我们村知青的背景,“家破人亡”的情形更加突出。
因为尽是些落难的“公子小姐”,大家普遍的心情是压抑和不满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接受再教育的心,反正也没别的出路,只能插队,就来了。第一年年底我们村知青中就有人走了,是去当兵,这是当时家里问题解决了的干部子弟通常的出路。这么一来,大家明白早晚有一天都能走,在农村插队无非是权宜之计。冬天地冻得硬梆梆,营生很少,很多人就回北京,一住几个月,春耕了再回来,像候鸟一样。 txt小说上传分享
无形的墙(2)
上河西女生在宿舍前合影。前排右一为玉诺儿,她是大队派来帮助知青做饭的“女儿”。后排右二为作者叶维丽。村里干部不“左”,从来不找我们的麻烦,和我们的私人关系也不错。我内心很希望我们村的知青是一伙做事的人,能够参与村里的事务,为老乡们做点儿事。我在黑龙江插队的同学和老乡相处得那么融洽,参与屯子里的公共事务,她们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在我们县别的一些村子里,知青有的当了队干部,有的当了会计、教师和赤脚医生。有个村的知青在村里几乎“夺了权”,大队小队的干部都有他们,在老乡中威信很高。而在我们村,除了个别男生,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融进村里的生活,也无意进去。有一度我认真地想要转到“干事儿”的村子去,但最终也没走。一想起在黑龙江的同学,我就惭愧不已。我恨自己无力冲破那堵无形的墙,有时恨得浑身燥热,但就是冲不破。
有个例子可以说明“墙”的存在。有一次两个知青要结婚,他们年龄都比较大了,在北京就是朋友关系。听说他们两人要在村里结婚,老乡们都很兴奋,觉得可以热闹红火一下了。结果没一个老乡被邀请,连村干部都没请,完全把门关上了,知青们自己开了一个party(聚会)。我想老乡们一定很失望,他们还准备“听房”呢。那两个知青结婚的时候我们已经到村里一年多了,认识很多人了,也不知道是谁决定不请老乡的。
马:有人提出异议吗?
叶:没有,我心里很不舒服,可什么话也没说。我们这些人里还有人号称要“解放全人类”呢。“解放全人类”是四中老红卫兵组织,男生中有几个人曾经和这个组织有关系。他们在自己的锄头上刻着“解放全人类”,每天上工扛着这么个锄头,我觉得特可笑。
到村里后不久,知青就分为两派。这种派系之争特别无聊,而有人却把它叫做“两条路线斗争”。两派知青的家庭背景相同,两派之间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分歧。我想是有个别男生权力意识特别强,习惯了“文革”中的派性斗争,就把它带到农村来了。两派都以男生为主,女生依附男生,我哪派都没参加。在很长一段时间,我“外人”的感觉非常强,既不是老乡中的一员,也不满意某些知青的拉帮结派,成了“两个世界”之外的人,一个人很孤单。
每派在一起最常做的事是“打平伙”,把从北京带来的挂面香肠之类凑在一起,再从老乡家买些豆腐、鸡蛋,做一顿好吃的解馋。我们平时的伙食干的是玉茭窝窝,稀的是玉茭糊糊或小米粥,粥里有时放山药蛋。雁北地区蔬菜种得少,老乡很少吃鲜菜,一年到头吃用洋白菜丝和胡萝卜丝腌的酸菜,叫“烂腌菜”,我们也跟着那么吃。刚吃的时候很不习惯,总觉得有一股酸臭味。刚去的那年吃不饱,有的男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就在伙房门口等着,向女生要吃不了剩下的。后来能吃饱了,但是没有油水。第一次在村里过年,伙房吃羊肉饺子,有的人先吃一轮,然后到外面去走路“帮助消化”,回去再吃第二轮、第三轮,没人把肠胃撑破了真是万幸。不知为什么,小米“养”女生,第二年以后女生都红润了一些,男生还是又黑又瘦。但就是这样,我眼看着我弟弟的身体一点一点往上蹿,撑破了一双又一双从家里带来的袜子,补他的破袜子是我的事。
每天吃饭的时候,大家端着玉茭糊糊碗就开始“精神会餐”,聊吃过的美味,还互相打赌一次能吃多少鸡蛋什么的,我记得一个男生说他能吃20个。我当时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