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十年·百姓影像-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牛: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可以算是你的第一个创作时期。你当时的代表作《春风已经苏醒》引起了轰动,也奠定了你在国内油画界的地位。那个时代,其实是对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等不正常的社会状态进行全面反思的时代,不论是绘画、文学、音乐,还是思想。《春风已经苏醒》这个作品在当时也是典型的代表作,对个人是,对时代也是。当时是怎么样一种创作背景?
何:《春风已经苏醒》是我研究生毕业时创作的。当时本身就准备创作与知青生活有关的题材,主题定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那时国外的油画开始进入中国,我们也在找寻国外大师的作品。我在《世界美术》杂志上第一次看到安德鲁?怀斯的画,震撼!立刻就决定用他的技法来画,画法和主题都定了,就把知青的形象改成了农民娃娃的形象,加上动物,加上一片草地。因为觉得怀斯的草画得很好。其实也不知道怀斯到底是怎么画的,就按自己的想象来画。这是我用怀斯的方法画的第一幅画。后来用这种方法画了差不多十年。
牛:这基本上形成了你最初的风格?
何:是的。整个80年代我基本都用这种技法在画。主要就是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我理解的自然的神秘性。其中很多结合了我下乡时候的印象,后来(主角)就变成了彝族人,背景很多都是大凉山的风景。
牛:在当时的美术界看来,你画中的技法胜过了所表达的意义。是这样吗?
何:我觉得画面效果就是我要表达的内容。我的画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的。没有那种情节性的主题,或者某种观念性的东西。我关注的是绘画本身的东西。
牛:80年代,思想与物质的禁锢陡然打开,很多思潮在翻涌,很多观念在创立。你在这十年之中都坚持着自己的风格和立场,为什么?
何:我始终是一个不喜欢跟潮流的人,只想照自己的想法画,主要是这样画自己很愉快,我想这也不算是坚持。
牛:有人把你80年代的作品称为“伤痕美术”的一个代表,你认不认同这种说法?
何:可能有点误解。当时“伤痕美术”在国内的兴起,也算是一种时代的潮流,是最前卫的。中国第一次出现了这种批判现实主义的绘画,也代表了那个年代的一批人的看法。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何多苓:享受着绘画、诗意以及边缘(2)
我的作品跟他们的只是形似,我的画并不是以社会批判为题材,也不是以社会批判为目的,主要是想表现内心的一些感受,跟政治背景没有大的联系。当然画的人物都是现实的人,但在题材上不带有批判性质。那是一种诗意的东西,个人化的表达。有某种文学性,这种文学性可以解释为诗意。不是故事性的,也没有情节。我一开始就与“伤痕美术”有很大的距离,跟罗中立的《父亲》这种类型有很大的距离,相似仅仅在于“乡土”上。
牛:你说的这种“乡土”,是和你当知青的经历有关?
何:肯定是。那时候虽然没有画画,但为后来画风的形成打下了思想基础。那时我就对自然界的壮观与神秘有兴趣,感到狂喜,自己完全融入其中。这种境界,这种审美倾向一直延伸到了我后来的创作中,顺理成章。恰好跟看到的怀斯的风格也结合起来了,也就形成了我近十年的画风。知青生活对我后来美学观点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画面来说,我跟时代并没有紧密的联系,因为我表现的东西都是很个人化的。但从观念来说,我和时代还是有联系。中国绘画从“文化大革命”时的宣传画到“伤痕美术”的批判,很快变为一种以自我表现为核心的形式。这样看来,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潮流中的一员。
一直到“,85新潮”,国内出现了观念绘画、行为艺术等。如果说把绘画作为个人思想的一种表达的话,我想我算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表达的方式很纯粹。我也是中国“新美术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吧。
牛:我记得80年代国内搞过一次人体绘画艺术展,引起了整个社会的轰动和讨论。应该说,整个80年代的艺术氛围还是很好的,大家经常谈的是文学、绘画、诗歌、音乐,经济意识还很淡,大家喜欢的是这种文化氛围。你觉得和现在比起来,那种氛围是不是更好一些?
何:也不能说更好。任何一个时代的大变革,总会提供很多机会。当时的口子刚打开,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吹进来的风都是很新鲜的,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很震撼。“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管是哪个领域。文学和美术可能是走在最前面的,诞生了一批很著名的画家,那个年代是一个造英雄的年代,很多人都受益于此,包括我自己。很多写小说的、搞艺术的、拍电影的,都出于那个年代。
现在主要是一个多元化的时期,多元化既成事实,每个人的表达权利受到充分肯定和尊重;当然,画的人也多了,竞争很激烈,路子也相对狭窄一些,因为每个领域都有许多人尝试,年轻的艺术家要找到自己的路更困难一些。
80年代是一个中国文化井喷的年代,禁锢那么多年,突然开放,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对绘画来说,它相对更自由一些,受到的禁锢更少。
牛:我们那时就非常羡慕画画的,很自由。想旷课就旷课,想留长发就留,生活方式也特立独行。
何:其实画画本身就是自我的行为,能不能展出是一回事,但创作过程是完全可以自我控制的。
牛:你这段时期大量的作品都是沿袭这种风格?
何:是的。简洁的构图,细致的刻画;与自然的对话,与内心的关系。内容基本都是受现代诗歌的影响,有超现实主义的,有印象主义的,也有象征主义的。在当时的80年代,我可以把诗歌翻译成某种绘画语言,最后直接用于绘画之中。因为我喜欢的,就是诗歌那种晦涩、朦胧的东西,以及它提供的象征符号和错位的感觉。不像小说那么明白,文学性那么强。换句话说,我是从现代诗歌中吸取了很多绘画的灵感。
牛:对于你来说,绘画就是写诗?
何:也可以说是“画诗”。两种艺术形式在我看来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市场年代:冲击心灵的底线
牛:你的画风产生比较大的变化是在90年代?
何:是。我80年代末去了美国,待了一年。那时候距离乡土的东西远了,没有直接的感受了,知青时代过去了。十多年来我完全处于都市之中,自己已经成了一个都市人,从知青的状态转换成了都市人的状态。
那时我在美国看了一些中国传统绘画、传统艺术。因为美国的博物馆里的很多好东西,在中国是看不到的。
何多苓:享受着绘画、诗意以及边缘(3)
牛:很奇怪,在美国看中国的传统艺术?
何:是,有些东西在故宫都看不到。其实此前我是不关心(中国传统艺术)的,我是画油画的,对这些都没关注过。那会儿只是对西方的油画很着迷。
在美国我看到了宋代的画、南朝的雕塑,很震撼。可能也和年龄有关系。中国文人到了一定岁数,他血脉中的中国传统基因就会显现出来。所以我在美国后期画的画已经离乡土甚远,主要画了一些个人感受的东西。
1992年回国的时候,马上就开始转换成了对中国符号的引用。比如“迷楼”系列,我抛开了过去所有的题材和技法,另起炉灶。
整个90年代就是在这种探索中度过的。
牛:因为出国产生的时空距离,你发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价值?
何:是这种远距离让我看清楚了,看到了中国的好东西。可能中国的文化人到了某一年龄阶段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年龄、阅历的沉淀,在我的画里面都成了抽象的表现。但我还是坚持一点——远离大的政治背景。我并没有真正刻画时代。所谓的时代精神,在我的画中主要体现在自我意识,以及(技法、题材)变革。
牛: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从社会到经济、文化都在迅猛发展,改革开放更加深入,国内的艺术品市场也开始逐渐形成,有了拍卖会,也有艺术品商人在活动。当时你怎么看待这一潮流?
何:一开始我们都不知道画也是一种商品。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有台湾的收藏人士到内地收画,我在美国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些收藏家,那时候就卖出了自己的第一批画;回国后发现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已经开始形成了。那时候画廊还很少,买家一般直接找画家去买,且以个人收藏为主。
牛:据说你在美国还很反感商业绘画?
何:对。我很不适应画那种商品画,还给朋友写信谈了这个问题,在国内一些刊物上也发表过这种看法,对绘画的商品化与市场化进行激烈批判。现在看来是非常偏激的。
牛:你是希望保持绘画的纯粹性?
何:想为艺术而艺术。(笑)我对绘画理直气壮地成为商品很不适应。当时的确很幼稚。现在看来,既然有人消费绘画,消费艺术,那它就是一种商品。在国外,艺术品分了很多市场,绘画也分了很多档次,每个档次都有自己特定的消费群,最后形成了一个很完善的绘画市场。
中国绘画市场的形成也很快,从只有画家开始,很快就有了一切。既然全球化的过程开始了,绘画也不可避免地进入了经济领域。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就形成了当下的格局。
牛:你算是较早一批被画商看中的画家吧?
何:算其中之一吧。其实陈丹青、艾轩他们更早一些。那时候已经有画商在收藏中国画家的作品了,价格很便宜。那些收藏家和画商收的种类也很多,有些着重收中国的观念性绘画,着眼于美术史;有些看重的是中国绘画的写实性;也有对中国民俗感兴趣的,对中国乡土感兴趣的。每个品种都有它的市场。不过因为买家是他们,所以他们的兴趣和倾向也影响了一些中国画家的题材与技法。中国大的社会背景、传统符号都容易受到国外收藏家的关注。当时一流的作品很多都外流了。国内也没有够实力的收藏家,开价太低了买不到画,美术机构也不能左右画家的作品。
牛:你的作品里对个体的描绘很多,你也说过自己基本上不关注群体,是不是和你个人的审美取向有关?
何:我主要是对细微的东西感兴趣,不喜欢喧嚣,不喜欢刺激,不喜欢大的场景。宁可画一些肖像性质的作品,很安静地画,让人也可以很安静地看,冷静地看,探索这种细节和人的内心世界。而且(主角)以女性为主,因为女性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充分,表情和肢体语言都特别微妙,也很唯美,画起来难度很大。我喜欢向自己挑战。这些东西最后就成了我绘画的内容,形式和内容结合起来了。
我把自己的绘画看成是独立的领域,我刻画的是内心世界,甚至不是我自己的,是虚拟的某种内心世界。我把它看成是至高无上的,我自己的情绪都不一定进入我的绘画。我想它是一种更高的东西,高于现实。
何多苓:享受着绘画、诗意以及边缘(4)
牛:你把创作和现实分得很开?
何:和我的生活也是分开的。
牛: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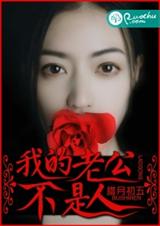
![[韩娱]我的外星女友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0/62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