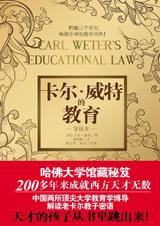于絮尔·弥罗埃-第22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么再见了,”萨维尼安说。“这个星期我要留在巴黎办几件事,我要作种种准备,买书籍,买数学上用的仪器,还得请大臣帮忙,给我最优越的条件。”
于絮尔和干爹把萨维尼安直送到铁门口,看他回进屋子,又看他出来,背后跟着蒂安奈特提着一口箱子。
于絮尔问干爹:“你既然有钱,干吗要逼他进海军呢?”
医生笑了笑回答:“这样下去,我看不久连他欠的债都要我负责了。我没有逼他;可是孩子,一套军服,一个凭军功挣来的十字勋章,可以抹掉一个人多多少少的污点。六年之内他可能当上舰长;我对他的要求也不过如此。”
“但是他可能遇到危险呀,”她说着,睑都白了。
“情人象酒徒一样,自有他的神道保佑,”医生带着说笑的口气回答。
孩子瞒着干爹,夜里叫布吉瓦勒女人帮忙,把她又长又好看的淡黄头发剪下一束,正好编一条辫子。隔了一天,她缠着音乐教师施模克老人,要他监督巴黎的理发匠防止调换,还得赶着下星期日把辫子编好。
萨维尼安从巴黎回来,告诉医生和他的干女儿说,志愿书已经签了,二十五日要赶到布雷斯特。医生约他十八日吃晚饭,他在医生家差不多消磨了整整两天。虽是米诺雷叮嘱两个情人的话入情入理,他们在本堂神甫,法官,奈穆尔的医生和布吉瓦勒女人面前,仍不由自主的流露出他们心心相印的感情。
老人说:“孩子们,你们得意忘形,不会把快乐藏在心里。”
到了萨维尼安的本名节,两人先在弥撒祭中彼此瞟了几眼;然后萨维尼安在于絮尔窥伺之下,穿过街,到她的小园中来了。他们俩差不多是单独相对。老人有心放任,坐在书
房里看报。
萨维尼安道:“亲爱的于絮尔,你可愿意使我的节日过得比我在母亲面前更快活,给我一个新生命吗?……”
于絮尔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我知道你要的什么。你瞧,这就是我的答复,”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辫子来递给他的时候,快乐得直打哆嗦,“你既然爱我,请你把这个带在身边。这礼物表示我的生命和你的生命连在一起了,但愿它使你逢凶化吉!”
医生见了,对自己说着:“啊!这小丫头!竞给了他一根辫子。她怎么弄起来的?把多美的淡黄头发剪下一把……那不是把我的血都给了他吗?”
萨维尼安吻着辫子,瞧着于絮尔,忍不住掉了一滴眼泪,说道:“临走以前,我要你切实答应我永远不嫁别人,你不会觉得我要求过分吗?”
于絮尔红着睑回答:“你在圣佩拉日的时候,我曾经到监狱的墙下徘徊;你要求我的诺言,倘若你还嫌我说得不够,我就再说一遍罢:我永远只爱你一个人,永远只属于你一个人。”
萨维尼安看见于絮尔半个身子掩在藤萝中间,忍不住把她搂在怀里,在她额上吻了一吻:她轻轻的叫了一声,望凳上倒了下去。萨维尼安正挨在她身边道歉,医生已经站在他们面前。
他说:“朋友,于絮尔是个极娇嫩的孩子,对她话说得重一点就有危险。你应当把爱情抑制一些才对!唉!要是你爱了她十六年,你单是听到她说话就会满足了。”他这样补充是针对萨维尼安第二封信里的一句话的。
两天之后,萨维尼安动身了。虽然他经常来信,于絮尔却害了一种表面上没有原因的病。好比美好的果子被虫蛀一样,她的心受着一个念头侵蚀。胃口没有了,血色也没有了。干爹第一次问她觉得心里怎么样,她说:
“我想看看海景。”
“十二月里可不便带你上海港去,”老人回答。
“那么终有一天能去的了?”她说。
一刮大风,于絮尔就着急;不管干爹,神甫,法官,把陆地上的风和海洋上的风分辨得多么清楚,她总以为萨维尼安遇着飓风。法官送她一张雕版的图片,印着一个全副军装的候补少尉,使她快活了几天。她留心读报,以为萨维尼安所参加的那次巡逻,报上必有消息。她拼命看库柏…的海洋小说,还想学航海的术语。这许多执着一念的表现,在别的女子往往是装出来的,在于絮尔是完全出于自然;甚至萨维尼安每次来信,她都在梦中先看到而在第二天早上向大家预告的。
这些在医生与神甫都不以为奇的预感第四次发生的时候,她对干爹说:“现在我放心了,不管萨维尼安离得多远,他要受了伤,我一定立刻感觉到。”
老医生左思右想的出神了;法官和神甫看他睑上的表情,认为他一定想着些很痛苦的念头。
他们等于絮尔不在面前的时候,问老人:“你怎么啦?”
老医生回答:“她将来怎么活下去啊?一朵这样纤巧,这样娇嫩的花,遇到感情的打击,是不是抵抗得住呢?”
虽然如此,这个被神甫戏称为小幻想家的姑娘,用功得很;她知道学识丰富对一个上流社会的女子多么重要;除了练唱,研究和声与作曲以外,她把余下的时间都用在书本上,那是夏勃隆神甫在她干爹丰富的藏书中挑出来的。她尽管很忙,精神上仍旧很痛苦,只是嘴里不说出来。有时她对萨维尼安的窗子呆呆的望上半天。星期日望过弥撒,她跟在波唐杜埃太太后面,很温柔的瞧着她;虽然老太太心肠冷酷,于絮尔仍因为她是萨维尼安的母亲而爱着她。她对宗教更热心了,天天早上都去望弥撒,因为她深信自己的梦都是上帝的恩赐。
老医生眼看相思病给她的伤害,心中很怕,便在于絮尔生日那天,答应带她上土伦去参观舰队远征阿尔及尔的开拔仪式,事先不让萨维尼安知道。法官和神甫,对这次旅行的目的替医生守着秘密,仿佛只是为了于絮尔的健康出门的,但一般承继人已经为之大惊小怪了。于絮尔和穿着候补少尉军服的萨维尼安见了面,参观了壮丽的旗舰,舰上的海军上将就是受大臣嘱托,特别照顾萨维尼安的人。然后她听了爱人的劝告,上尼斯去换换空气,沿着地中海滨直到热那亚;到了热那亚,她得到消息,舰队已经安抵阿尔及尔,很顺利的登陆了。
医生本想继续在意大利观光,一方面让于絮尔散散心,一方面也多少能补足她的教育:大艺术家生息的土地,多少不同的文明留下光华的遗迹的土地,本身就有一种魔力,再加风土人情的比较,当然能扩展她的思想。但医生听到国王跟
那有名的一八三0年的国会冲突的消息,不得不赶回法国。干女儿出门一趟,变得生气勃勃,非常健康,还把萨维尼安服役的那艘军舰,带了一具小巧玲珑的模型回来。
一八三0年的选举,使米诺雷的承继人都有了立足点。在但羡来和古鄙策划之下,他们在奈穆尔组成一个委员会,推出一个自由党人…做枫丹白露区的候选人。玛森很有力量操纵乡下的选民。车行老板的佃户中间,五个是有选举权的。迪奥尼斯也拥有十一票以上。克勒米耶,玛森,车行老板和他们的党羽,最初在公证人家集会,以后经常在那儿见面了。米诺雷医生回来的时节,迪奥尼斯的沙龙已经变做承继人们的大本营。法官和镇长联合起来抵抗自由党,他们虽有四乡的贵族支援,仍旧被反对派打败;但打败以后,他们倒反更团结了。这样的对抗使奈穆尔破天荒第一次有了两个党派,而米诺雷的几个承继人居然占了重要地位。正当邦格朗和夏勃隆神甫把这些情形告诉医生的时候,查理十世已经从朗布依埃宫堡出奔,逃往瑟堡去了。但羡来·米诺雷的政见是追随巴黎的律师公会的;他从奈穆尔约了十五个朋友,归古鄙率领,由车行老板供给马匹,在七月二十八的夜里赶到巴黎。袭击市政厅的一役,就有古鄙和但羡来带着这批人马参加。事后,但羡来得了荣誉勋位勋章和枫丹白露助理检察官的职位。古鄙得了七月十字勋章。迪奥尼斯当选为奈穆尔镇长,接替前任的勒弗罗;镇公所的委员包括副镇长米诺雷勒弗罗,玛森,克勒米耶,和迪奥尼斯沙龙的全部党羽。邦格朗靠着儿子的力量才保住原职;那儿子作了默伦的检察官,和勒弗罗小姐的亲事大概也有希望了。
医生听说三厘公债的行市跌到四十五法郎,便搭着驿车上巴黎,把五十四万法郎买了不记名公债。剩下二十七万左右现款,他用自己的姓名买了同样的证券:这样,外边只知道他每年有一万五千进款。老教授姚第遗赠于絮尔的本金,和九年之间所生的八千法郎利息,都用同样的方式存放;老人又添上一笔小款子,把这份薄产凑成一个整数,让于絮尔有一千四百法郎收益。老妈子布吉瓦勒听着主人劝告,也把五千几百法郎积蓄买进公债,每年有三百五十法郎利息。这些跟邦格朗商量好的,非常合算的调度,因为政局混乱,居然没有一个人知道。
局势大定以后,医生又买下贴邻的一所小屋子,把它拆了,把自己院子的界墙也拆了,另外盖起一间车房一间马房。拿一笔可有一千法郎利息的本金起造下房,在米诺雷所有的承继人眼里简直是发疯。这桩被认为发疯的行为,在老人的生涯中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那时的车辆马匹,价钱跟白送差不多:医生便从巴黎带了三匹骏马和一辆四轮篷车回来。
一八三0年十一月初的一个下雨天,老人第一次坐了四轮篷车去望弥撒;他下了车,正在搀扶于絮尔,镇上的人已经全部赶到广场上,为了要瞧瞧医生的车,盘问一下马夫,也为了要把医生的干女儿批评一番:据玛森,克勒米耶,车行老板,和他们的老婆的意见,老叔的荒唐全是野心勃勃的小姑娘撺掇出来的。
古鄙嚷道:“喂,玛森,有了马车了!你们的遗产去路很
大,嗯?”
站在牲口旁边的马夫,是米诺雷车行里一个领班的儿子;车行老板对他说:“卡比罗勒,你要的工钱大概不小罢?八十四岁的东家用不了多少马蹄铁的了。两匹马花多少钱买的?”
“四千法郎。车子虽是旧货,倒花了两千;可是很漂亮,车轮是把挡的。”…
“卡比罗勒,你那句话怎么说的?”克勒米耶太太问。
古鄙抢着回答:“他是说白揭。那是英国人出来的玩意儿。你瞧,外边什么都看不见,样样都包在里头,多漂亮,又不会勾着人的衣衫,套在轴梗头上的那种难看的方铁帽也取消了。”
“什么叫做白揭?”克勒米耶太太很天真的问。
古鄙道:“怎么!你不想揭些便宜吗?”
“啊!我明白了,”她说。
“嗨!不是的,”古鄙道,“你是个老实人,我不好意思哄你;真名叫做百挡脱,因为梢子藏在里头。”
“对啦,太太,就是这意思,”卡比罗勒说。古鄙态度一本正经,连马夫也上当了。
克勒米耶嚷道:“不管怎么样,反正是一辆挺讲究的车;不是财主,谁撑得起这样的场面!”
古鄙道:“小姑娘抖起来啦!她这办法不错,教你们也享享福。喂,米诺雷老头,干吗你不弄几匹好马,买几辆篷车?你不争这口气吗?换了我,要不高车大马,摆摆威风才怪呢!”
玛森问:“喂,卡比罗勒,我们的老叔这样铺张,可是小姑娘撺掇的?”
卡比罗勒回答:“不知道;可是她在家里就象东家娘一样。天天有各种各样的教师从巴黎来。听说她还要学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