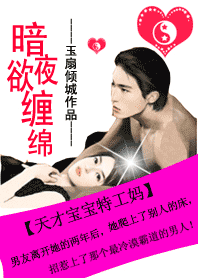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第15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就算废了。经过最初的接触失败以及连续失败后,我开始拿出了二皮脸精神,没事儿就去,有事儿办完绕道也去。我就当是谈恋爱追她了。
终于,她的心灵之门被我打开了。
……
我:“我一直就想问你,但是没敢问。”
她笑:“我不觉得你是那种胆子小的人。”
我:“嗯……可能吧。我能问问你为什么用那么多胶条把电视机封上吗?”
她:“因为他们(指她父母)在电视台工作。”
我:“不行你得把中间的过程解释清楚,我真的不懂。”
她是个极聪明的女孩,老早就认字,奶奶教了一点儿,不清楚自己怎么领悟的。5岁就自己捧着报纸认真看,不是装的,是真看。幼儿园老师觉得好笑就问她报纸都说什么了,她能头也不抬的从头版标题一直读下去,是公认的神童。她父母都在电视台工作,基本从她出生父母就没带过,是奶奶带大的,所以她跟奶奶最亲。在她11岁的时候奶奶去世了,她拉着奶奶的手哭了一天一夜,拉她走就咬人,后来累的不行了昏过去了,醒了后大病一场。从此就不怎么跟人说话。父母没办法,也没时间,几个小保姆都被她轰走了。不过天才就是天才,一直到上大学父母都没操心过。毕业后父母安排她去电视台工作,死活不去。自己找了份美工的工作。每天沉默着进出家门,基本不说话。如果不是她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我猜她的父母依旧任由她这样了。会有这样的极品父母吗?我告诉你,有,是真的。
她皱了下眉:“他们做的是电视节目,我讨厌他们做的那些,所以把电视机封上了。”
我:“明白了,否则我会一直以为是什么古怪的理由呢,原来是这样啊。”
她:“嗯,我以为你会说我不正常,然后让我以后不这样呢。”
我:“封就封了呗,也不是我家电视,有啥好制止的。”
她笑了。
我:“那你把门锁换了,为什么就给你爸妈一把钥匙呢?”
她突然变得冷冷的:“反正每次他们就回来一个,一把够了。”
我:“哦……第二个愿望也得到满足了,最后一个我得好好想想。”
她再笑:“我不是灯神。”
我:“最后一个我先不问,我先假设吧:你总戴着这个黑镜架肯定不是为了好看,应该是为了有躲藏的感觉吧?”
她:“你猜错了,不是你想的那种心理上的安慰。”
我愣了下:“你读过心理学……”
她:“在你第一次找我之后,我就读了。”
原来她也在观察我。
我:“最后的愿望到底问不问镜架呢?这个真纠结啊……能多个愿望吗?”
她:“当然不行,只有三个。你要想好到底问不问镜架的问题。”看得出她很开心。
我凭着直觉认为镜架的问题很重要。
我:“……决定了:你为什么要带着这个黑镜架?”
她:“被你发现了?”
说实话我没发现,但故作高深的点头。
她认真的想了想:“好吧,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是我最大的秘密。”
我:“嗯,我不告诉别人。”
她:“我戴这个镜架,是为了不去看到每天的颜色。”
我:“每天的颜色?”
她:“你们都看不到,我能看到每天的颜色。”
我:“每天……是晴天、阴天的意思吗?”
她:“不,不是说天气。”
我:“天空的颜色?”
她:“不,每天我早上起来,我都会先看外面,在屋里看不出来,必须外面,是有颜色的。”
我:“是什么概念?”
她:“就是每天的颜色。”
我:“这个你必须细致的讲给我,不能跟前几个月似得。”
她:“嗯……我知道你是好意,是来帮我的,最初我不理你不是因为你的问题,而是你是他们(指她父母)找来的。不过我不是有病,我很正常,只是我不喜欢说话。”
我:“嗯,我能理解,而且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才会认为你不正常的。例如电视机的问题和你把鱼都放了的问题。”
(受字数限制,本篇未完待续)
她曾经把家里养的几条很名贵的鱼放了。基础动机不是放生,比较复杂:因为养鱼可以不像养猫狗那样定时喂或者特别的关注,养鱼现在啥都能自动,自动滤水,自动投食器,自动恒温,有电就可以几个月不管,看着就成了。她觉得鱼太悲哀了,连最起码的人为关注都没有,只是被用来看,所以放了。那是她不久前才告诉我的。
她:“嗯,不过……我能看到每天的颜色的事儿,我只跟奶奶说过,奶奶不觉得我不正常,但是你今后可能会觉得我不正常。”
我:“呃,不一定,我这人胆子不小,而且我见过的稀奇古怪人也不少。 ‘每天的颜色’是我的第三个愿望的解释,你不带反悔的。”
她:“……每天早上的时候我必须看外面,看到的是整个视野朦胧着有一种颜色。例如黑啊,黄啊,绿啊,蓝啊什么的,是从小就这样。比方说都笼罩着淡淡的灰色,那么这一天很平淡;是黄色这一天会有一些意外的事情,不是坏事,也不是好事。如果是蓝色的话,这一天肯定会有很好的事情发生,所以我喜欢蓝色;如果是黑色就会发生让我不高兴的事儿。”
我:“这么准?从来没失手过?”
她笑了:“失手……没有失手过。”
我:“明白了,你戴上这个镜架就看不见了对吗?”
她:“嗯,我上中学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戴上这种黑色的镜架就看不到每天的颜色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好像你刚才没说有粉色?对吧?”
她变得严肃了:“我不喜欢那颜色。”
她房间里一样粉色或者红的的东西都没有。
我:“为什么?”
她:“粉色是不好的颜色。”
我:“呃……你介意说吗?”
她:“如果是粉色,就会有人死。”
我:“你认识的人?”
她:“不是,是我看到一些消息。报纸上或者网上的天灾人祸,要不同事同学告诉我他们的亲戚朋友去世了。”
我:“原来是这样……原来粉色是最不好的颜色……”
她:“红色是最不好的。”
我:“哦?红色?很……很不好吗?”
她:“嗯。”
我:“能举例吗?如果不想说就说别的;对了有没有特复杂你不认识的颜色?”我不得不小心谨慎。
她:“就是因为有不认识的颜色,所以我才学美术的……我只见过两次红色。”
我:“那么是……”
她:“一次是奶奶去世的时候,一次是跟我很好的高中同学去世的时候。”
我:“是这样……对了,你说的那种朦朦胧胧的笼罩是象雾那样吧?”
她:“是微微的发着光,除了那两次。”
我觉得她想说下去,就没再打岔。
她咬着嘴唇犹豫了好一阵:“奶奶去世那天,我早上起来就不舒服,拉开窗帘看被吓坏了,到处都是一片一片的血红,很刺眼。我吓得躲在屋里不敢出去,后来晚上听说奶奶在医院不行了,我妈带我去医院,我都是闭着眼哭着去的,路上摔了好多次,腿都磕破了。妈还骂我,说我不懂事……到了医院,见到奶奶身上是蓝色的光,可是周围都是血红的,我拉着奶奶不松手,只是哭……我怕……奶奶跟我说了好多……她说每天的颜色其实就是每天的颜色,不可怕。她还说她也能看到,所以她知道我没有撒谎。最后奶奶告诉我,她每天都会为我感到骄傲,因为我有别人所不具备的……最后奶奶说把蓝色留给我,不带走,然后就把蓝色印在我手心里了……每当我高兴的时候,颜色会很亮……我难过的时候,颜色会很暗……我知道奶奶守护着我……”
她红着眼圈看着自己右手手心。
我屏住呼吸默默的看着她,听着窗外的雨声。
过了好一阵,她身体慢慢放松了。
她:“谢谢你。”
我:“不,应该谢谢你告诉我你的秘密。”
她:“以后不是秘密了,我会说给别人的。不过这个镜架我还会戴着,不是因为怕,而是我不喜欢一些颜色。”
我:“那就戴着吧……我有颜色吗?”
她想了想着我的外套:“那看你穿什么了。”
我们都笑了。
作为平等的交换,我也说了一些我的秘密,她笑的前仰后合。
真正松一口气的其实是我。我知道她把心理上最沉重的东西放下了,虽然这只是一个开始。
临走的时候,我用那根蓝色的笔又换来她的一个秘密:她喜欢下雨,因为在她看来,雨的颜色都是淡淡的蓝,每一滴。
到楼下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她正扒着窗户露出半个小脑袋,手里挥动着那只蓝色的笔。
我好像笑了一下。
走在街上,我收起了伞,就那么淋着。
雨默默的。
第20篇《最后的撒旦》
我:“我看到你在病房墙壁画的了。”
他:“嗯。”
我:“别的病患都被吓坏了。”
他:“嗯。”
我:“如果再画不仅仅被穿束身衣,睡觉的时候也会被固定在床上。”
他:“嗯。”
我:“你无所谓吗?”
他:“反正我住了一年精神病院了,怎么处置由你们呗。”
我:“是你家人主动要求的。”
他:“嗯。”
我:“是不是很讨厌我?”
他:“还成。”
我:“那你说点儿什么吧?”
眼前的他是个20岁左右的年轻男性,很帅,但是眉宇间带着一种邪气,我说不好那是什么。总之很不舒服——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
他抬眼看着我:“能把束身衣解开一会儿吗?”
我:“恐怕不行,你有暴力倾向。”
他:“我只想抽根烟。”
我想了想,绕过去给他解开了。
他活动了下肩膀后接过我的烟点上,陶醉的深深吸着:“一会你在给我捆上,我不想为难你。”
我:“谢谢。”
他:“我能看看你那里都写了什么吗?”他指着我面前关于他的病例记录。
我举起来给他看,只有很少的一点观察记录,他笑了。
我:“一年来你几乎什么都没说过,空白很多。”
他:“我懒得说。”
我:“为什么?”
他:“这盒烟让我随便抽吧?”
我:“可以。”
他:“其实我没事儿,就是不想上学了,想待着,就像他们说的似得:好逸恶劳。”
我:“靠父母养着?”
他的父母信奉天主教,很虔诚的那种。从武威(甘肃境内,古称凉州)移居北京前N代都是。
他:“对,等他们死了我继承,活多久算多久。以后没钱了就杀人抢劫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