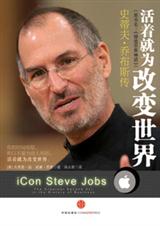我要活着-第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昨天的少先队员会议上,莉萨对于已经离开先锋队的女生,也包括我,散布谣言,恶意中伤。反正本来就没人喜欢她,现在她更不受欢迎了。课间休息时我们商量了很久,决定孤立她。今天,几乎所有人都一致支持我们。噢,我们会报复她的!决不会让她嘲笑我们,我们要让她为自己的尖牙利齿而后悔。被全体同学孤立可不是开玩笑!
学生必须加入少年先锋队——一种根据英国人贝登堡发起的童子军运动而建立的共产少年俱乐部。1922年由第五届共青团团代会设立,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教导10至14岁的学生遵纪、勤劳,有道德心与集体观念。少年先锋队与童子军有类似的仪式,也有不同的“时刻准备着”的格言。活动内容包括行军、唱歌,还有夏令营。离开先锋队或是拒绝成为其中的一员是公然反抗的表现。
1933年9月28日
作业——天哪,布置了好多作业。一点儿也不顾虑我们青少年,不想想我们也是人。那个叫什么布勃诺夫的家伙他在报纸上登文章,说有必要提高学习水平和纪律水平,但却没人理解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其实他们是在拖我们的后腿。我学得比以前更差了,兴趣全无,学习变得既没有意义又让人厌恶。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1884-1934年),人民*长,负责上世纪30年代的教育改革。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1933年10月17日
今天,喀秋莎和我一起走着去新圣女修道院。当我们走近时,不得不在路的转角停下脚步,等着一辆车转弯过去。这辆车看上去很奇怪。从远处看像是救护车或是用来运送病人的车——大大的窗子,车里灯光很亮……它缓缓从我们身边开过,离得很近,所以我看清了坐在凳子上靠着车壁的几个人。大约有五六个,两个平民打扮,其余的穿着制服。
他们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也一动不动,用奇怪的眼光打量街上的人们,既紧张又专注。'一行字被划掉'有个离我们最近、靠窗而坐的士兵经过的时候一直看着我们,后来甚至还转过头继续看。那真的是他吗?不可能,我们一定是搞错了,肯定错了!我不相信,就算是现在我也不完全相信。我们加快了脚步。快,快!我们得及时到达修道院,为了赶上他。
我们几乎在跑了,终点站有许多人。间距很大的街灯发出微弱的光,给周围裹上了一层忧郁。喀秋莎和我穿过墓地的门。'划掉一行'越过狭窄的大铁边门,能看到门口的柏油路偶尔有人影穿过。右边能依稀辨出是工人们的木营房。我们的面前是通向池塘的下坡路,路上很黑,空无一人,沿着河是厚厚的修道院外墙。黑色的垂柳依偎在池面上,远处还能看到一长排明亮的灯——那是堤防。
空无的夜色真叫人心生恐惧。我们站在大门边的路上,低声交谈,几乎在耳语。“那辆车说不定就在墙后面,停在池塘边,那里没人。”可是那里黑得太吓人了,我们不敢再走过去,只能站在这里,小声说话,等着有人经过这条小径。终于,有个人经过我们身边,向着池塘走去。
我们跟在他后面,爬上了陡峭的坡,黑色斑驳的墙看上去很可怕,池水纹丝不动,映射出街灯的光,远处的对岸还有房屋。在我们身后,可以清楚地听到女人或小孩的声音,这让我们的胆子大了些,就加紧了脚步直到转弯。城里的灯光照不到这么远,这里简直伸手不见五指。前面还能听到叫喊声和男人们的谈话声。
“我们回去吧!反正什么也干不了。”我们按原路慢跑回去了。
重重的脚步声在门拱下发出回音。路边有紧紧挨着生长的浓密冷杉。看不见坟墓与十字架。一切都是废墟。陈旧的白色教堂的钟楼在黑暗中显得特别清楚,钟楼顶上闪着一点一点微弱的光。几棵蓝色的冷杉挺拔高耸在一小块有着金色圆顶的白色地下室周围。我们当时究竟想过去干吗呢?
据说斯大林要去新圣女修道院坟场为他妻子阿利卢耶娃扫墓。她们看到的极有可能就是他。
1933年10月20日
爸爸有个好朋友名叫彼得?伊万诺维奇'尼娜父亲的好友兼前任同事,管理尼娜家合作企业的资金'。我记得第一次见他时他坐在出纳桌上。后来他因隐藏自己的真实姓名而被流放到了北方。在那里过了六年,和爸爸差不多同一时间回来。两年前的某个春日,他来到我们家里。是我开的门,他脱下外套时好像很不好意思——或者更可能是尴尬,然后把一副灰色手套作为礼物硬塞到我手里,“来,拿着,会有用的。”
我接过手套谢了谢他。我一边轻蔑地瞥了一眼手套,一边心里在想:“他是疯了还是什么?”那是一副既普通又便宜的手套,手指对我来说还太长了。因为觉得讨厌,我就把它们塞进了抽屉最里面的角落里,还把其他东西堆在了上面。
这件事我记了很久。尽量不去想他,每次想到他就觉得不舒服。真该把那段奇怪的插曲抛之脑后:在其他任何方面彼得都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人。他说话很慢,总是拖长了音,好像唱歌似的。他的脸显得平静又和善,甚至有点儿迟钝。
1933年10月30日
今天本来不上课的……盼今天已经盼了整整五天了,然而……生活有时候真是糟糕。今天对我来说已经全毁了。9点我得到学校,喀秋莎十分钟后来,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人活着真惨,总有这么多的矛盾。没有真理,没有公正,到处都是谎言和欺骗。甚至连真理里面也存在谎言,一切都有谎言的影子,而且会永远这样下去。永远看不到有这样的时候:世上人人平等,没人有权强迫或羞辱其他人,强者不奴役别人,弱者不再没有权益。
生活是场战争。战争里,强者永胜,还被吹捧上了天,弱者则在他的脚下卑躬屈膝,摇尾乞怜。女人又是什么?女人就像一条想要和主人平起平坐、却达不到目标的一条狗。女性解放运动又是什么?那是海市蜃楼,一场幻觉罢了。
与划出这段话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所相信的恰恰相反,尼娜并不认为女性低人一等——显然这里运用了讽刺手法。
1933年11月8日
如果没有休息过我一定比现在好得多。如果一直关在笼子里也罢了,偏偏他们把我放了出来,让我伸展了翅膀,呼吸了新鲜的空气,接着又把我关回去。想到今年年初我对学校的看法就觉得奇怪可笑,那个时候学习好容易,也很有意思。我有许多的计划和希望——想想两个月前自己有多天真。现在呢?现在我又变成什么样了?没力气好好学习,但不学习又不是个办法。
去年那样的沮丧如今又来了,不知为什么,这次觉得轻松点儿了。我不再一连几天闷声不响,为伤痛而退缩,有时候我甚至花好多时间告诉妈妈和爸爸学校里的事,还对着他们诅咒我的整个的生活。老天,活着真可怕!要是学校被烧掉,我们被送回家来我才高兴呢,真的。我现在什么也做不了,欠了好多作业,还在继续欠着。怎么才能改变这可怕的生活呢?这样的生活常常让我渴望那些逝去的好日子,那段时间不需要学习,整天随心所欲地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今年十月的假日过得有点儿奇怪。10月6日,莉莉娅和我去了梅里剧院看《柳博芙?亚罗瓦娅》'康斯坦丁?特列尼奥夫(1876-1945年)1926年的戏剧作品'。很久没去剧院了,最近反而觉得不太习惯,一点儿都不想上剧院看戏,可现在却很想多去看看。是的,真想多去去。今天之前,我还从来没见识过真正的演员——以前倒是看过好的表演,却没有一次演得像这次这么精彩。真的太棒了!
人只可能在别人的生活中感受生活。不再属于自己,也不再是你自己,却能感受与经历其他人的感觉。我从来不怀疑有人可以演得那么真实,一点儿不自然与矫揉造作的痕迹也没有。不,我简直无法描述这出剧带给我的强烈震撼!中场休息时,我一个人坐在那里神思恍惚,不停想象着柳博芙?亚罗瓦娅的样子,从她的声音里能听出泪水与苦难。噢,天哪!她'女演员帕申那娅'演得太好了!还有亚偌瓦中尉!当他双手抱头说着:“柳博芙!我离不开你”时,声音颤抖得多么厉害!
看着他们的时候我难受死了,和他们一起受苦,为他们而难过。走出剧院后,我自己的生命好像变得更可耻,更让人厌恶了……
1933年11月9日
今天没去上课,在家里待了一整天。外面下着雪,很想出去逛一圈,但是我不能,没时间去……我为什么要折磨自己?为了得“优秀”一连几天坐在这里做功课。总之,我忘了去年做过的所有事,不比阿尔卡记得多多少。我本来也可以抛开这一切,管它及格不及格呢,整天自由自在的:想散步的时候就出去走走,想玩游戏,画画或是写作都可以。那才叫棒呢!但是……我知道不能放弃学习,我无法忍受自己的成绩比伊琳娜或是其他同学差。凡事都想争第一的模糊渴望已经成了我身上重要的一部分——我太有野心了。
一直在思考怎么合理安排时间,用不着学很久也能考到好成绩。我可以在学校完成所有的作业;少在考试前临阵磨枪,少和同学胡闹就行了。再过一两个月我就习惯了,不会觉得别扭。去年我还能安心地睡上一觉,今年却连这个时间都没有了。对学习与学校的憎厌也一天比一天强烈。我梦想着能早日摆脱它们,却发现自己不经意间已经在这种枯燥的生活里越陷越深,就算有机会,也没办法放弃了。
有时候真想出门散步,在雪地里打滚,不过我明白,事实上这根本不会让我的心情好到哪去,我早就把这样的生活远远抛在脑后了。去年的我可真蠢,瞧我写廖夫卡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文字……怎么会?那时的我真是既天真又早熟。现在读着那些内容,对自己会胡扯的本事真是惊叹。再过两年,可能我就会把这些话都划掉了。
我没去参加*;前一天晚上睡得很晚,就不想早起了。早上,广播里传来一阵阵“万岁”的叫喊与交响乐的声音。知道自己没过着和其他人一样的日子,这种感觉真是又痛苦又恼人。'划掉四行'
1933年11月11日
永别了,涤荡不净的俄罗斯!
永别了,奴隶与绅士的国家,
还有你,穿着蓝制服的军官,
还有你,向军官低头的人们。
也许我在高加索的山岭那边,
可以逃避开你们长官的奴役,
躲开他们窥视一切的眼睛,
躲开他们探听一切的耳朵。
'《永别了,涤荡不净的俄罗斯》(1841年),作者:米哈伊尔?莱蒙托夫(1814-1841年)'
'划掉两行'
热爱自己的家乡与家乡的人民固然是好事,但是当周围尽是野蛮人——没受过教育也没文化的大众时,就很难真正爱得起来。我活在对周围一切人和事的无尽愤怒中,从社会的最底层开始,我憎厌无知的农民,憎厌那些愚昧、顺从得荒唐但有时又很难管教的民众,还得尽全力去帮助他们。
从对普通民众的责骂中不难看出尼娜的势利——父亲遗传给她的态度——这就是“中产阶级”的态度。
1933年11月12日
还有一个半月就到我生日了,但生日已经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