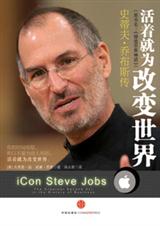我要活着-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在。
我不太和他说话,总之,我的话少得可怜。但只要我们刚开始谈论什么事,就必定会以争吵结束。我开始对爸爸有了一种不可理喻又无法控制的愤怒。这是何等愚蠢?可就是没法自控。爸爸向来有些脾气暴躁,年纪大了就更厉害了。对每件事都有抱怨:收音机不好,妈妈不好,我们三姐妹不好,我想最多的可能还是我不好吧——毕竟,我总在家里。抱怨对他来说,就像食物和睡眠一样必需。
然而,这并不会让我停止甚至减弱对他的尊敬。如果说我有一个通晓几乎所有事情的权威顾问的话,那个人肯定是爸爸。他的话对我来说就是最终决定(我应当附文写明仅限于政治与科学领域。)'划掉一行'。我把爸爸充满鄙夷和讽刺的话语当作真理,因为真理越是尖锐我就越喜欢。爸爸其实很棒:他从一个朴素的农民成为一个受到全面教育、极其聪明和先进的人,一路走来并不容易,我觉得我们谁都比不上他。
虽然我们并没觉得自己有多好,可是爸爸对我们的评价也太低了。他贬低所有的苏联青年。对他来说,我们姐妹三个在各个方面都笨得无可救药,没什么长进,都很肤浅。我们是女流之辈这个事实更让他坚定了态度,因为照他看来,所有的女人都是垃圾——这也不单单是他的想法,其他许多男人也是这么想的。幸好我没有兄弟:否则他和我们的待遇差别就更大了。
共产革命的目标是社会平等,也就意味着妇女该享有同等的权利。然而,没有一个女人在政府担任要职,通常,女人不掌权。理想的苏维埃女性是纺织女工、农民或是工兵,她应当多生儿育女,忠于丈夫与国家,做事高效尽责,同时必须顺从。性别歧视在20世纪30年代是视为社会正常的思维方式:尼娜父亲对女性的看法在苏联被许多男性认同。
1934年1月1日
就前面一小会儿,我和伊琳娜出去谈了谈——毕竟,和她一起可以畅所欲言,她自己也说个没完。我对她说的内容不是特别感兴趣,边散步边听她说着跟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的种种琐事,感觉实在有点儿怪。或许她也不是特别开心,不过她还是兴致很高地描述了自己的生活,她与两个迷人的伙伴一起度过的时光,一个是比她大两岁的漂亮女友,另一个则是她的追求者,一个和她同龄的希腊人。他们在一起度过的夜晚就是谈谈情,跳跳舞。
要不是她亲口告诉我的话,我不会相信那就是13岁的伊琳娜所做的事。在这方面,她似乎比我成熟多了。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一个风趣、苗条而快乐的女孩的影子,她知道该对追求她的人说什么话,而且她还会跳舞。最开始她总是说不喜欢跳舞,但很快就乐此不疲了。
女孩子就该是那样!而不是像我这样的丑八怪,脑子里总想着所谓平等,坚持要被当作一个人来看待。是谁把这些愚蠢的想法塞进了我们的脑袋?为什么男人掏钱帮我们买电车票或者请我们去看戏时我们会觉得很不好意思?真是可笑!我们现在真应该意识到,我们不过只是女人而已,别指望男人会对我们另眼相待,否则那才叫荒唐愚蠢呢。
我想如果有一天,伊琳娜的希腊爱人把她的外套递给她,或是赶紧冲上前去帮她搭鞋扣,伊琳娜一定不会觉得惊奇,反倒是十分荣幸。她那样也是对的。莉莉娅已经把电车上男士给女士让座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尽管我还是觉得很丢脸。一旦我意识到男人比我强百倍的时候,我就会抛下一切想与他们平起平坐的抱负,甚至还会感激他们给我们随手丢来的微薄施舍。
简而言之,我今后也不过就是个女流之辈,还要特别提防男人跟女人说话时脸上那种特别的讥笑和嘲讽,还有他们夸张的优雅与礼貌。今天,爸爸让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微不足道的女人,他说:“你们这些丫头怎么能和男孩子比?他们都很了不起,你们只是丫头片子。”我站在那里,轻轻笑了一下,倒没觉得生气——他自然是对的:我们怎么能和男孩子比?我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梦想与抱负,它们以后注定要流离失所。
1934年1月7日
一个人在家真是开心极了。我告诉自己:“只有两个解决方案:一种是想办法改变自己的生活,这不可能;另一种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也不可能。那就只剩一件事可做了。”我嘲笑自己毫无逻辑的结论:只能什么也不改变,继续生活下去,但那也不可能,不是吗?有三个不可能,第三种最不可能。痛苦地发现自己竟然这么无能。“我可以毒死自己,”我想,但不用以前想的方法,不再偷偷摸摸地,而是用完全合法的办法。如果有人想开玩笑送我一瓶鸦片,我才不会拒绝呢,会很开心地喝掉。但……没法做到不让别人知道。这感觉怪怪的,让我很害怕。妈妈知道会怎么想呢?这会对其他人——特别是妈妈有什么影响呢?
我越来越为自己的长相与性别痛苦不堪。我是个女的!还有比这更丢脸的事吗?我是个贱人!但终究还是个人。吃晚饭时还要伺候爸爸和尼古拉,真是件痛苦和丢人的事。他们凭什么坐在那里谈笑风生,让我不能好好吃饭,还要给他们递勺送盘?就算我没他们好,比他们低一等,那又怎么样?我还是个人,一个自由的人。我想要自由!
但是不,他们会阻止我,他们总会得逞;就算是现在,爸爸还在固执地把我变成那种卑微的奴隶。他很可能不愿意让我自问他亲自教我的那个问题:“他们凭什么这样做?”我不会放弃的,是吗?不,永远不会。
1934年1月11日
刚才一直坐在厨房里画画。房间里除了我和小狗彼得卡就没别人了。突然,有人敲门,不是我熟悉的敲门声,而是非常坚定的那种。早已对敲门声习以为常,我继续画画没去在意它,也不想开门。我知道一定是陌生人。要不是因为爸爸的尴尬处境,本来没什么好怕的。但现在他和我们住在一起,却没有通行证,就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门外很可能就是民兵部队的人。十七届党代会召开之前,他们在到处搜查没有通行证的人。他们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没有人知道……
门口的人又是按门铃又是敲门折腾了好长时间。我把铅笔和纸放到一边,脱下鞋子,悄悄走到门廊那里。就在这时,一个女人从隔壁公寓走出来,大声说:“他们可能不在家。”
“那这只狗在这里干吗?”有个男的回答。他又敲了一会儿门。彼得卡爬到了大衣箱上,叫得很大声,我就站在一旁,心跳得厉害。
彼得卡终于不叫了,我以为那个男的一定走远了。但是25分钟后,传来一阵更急促的敲门声。好像听到有人敲了三下,但我不确定。狗又开始叫唤了,我站在那里,一动不敢动,心里想:“我得尽快离开这里。但又不能逃走:爸爸随时可能回来,我得帮他开门。但是,无论如何,只要等到4点钟就行。4点以后我就带着彼得卡溜去奶奶家。不知道这个男的还会不会再回来?”离4点还有半小时。真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我害怕极了,没办法集中精力,什么事都干不了。我真恨他们!
从1933年的夏天开始,尼娜家就决定让父亲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敲门,以便让全家知道他来莫斯科非法探亲了。
1934年1月17日
晚上10点到12点之间,我们正在喝茶的时候,尼古拉来了,告诉我们房管委员会决定在今晚搜查。“赶紧走吧,”他对爸爸说,“现在就得走。”爸爸的心情显得特别平静,可能与他的特殊处境有关。他慢条斯理地喝完了茶,还吃了几小口面包。但在他的一举一动之间,仍能感觉到一丝匆忙与克制住的焦虑。我忍不住想:得有多强的自控力与意志才能在这种时候保持冷静啊。就连我都觉得好紧张,好像心脏跳快了几下。
1934年1月31日
我究竟是怎么了?就在三四个小时前,还心满意足挺开心的,在学校里叽叽喳喳,笑个不停。没想到一下子,所有的事都颠倒过来了,无聊与痛苦的感觉又回来了。很想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想归想,可就是没法弄明白。直到28号,一切还安然无恙,那天我没去上学,因为得去医院——爸爸替我预约了眼科医生斯特拉霍夫。奇怪的是:放假的时候,也就是学校还没开学那一阵子,我对自己的眼睛心烦得要命,担心休息这么长时间以后,再回到学校我就会没法忍受眼睛的畸形了。然而后来……突然就不是那么回事儿了!我完全忘了眼睛这回事儿,甚至不想去看医生,因为“那”已经不再困扰我了。
斯特拉霍夫医生说我应当动手术,我听了既不惊奇也不害怕,因为以前就想过手术的事,不过倒也没觉得高兴。一开始,想到要在医院待上一段日子,我甚至还挺开心的,心情好极了:以前觉得不可能的梦已经变成现实了。
白日梦很甜蜜,因为它只是一个梦而已,我也渐渐习惯了做梦,但……一旦有机会将梦变为现实的时候,我却害怕了,有种不应该这么做的感觉。我想象自己的眼睛恢复了正常,我明白这并不会让我开心,其实动不动手术都是一样。那么以前究竟是什么让我那么心烦意乱?会不会是受了学校面试的影响呢?不,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我感受到了现代生活的丑陋与一无是处,心里觉得很沉重。眼看着社会的不公正,虚假与冷酷,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可话说回来,又能做些什么呢?人是不是永远得不到完全的自由呢?自由只是虚幻的吧?人类几个世纪以来争取自由的无尽斗争难道都是徒劳的吗?
昨天,为了庆祝十七届党代会,一只高空热气球在空中放飞。无视这样的坏天气,那三个冒失鬼就冒着生命危险,飞入了令人生畏的云层,消失在潮湿的雾气中。根据气球发回的数据,他们已经到达了两万多米的高空,最新数据在下午三四点之间返回地球——气球已经开始降落,进入了一片厚重的云层。
然后就音信全无。昨晚到今天早上都没什么消息传来,今天下午才得知,吊篮的碎片和受难者的尸体已经找到,他们早已面目全非,根本辨认不出是那三个前天随着热气球一起升入遥远高空的冒失鬼。想想在高空中的他们吧,曾经孤独地在无风的茫茫宇宙里翱翔,在热气球以惊人的速度向地球飞奔时,他们能感受到风在耳边呼啸而过,呼吸越来越钝重,而在地面上等待他们的,却是不可避免的可怕死亡。
1934年1月30日,安德烈?瓦先科(35岁),帕维尔?费多先科(36岁)和伊利亚?乌瑟斯金(24岁)搭高空热气球飞到了22千米的高度。降落时,气球被毁,牺牲的宇航员如今安葬在莫斯科红场。
1934年2月10日
我15岁了,别人说这是一生中最好的年华。我可不这么觉得。年幼的时候,活在孩童的无知与天真中可真是幸福,因为那时不用读书,什么事都不懂。如今,我明白了幸福是虚无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你也永远找不到它。有时候好像幸福就坐在你身边*你,垂手可得。但那只是海市蜃楼,一种妄想罢了。
没人理解我,没人对我感兴趣,也没人想教会我如何生活!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事忙个不停,没人有空理睬我。那我该怎么办?是否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