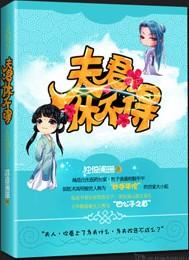不得不贱-第1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雨一直在下,我茫然地掏出手机拨号,响了几声后,凝眉清恬的声音传了过来:“喂,您好。”我开始有些清醒,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我太需要凝眉的温暖了,才下意识地拨通她的手机。我声音很低:“凝眉,你能出来陪陪我吗?”
她半天没有说话,过了好久,她的声音才飘过来:“对不起,阿武,我现在不在学校里。”
我脑袋里一片空白,多么希望凝眉就在我的身边,让我在她的面前像孩子一样无拘无束地大哭一场。可是她不在,我没有问她去了哪里,失魂落魄地挂了电话。
现在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空虚,是我抛弃了这个虚伪的现实,还是虚伪的现实抛弃了我?不想它了,我一头扎进一家餐馆。
老板看见我浑身湿透、眼神发直地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点菜,示意服务员上来询问我。服务员一看我像刚受到什么情感创伤、四处找茬的主儿,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同学,你要点什么?”
我要了一打啤酒,没有要别的菜,一边打着嗝一边往肚子里猛灌。冰凉的啤酒冻得我发抖,但是我还是想喝。我想用酒精麻醉自己,忘记一切的不开心。
这时候,有人在后面蒙住了我的眼睛,声音如银铃一般清脆:“猜猜我是谁?”
我晕晕乎乎地挣扎:“非礼啦!救命啊!”
全餐馆的目光都投向我,吓得霜儿那个小妮子急忙放开手,坐了下来,气鼓鼓地问:“胡说什么?你也值得我非礼一回?”
我醉眼蒙眬:“哦,我妹妹!霜儿呀!等你长大以后不要找男人,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说话声音很大,所有的人目光再一次聚焦在我身上,就像看着一个怪物一样。霜儿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她死死地掐我的胳臂,小声地哀求我:“不要再胡说了,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
我指着满地的空啤酒瓶子,拼命地挣脱她:“我不要走,还有这么多瓶没喝呢!走就浪费了!”
霜儿无可奈何,只好给我们寝室打电话。很快,救驾的江哥来了。我很大度地冲着霜儿挥手:“你可以走了,老爷们喝酒,女人不要参加!”砰!我实在支持不住了,倒在桌子上,模糊间有趣得很,江哥变成了两个,霜儿也是两个。
江哥和霜儿拖着烂醉如泥的我往寝室走,在混沌不清中,我似乎听到江哥的叹息:“阿武还不算是男人,他只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他还不能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世方式。”
我刚要*服和裤子证明我是个男人,突然感觉到一阵强烈的不适。我死命地推开他们两个,跑到一边,抱着一棵粗大的柳树开始剧烈地呕吐起来。
迷迷糊糊间,似乎有一双轻柔的小手轻轻地拍着我的后背,舒服得很。
后来,我晕了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了。
七、谁都不容易,贾贝勒“堵”人的过去。(1)
似乎过了很久,我终于醒了过来,却赖在床上,头很疼,整个人稀里糊涂的。其实我一直都不习惯喝太多的酒。每次大家一起出去喝酒我都投机取巧,大家也很少揭破我的“海量”。
寝室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都死到哪里去了。真是一帮天理不容的狠兄奸弟,我都到了如此狼狈的地步,他们居然连一点点温情的关怀都没有给我。
我挣扎着起身要拿水杯,寝室的门突然被推开了。我迅速钻回了被窝,开始做痛苦状地大声呻吟。
回来的是贾贝勒,他笑嘻嘻地坐在我身边:“身体还不舒服吗,阿武?”
我没有搭理他,继续大声地呻吟。
他还是笑嘻嘻的,居然还摸了摸我的胸部,大吃豆腐:“活该!我和赵远打架,谁让你装大尾巴狼去喝酒了?”
我被气得直翻白眼,用手指着他:“贾二,你的良心纯属让狗,不是,让你给吃了!”
贾贝勒生怕我被他气死,急忙笑着安抚:“好了好了,你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让哥哥很是心疼。那天也不能怨我,是赵远那小子先骂我的,你怎么反而把矛头指向我呢?”
我已经没有力气再翻白眼了:“给我买点吃的去。我要吃蟹黄小笼包,奶奶的,不宰你一把难泄我心头之恨!”
贾贝勒嬉皮笑脸地凑上来:“饿了?好,这表示还死不了!你放心,我以后不再欺负赵远了!”
我虚弱地点点头:“你,用毛主席的名义向我发誓!”
贾贝勒大笑着夺门而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
没过多久,门突然又开了,我以为贾贝勒回来了。抬头一看,竟然是赵远和江哥。
赵远似乎满怀愧疚:“阿武,你这是何苦?我对不起你,是我害了你。”
我摇摇头:“没事,多喝了点酒。算不了什么的。”
赵远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使劲地搓着衣角。
我不忍,毕竟赵远受了委屈:“亲兄弟还锅碗瓢盆地打架呢!你和贾二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他犯浑,现在还都在直抽自己嘴巴地后悔,自家兄弟,你得多担待些。”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赵远的嘴角竟然浮出让我害怕的微笑:“这个自然,谁让贫穷的尊严相当地廉价呢?”这个时候,江哥的脸色变了变:“你为什么要这么固执地坚持承认自己贫穷呢?”
我突然感觉到他很陌生,一时间竟说不出什么。
赵远的脸色很平静,眼神里有一丝狰狞,声音很低:“他瞧不起我的今天,我瞧不起他的明天。”
我开始发抖,也许赵远的话并不是想对我说的,而是对他自己说的,一种从心底冒出的寒意让我抖得更厉害。我不知道这是贾贝勒无意犯的错误还是赵远的天性使然,我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一个灵魂遭到自我扭曲和流放。
有时候,忍受比爆发更难以做到。我无力地挥手:“我没事了,你们上课去吧!别把事情往心里去,大家还是好兄弟!
赵远点点头:“我知道了,你休息吧,我回去上课了。”
门开了,他刚要往外走,贾贝勒抬脚就进来了。他们正好相撞,贾贝勒用挑衅的眼神看着赵远,活像一只充满战斗力的公鸡,头发齐齐地上竖,早就把他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抛在了脑后。
七、谁都不容易,贾贝勒“堵”人的过去。(2)
我垂头丧气,实在不知道如何劝解。江海河更是不敢去惹贾贝勒这个镇山太岁。突然,贾贝勒冲上去抱住赵远:“兄弟呀,你受委屈了,是哥哥错了,要不你打哥哥两下出出气?”
赵远被他弄得手足无措,轻轻地挣脱:“二哥,是我不好。”
我不禁愕然,没有想到竟然是这样的结局。
贾贝勒亲热地和赵远勾肩搭背:“兄弟,你走吧,阿武就交给我伺候了!”
他目送着赵远、江海河走出寝室,嘴角突然浮出一抹陌生的笑意:“没有血性,自私狭隘,以后我再不会把他当做真正的朋友。”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心里很不舒服:“那你真正的朋友是怎么样的?”
贾贝勒收起平时的嬉皮笑脸,很认真地看着我:“是你!”
我苦笑着摇头:“要是哪天你把我也打了,我还要跪谢你把我当成真正的朋友打来揍去。”
贾贝勒摇头:“阿武,你陷入了一个误区,你以为是我‘欺负’了赵远。其实你转换一下角色,如果别人用极度轻蔑的口气骂你,你会不会揍他?赵远也陷入了一个误区,他家境不好,但是他的内心极度仇富。他常常为了维护他莫名其妙的自尊来针对我。我可以忍让他一时,但是不表示他可以总把我当成靶子发泄,来平衡他的心理。”
我无言以对,贾贝勒的话让我没有任何反驳的余地。
我心里更不舒服的是,赵远一直没有把那1500元钱还给贾贝勒。也许,江哥说得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别人无权干涉。
这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大家彼此之间很客气,尤其是贾贝勒和赵远,简直可以用“相敬如宾”来形容了,可是寝室再也不能恢复到以前那个亲兄热弟的时候了。
这天,贾贝勒突然提出要请我喝酒,我去了。地点定在双旺大酒店,规格待遇之高,令我瞠目结舌。
诸位不要以为是什么五星级别的海鲜大酒店,那只是我们学校门口一条胡同深处的一家没有正式挂牌的小吃店,我们戏称它为“双旺大酒店”,平常也只有我们学生和民工偶尔光顾。
我和贾贝勒坐定后点了四菜一汤,臃肿的老板娘一看难得有如此大手笔的客人,乐得合不拢嘴,撒鸭子似的忙前跑后,端茶递水。
贾贝勒深深嗅了嗅屋子里很不新鲜、还少许混有的臭鸭蛋味道:“很亲切!我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
我险些从本来就不稳的凳子上跌下来,贾贝勒的“阿玛”是省里的高官,“额娘”更是商界女强人,我一直以为我们贝勒爷是含着金汤匙、躺在银蜜罐里长大的呢!
贾贝勒很少有严肃的时候,永远都是笑嘻嘻,玩世不恭的样子。他看着我:“阿武,你相信吗?我妈以前和刚才的老板娘一样。”
我见过贾贝勒的妈妈,华丽如名流贵妇。他今天要和我说的,可能是他家的发迹史吧!有时候,朋友是最好的倾听者。
贾贝勒喝了一口酒:“现在的父亲是我的继父。如果说具体一点,是第二个继父。”
听完开头我就意识到,这个故事不是美好的童话,主人公的经历甚至会很残酷。
贾贝勒的眼神开始慢慢深邃:“我父亲是警察,死得却不光彩。他死的时候我才7岁,我妈妈带着我经营着一个馄饨铺,在街坊邻居的流言蜚语中艰难度日。你无法想象孤儿寡母会受到什么样的欺凌。从那时候起,我从来没有一件新衣服,没有新玩具。同在一起的小孩合伙欺负我,动不动就骂我没爹。”
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只是我没有想到,会这么残酷。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会对赵远的辱骂产生激烈的反应。
“以前,我也因为一根冰棍让四五个小孩一起欺负,欺负够了,他们才给我一根冰棍吃。冰棍真甜真凉,我至今还记得它的味道。那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冰棍,我把它含在嘴里,还生怕它化得太快。回到家,我妈看见我鼻青脸肿的模样,一下子就哭了,哭得很伤心。”
贾贝勒又喝了一口酒:“我妈她很隐忍,一点点地向上爬。为了铺平她的路,她不惜和她不爱的男人结婚。她一共结了三次婚,越嫁越好。我成了少爷,可是我却怀念起原来的小馄饨铺,现在的老妈天天如真正的贵族一般生活着,我却知道这背后她有多少打落牙齿的苦楚。”
我不知道如何来安慰他,也许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有多爱他的妈妈。可是,他的妈妈给了他生命和财富,却不能给他真正的安全感和归宿感,让他觉得自己是个没用的孩子,所以他用浪荡不羁来填补自己的空虚。
贾贝勒的眼里似乎闪着泪光,他看出了我欲言又止的神色:“你不用说什么,我只是想找一个人倾诉。”
我试图转移话题:“老二,你为什么认为我是你真正的朋友?”
他似乎还沉浸在回忆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