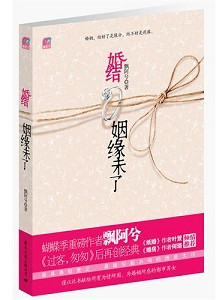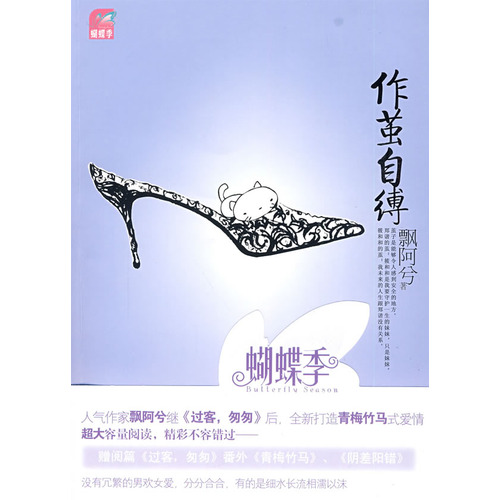飘阿兮-作茧自缚(出书版结局+番外)-第44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郑谐头也不回。岑世笑得开怀,郁闷一扫而光。
行驶的车子里,副驾位上的和和整个人趴在车内的台面上一动不动。
岑世推了推她:“喂,别睡着了。系上安全带。”
和和抬起头来,作了几个深呼吸,还是胸闷。她把窗开到最低,窗外呼呼的北风卷着稀稀零零的雪花飘进来,车台上的几张纸被刮了起来。
岑世把她伸到窗外的脑袋掰回来。刚有一辆车贴着他们的车驰过,离和和的头那么近,他惊起一身冷汗。“干嘛呢你,又不是小孩子,玩这种冒险把戏。”
和和面色惨白,说话也有气无力:“都是你不好,去招惹你前女友就算了,为什么还要被他看见?笨死了你。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你怎么专门缠着前女友啊!”
“迁怒,这就是标准的迁怒。怎么了?”
和和不说话。他乱猜:“勒令你限时甩了我?不让你去C市?穿梆了?”
和和眼圈红了:“都怪你太笨,害我说错一堆话!”
“不会是你为了替我说话,把郑公子给得罪了吧?哎,那不得把我美死?”
和和哭了起来:“我本来没打算那么说的。他一定会觉得我忘恩负义不识好歹,他现在一定讨厌死我了!”
“筱姑娘,别这么激动。等明天跟他道个歉不就得了。郑公子那么大人大量,又疼了你二十多年,怎么可能跟你一般见识呢?”他见和和的泪一串又一串地滑落,没有停止的迹象,深深地叹气,递上一包纸巾,“喂,我说,别不承认,你是不是因为他要结婚,所以触景伤情了?”
和和一边抹泪一边说:“去你的!”
岑世继续叹气,把车停到路边,拿纸巾帮她擦泪:“喜欢他就去说呗,那位小姐现在只是未婚妻,不是郑夫人,你大概还来得及。”
和和抓下他的手用指甲狠狠地掐下去,岑世杀猪一般地叫了起来:“啊,我的手要废了!”
和和听他的叫声不像掺假,立即松手。岑世开了灯,灯光照射下,他的左手瘀肿一片,有几道青紫色的指痕。
和和惊讶得顾不得哭了:“这是怎么弄的?”
“被郑公子的九阴白骨爪抓的。以前听人说他身怀绝技,我还不信,今儿算见识了。”
和和觉得不好意思,弱弱地说:“我来开车。等等,那边有药店……我去给你买瓶跌打药。”
她一边给岑世抹着药,岑世一边念念有词:“筱姑娘,你觉得,我如果去告郑公子人身伤害,索赔多少钱比较对得起他的身价和身份?”
和和停下手,郑重其事地说:“岑公子,求求你,今晚能不能不要再提他的名字了?还有,我真的从来没想过你猜测的那个问题。从来没有。你信不信?”
岑世敛了嘻嘻哈哈的表情:“我信。”他叹气,又重复了一遍,“我真的相信。”
另一辆车里,郑谐一如既往地开快车,但是他今天开得不太稳。后面有一辆车违章超车,他一闪,差点擦到另一辆车。
杨蔚琪看他状态不佳,摸了摸他的额头,又搭住他的手:“还好不发烧。可是你的手怎么这么冷?你好像有点抖,不舒服吗?要不要去医院?”
“明天吧,今天很晚了,我有点累,想早些睡。”郑谐把车速减慢。
“也是,你今天刚回来。我本不该拖你出来买东西的。”
“没关系。”
“明天中午……”
“饭局取消了。”
“为什么?”
“没什么,今天都见过面了。”
杨蔚琪犹豫了一下,低声问:“你跟和和呕气了?”
郑谐不出声。
“你也很久没见她了,何必一见面就跟她闹别扭。我去楼下找她时,她正在抹眼泪。”
“别提她,换个话题。”
“那你觉得,我若请和和来做我的伴娘,她会愿意吗?”
郑谐直视着前方:“再换个话题。”
杨蔚琪轻轻地叹了口气:“有时候我还真是挺同情你的。连生气的时候都这么压抑的人,你的人生乐趣一定很少。”
他俩也一路无言。
到杨蔚琪家时,她终于打破沉默说:“刚才算我错了好吧,你不要一直板着脸了,笑一笑。”
郑谐冲着她勉强勾了勾唇角:“我心情不好,你别介意。”
“你居然也会承认自己心情不好?我还以为你的情绪一直是直线。”
他俩在车里安静地坐了一会儿,杨蔚琪又说:“我最近也觉得很恍惚,总是想起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还记得吗?”
“停车场?”郑谐想了片刻回答。
“还有相亲。就像一部小说的开头。可是小说都是很曲折的,而我们这么顺利,顺利得不可思议,就像做梦似的。”
“你最近加班太多,没休息好,所以才会胡思乱想。”
“可能吧。”
第二天杨蔚琪与一位杂志专栏编辑有约。她一直为她们提供女性权益方面的法律咨询服务,与那贺姓编辑私交也不错。
“大周末的不陪你未婚夫,却来跟我一起加班,你也敬业太过了吧。”
“我要出差一周,怕误了你的专栏。”
贺编辑一听她出差的地方,倒吸一口气:“那个地儿,气候糟,人难搞。而且你快结婚了,去那边一趟能把你皮肤折腾得几周也养不回来。你老板一向挺照顾你的不是?”
“我自己要求的。那地方贴近自然,城市气息少,有些事情可以想的更清楚些。”
“我听说女人容易犯婚前恐惧症,原来你也不例外。”
杨蔚琪弯腰去捡落在地上的餐巾,领口里的项链滑出来,露出挂在链子上的戒指。
“唔,好漂亮的钻石。他一定很喜欢你。”
“你怎么不说他爱我呢?或者说,他很有钱?”杨蔚琪轻声地说。
“口误口误。”对方耸耸肩。
杨蔚琪轻轻地叹了口气:“上次你说,男人都有红白玫瑰情结。其实这两天我在想,不是的。有些男人就像小王子,如果他心中已经有了一朵玫瑰花,那么别的玫瑰,无论什么颜色什么品种,也不过是其他一万朵玫瑰中的某一朵而已。”
“快要结婚的人了,别胡思乱想。你搞法律的人,不是最应该重视证据的吗?钻戒是定金,结婚证是产权,你一样东西已经手,另一样也马上要得到,还在意别的做什么?”
“大概我最近有点职业倦怠吧。”
“好啦。以前你说,你最欣赏的男人的三类品质,勇气,责任,亲情,郑先生恰好都具备了。其实真没几个女人能像你这么幸运地遇上自己最欣赏的那一型。”
“是啊,怎么会这样幸运。”
“我的好朋友说,对男人嘛,不要太较真,只要不是原则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好了。”贺编辑说,“谈正事谈正事。你这个样子,让我这种没行情的人情何以堪。”
郑谐的日子过得浑浑噩噩,但看在别人眼中却是更加的规律而机械。白天他流水线作业一般开会谈判签合约,效率太高导致他经常无事可做,他一没事做,下属就心惊肉跳。他的感冒又一直好不彻底,咳嗽缠绵不愈,大多数的饭局也不参加,所以他更闲。
杨蔚琪出差去了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快一周了还没有要回来的迹象。他想找她时却总找不到人,但也习惯了。什么事情都只要习惯了就好。
他与和和彻底谈僵的那天晚上之后,就再没与她联系过。
或许也算不上闹僵,和和只是说了一些她以前从来没说过的话而已,即使当时她和他都有点激动,但那些话的字里行间,后来他回想一下,觉得她说的很有道理。
对于和和,他的确太自以为是了。就像他一直自诩为和和的保护神,结果可能给过她最大伤害的恰恰是他自己,而多年来他却毫不知情。
他不伤心,他的心脏一向都很强壮。只是在他真正听到和和说,他的存在对她而言是一种负累时,他还是觉得心脏空落落的,好像那里被人剜掉一大块。
其实,那地方本来就已经生出一颗肿瘤,尽管他视而不见,但一直在慢慢地滋长着,成为一处隐患,如今被生生地一刀切掉,反而好,很解脱。
晚上又有人约他去聚会。那群狐友每有聚会都喊他,但他三回里总有两回不去,已成常态,所以一旦应允,大家反而吃惊。
冬日聚会无非就是先打球再打牌。牌室一面墙上开着电视,静了音,只有图像闪忽。
郑谐坐的位置恰好正对着电视,他一边向外丢着牌,一边瞅着荧光屏。就这么一心二用地走着神,仍是连赢两局,有人怒了:“没天理了,关掉关掉。”
大家定睛一瞧那电视,虽然静了音,节目下面却有字幕的。那让郑谐边打牌边看得专注的节目,是一出情感谈话类节目,儿女亲情,家长里短,此时一位优雅女子正抹着泪,控诉自己为男友多年来付出的感情被践踏。
旁边有人去摸郑谐的额头:“太可怕了,这人脑子烧坏了,现在居然开始看这种东西。”
郑谐敏捷地躲开他的手。另有人说:“这是婚前恐惧症的另类表现。”
因为郑谐已经很久没跟他们小聚,大家索性把晚宴当作他的单身告别派对第一场,招呼了一大群人吃饭,还找了弹月琴唱小曲儿的姑娘和会变魔术的小伙儿助兴。
郑谐被灌了一些酒。因为他已戒酒多时,又病未痊愈,喝得还算节制,倒是那些人,个个东倒西歪。
席上有几张不太熟的面孔,朋友的朋友,以前或许也见过,但不曾相交。当那群人纷纷趴的趴,溜的溜时,除了郑谐,只有另一个他看着面生的年轻男子还直直地坐着。
刚才吃饭前有人介绍过,穆格,朋友的朋友。他的另一重身份是杨蔚琪的老板。朋友给他介绍郑谐时打趣说:“这是你员工家属。”
此时他端起酒杯,朝郑谐举一下:“郑先生,敬你与蔚琪白头谐老。”语气淡淡的不见热情。
郑谐没加推辞,将杯中酒一口喝掉。
晚上郑谐给杨蔚琪打电话。他发现为什么觉得处处都不对劲了,原来她连续几天晚上都没给他打电话。
“工作不顺利吗?怎么去这么久?”
“还好吧。这里环境挺好的,我权当放假。”
“穷乡僻壤的,又是冬天,哪有什么好玩的?”
“山上积雪,湖面结冰,非常漂亮。大家都在忙着准备过年,我跟大妈学做艺术馒头,跟孩子们学从冰里钓鱼。”
“听起来过得不错,我以为你会吃苦头。”
“还好,就是不太方便而已。你想念我吗?”
“你何时回来?”
“再过两三天。”杨蔚琪在电话那头儿静默了一会儿,“郑谐,你爱我吗?”
“你怎么了?”
“没事,就是有些无聊。你爱我吗?”
“我很喜欢你。”几秒钟后,郑谐在电话的另一头回答。
仅仅过了两天,郑谐再次遇见杨蔚琪的老板。
说起来也正常,他俩的交友圈子有很大重合,或许之前就见过面,只不曾有过真正交集。一旦认识了,便发现,原来两人时常擦肩而过,就像当初他与杨蔚琪一样。
那日郑谐又被拉去凑份。哥们儿说:“阿谐这宅男,以后若结了婚,就更不掺和我们了。多一回算一回。”
郑谐那哥们儿最近请穆格帮着打一个艰难的官司,所以时时把他请出来套近乎。
后来就把穆格灌高了。一群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