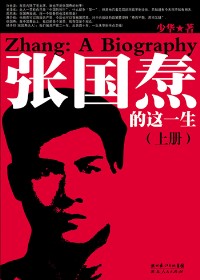中共地下党人-第6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柯麟在广州救治好一批受伤的赤卫队员后,又秘密潜回了香港,与叶剑英住在一起,几个月后,党组织指示他们到上海,俩人化装后乘船北上。这些日子,他亲眼目睹了起义的失败,战友们的牺牲,悲痛之情让他难以释怀。望着东方透白,云蒸雾绕。他遗憾地说:“云太多,恐怕看不到海上日出了。”
“等等,再等等。现在正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过,乌云再多,终究挡不住太阳的光芒。”
柯麟明白了叶剑英话中寓含着的深意,默默地望着东方。过了一会儿,霞光便冲破云雾,红日从海面上冉冉升起,映照得海水波光粼粼,一片灿烂。
叶剑英感叹说:“柯麟,你看这红色多壮丽啊!”
“是啊,这真是象征着我们革命形势的未来!”
“说得太对了!”叶剑英拍拍柯麟的肩膀:“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前仆后继,战斗到底!”
船到了上海,二人随着乘客走下船舷,远远看见先期到达上海的贺诚、周越华和另外一个陌生人前来接站。贺诚穿着入时,一副有钱人的派头。周越华穿着虽然素淡,但她人长得漂亮,又很文静,显然一个大家闺秀。而那个陌生的年轻人,则是一身青缎裤褂,裤腿还用黑缎带扎紧,留着小胡子,戴一副墨镜,样子很像上海“小开”。
战友们在异地相逢,倍感亲热,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唯独那个上海“小开”站在一边冷眼相看,操一口上海普通话说:“先勿要亲热啦,拿起东西走好啦!”说完,提起叶剑英和柯麟的包,先往前走了。
这副模样的人让柯麟心里起疑,他悄悄问贺诚:“他是什么人?”
贺诚诡谲一笑,“是党内同志。”
叶剑英眨巴一下眼睛,疑惑地说:“这人看着有点面熟。一时又想不起来。”
贺诚笑而不语,带他们出了码头。
5人分别乘坐着三辆黄包车来到了租界旅店。这是一个套间,刚进来还没有安顿好,只见那个“小开”走到叶剑英面前“啪”一个军礼:“报告叶参谋长,王庸向你报到!”
“王庸?”叶剑英一怔,目视贺诚。
那陌生人说:“本人真名陈赓,化名王庸。”
“噢,是你这家伙!”叶剑英讶然喊道,“化装化得太好了,活脱脱一个上海“小开”,把我和柯麟都给蒙住了!”
周越华笑着介绍道:“陈赓同志现在是中共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还兼着中央军事部的情报工作,他是个大忙人,也是上海滩有名的“百变人”,一天一个样,可会化装了。”
陈赓得意地笑着,一边与叶剑英、柯麟握手,一边自谦道:“雕虫小技,雕虫小技,不值一哂。”
叶剑英看着陈赓关切地说:“大活宝,我听说你在南昌起义中腿部负重伤,怎么样?现在恢复了吗?”
“彻底恢复了。不信你看。”陈赓边说着边即兴表演起来,一会儿纵情跳跃,一会儿又下蹲屈腿。“看,怎么样?还能跳舞呢。”
“好啦,好啦,你那个舞就不要跳了。”叶剑英笑着阻止他。大家也忍不住笑了起来。柯麟也被陈赓热情幽默的情绪感染,笑得十分开心。
叶剑英受命与另外五位同志从东北进入苏联,到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办的一所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而柯麟则要留在上海中共特科工作。周恩来考虑到他是一个经受了多次考验的同志,又有医生的身份,在隐蔽战线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这一天,柯麟、贺诚、周越华去戏院看表演。舞台上,一个矮胖的名叫“化广奇”的魔术师正在表演大卸美人的魔术。几个年轻人穿着戏服在音乐声中做他的助手,只见美人夸张地表演着,台上台下兴致很高。节目结束了,大家热烈鼓掌。化广奇和美人连连谢幕。
陈赓穿一件月白色长衫,来到柯麟他们的桌前,坐下喝一口茶,抬头回应着其他桌上各色杂人的热情的招呼,看得出来,他的人头很熟。柯麟颇为欣赏地看着这位“王庸先生”。陈赓转过身来,小声对他们说:“一会儿分开走,溜到后台去,到“化广奇”的化妆间。”说完,自己先起身离去。柯麟、贺诚和周越华也相继离开,分头进了化妆间。
那位魔术师已卸完妆,原来他是特科的负责人,名叫顾顺章。他同进来的柯麟、贺诚边一一握手,说:“怎么样?我的魔术表演够水准吧?”
柯麟和贺诚异口同声地夸赞:“精彩,非常精彩!”
顾顺章得意洋洋地:“厉害吧,搞地下工作嘛,脑子里时刻要有变魔术这根弦。不然,出现问题了,不能随机应变就麻烦了。”
陈赓笑一笑说:“别吹啦!你还是给他们说一说办诊所的事情吧。”
顾顺章这才看着柯麟和贺诚说:“办诊所的小楼已经租好了。”他从兜里取出两把钥匙,“没有什么可说的了,这是诊所小楼的钥匙,就交给你们啦。”
刻不容缓,第二天柯麟和贺诚就来布置“达生诊所”了。诊所设在上海威海路春萱里弄的一幢三层小楼里。这一带是中产阶级的住宅区,又属英租界,比较安全,环境也很幽静。门诊室设在楼下。楼里两间房的墙上分别挂着两块柚木牌,上面写着蓝字,一块上写“柯达文医生”;一块上写“贺雨生医生”。前者是柯麟化名,后者是贺诚的化名。诊所的护理员是18岁的交通员“小四川”。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地下党人》第三章(2)
诊所挂牌后,周恩来、陈赓和顾顺章便前来视察。
“一楼是诊室、治疗间;二楼有小客厅和两间房,可做病房;三楼顶有两间小阁楼,一间是我们夫妇的寝室,一间是柯麟的寝室,也可以成为观察楼外动静的瞭望哨。”贺诚介绍着。
周恩来赞许地说:“很好嘛!现在我们党处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包围之中,我们的同志必须适应这种复杂困难的环境。”他停顿了一下,又问:“这里安全没问题吧?”
柯麟回答说:“这幢楼房,每个房间互相连通,有个后门可以通到另一条街上。中央领导同志秘密会议的房间挂上传染病房的牌子,我们在门口摆上了消毒药品,病床上挂了治疗卡,一旦有问题,在里面的病人看起来都是在治疗,敌人不容易察觉和找到破绽。”
“嗯,这办法好。政治局的同志一进了这道门,全是‘传染病人’,看谁敢碰?”陈赓诙谐地说。
周恩来看着治疗卡,也很满意地说:“诊所虽小,责任重大。你们做的工作关系到党中央和政治局同志的安全,要经常和敌人直接打交道,要成为党的耳目、神经和血脉。你们是医生,自然知道耳目、神经、血脉的人体中的重要作用的。我们要胜过敌人,高敌人一招,胜敌人一筹。就要做到胆大心细,沉着冷静,临危不乱,守口如瓶。”
正说着,顾顺章不合适宜地打了个哈欠,他大概感觉到了在周恩来面前这样哈欠连连太不雅观,忙遮掩说:“不行。我有点儿急事得马上去办,周公,我先走了。”说完,也不等周恩来说话,匆匆离去。
周恩来看他离开,继续对柯麟和贺诚嘱咐道:“切切记住,除了党内直接领导外,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要暴露自己是共产党员,这是地下工作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
柯麟和贺诚点着头说:“是,我们一定严格遵守!”
诊所开张后,一个十八、九岁的清秀女子找上门来,要见诊所负责人。
“你们不是在招聘护士吗?我来应聘。”说着便从包里取出一封信,交给柯麟落落大方地说:“我叫陈志英。有人介绍说你们在招聘护士,我就应聘来啦。喏,这是介绍信。”
柯麟看了信,原来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关向应同志写来的。他热情地做了自我介绍:“陈志英同志,欢迎你来我们诊所工作。我是柯达文医生。还有一位贺雨生医生,他现在不在诊所。”
陈志英也自我介绍说:“我在同德产科学校读书,还没有毕业。关向应书记说这里急需要护士,组织就派我来了,请多指教。”
“我们是一家人,用不着客套。”柯麟又转身对小四川说:“你帮陈护士安置一下。”
党中央的会议第一次在诊所召开时,前来开会的周恩来等领导同志都化装成病人,柯麟和贺诚、周越华以及实习护士陈志英也都戴着口罩,紧张地守在楼下门口轮流放哨,观察动静。
突然,一位一个身穿短装,头戴鸭舌帽的捕房“蟹脚”,一头闯了进来
在场的人都大吃一惊,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只见那“蟹脚”用上海话嚷着,直往楼上奔。“医生呢?医生呢?快给阿拉看病!”
柯麟一个箭步上去挺身挡住他的路,刚说了“先生”两个字,就发现了问题,“是你?王先生……”
原来那“蟹脚”是陈赓假扮的。
陈赓摘下帽子,故做遗憾地:“哎呀!露馅了。真糟糕!”
原来他是有意来测试一下诊所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应变能力。
一场虚惊后,他们又听到在大门外面望风的小四川和人发生了争执。大伙儿的目光一齐警觉地看向门口,只见一位太太拖儿带女闯了进来,她左手抱着一个婴儿,右手拉着一个女儿,后面跟着一个大女儿领着一个小男孩,大大小小五个人闯进了诊所。
那位太太看起来精明、跋扈,却又很世俗,她脸红脖子粗地嚷着:“你们是开诊所的,为什么不让人进来看病?”
小四川说不过她,结结巴巴地阻拦着:“不、不是不让你看病,是这个……是那个……”
柯麟见事情紧急,忙迎上前去解释说:“哦,是这样的,我们这里住进来一位传染病人,接待其他患者怕引起传染,因此暂时不对普通病人看诊。对不起啦。”
为配合柯麟的话,在楼上望风的周越华赶快拿起准备好的消毒用品,动作夸张地做起了消毒的动作来。
那位太太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式,但一听有传染病人,不嚷了,疑惑地问:“是吗?什么传染病?”
“开放性肺结核,”柯麟一脸严肃地说,“你看,我们这不都戴着口罩吗?”
“要死喽!快走快走!”那位太太败兴地嚷着,招呼孩子们赶快离开诊室。可是那个男孩却对周越华的消毒器大感兴趣,挣脱姐姐的手“噔噔噔”跑上了楼梯。陈志英一看情况不好,怕小孩儿上楼影响党中央的会议,马上冲过去把男孩子从楼梯上拉下来。
那位太太见男孩儿淘气不听话,逮着他就是一个巴掌,打得孩子大哭大闹。陈志英忙抱起孩子跑出楼去。
柯麟对陈赓、贺诚说:“既然是病人来了,我去处理一下吧。”他说完,走出门来,只见那个小男孩儿一边哭着一边呕吐起来。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地下党人》第三章(3)
他摸摸孩子的头:“嗯,他在发烧呢。”
那位太太着急地大诉其苦:“可不发烧呗!我昨天去状元楼吃喜酒,不乐胃,到今朝没有消化,两个囡跟我去吃喜酒,回转来也不适意;儿子伤风咳嗽,我的老公做生意忙得四脚朝天,家里的事情油瓶倒了也不扶……”她越说越伤心,流下了眼泪。
柯麟安慰她说:“像这种情况,你可以给诊所打个电话,我们会到你们家出诊的。”
那太太苦丧着脸:“咳!四个孩子病了仨,我一个头两个大,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