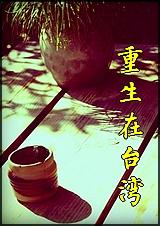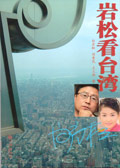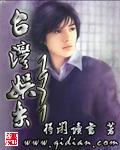�ƾ�̨��ľŴ�ʦ-��8����
�������Ϸ���� �� �� �� �ɿ������·�ҳ���������ϵ� Enter ���ɻص�����Ŀ¼ҳ���������Ϸ���� �� �ɻص���ҳ������
��������δ�Ķ��ꣿ������ǩ�ѱ��´μ����Ķ���
������ȻǮ�¸�Ů��˵��ƽ���Ŀ�����Щ��ʵ�ڵ�˵���������������粻ֹ������¥�粨������������Ҫ��Ǯ�¡�֪�˲������������粨��Ǯ�Ҳ��ð�������Ȼ̨�塰������1988����Ը���ؿظ洦�Բ����߾�������Ǯ��ֻ����Ȼ�뿪̨�壬ϣ�����鵽��Ϊֹ���������ӵ�Ǯ�°��˵�˵������Щ���Ѿ���ȫ�������й��Ļ���ͳ�������ϸ�Ů������飬��������������Ů��Ϊ�λ����ôԶ�ĵط����������ס���
����Ǯ����Э��δ��Ը�游�״���ƽ����������ֶ���Ǯ�µ�����¥���ⶰ����ԭ�ǽ���ʯ������ʿ��Э���õع�Ǯ�³��ھ�ס��ס����δ��ʱ�ձ�Ǩ����Ȩ��������ɽ������ת�Ƶ�̨���������������̨������Ա���ɣ�Ǯ��ס����̨���������Ʋ���ȴ��������Լ����û�����������ɹ����ã���ͬ��ռ�á�
�����������ʿ��Ҫ���ʮ��������Ǯ�����ڰ�ҡ�ʱ�Ρ�����ίԱ����###Ҳ������Ժ�����ѯ��Ҫ���и������ջع����������ԡ���ռ�в���Ϊ������������Ǯ�£�������������Ǯ�´����൱���ѹ�������衣�����ջ�����¥֮��Ĵ������������Ц�ֿɱ�������֮һ�ǣ����衰Ǯ�¼���ݡ���
������������¥�˽���ͼ��Ǯ�·��˺��������棬������Ҳ��̨���������������粨֮����˫��һ�ȶ�Լס��1992��Ϊֹ��δ�������˶Դ�������һ���ʱ�䣬Ǯ�������ⲻ������������š�ѧ�����й��ۣ��˸��������Ǯ�£������ڲ�Ը�����������ķ߿��У���1989��8����������������ԸǨ������¥Զ���Ƿǣ���Ȼ�뿪������ĵء�
����1990��5�£���λ��ȫä�Ĺ�ѧ��ʦ��ȻǨ����ס��ʮ�������¥������̨��������·���ݾ�ס����������¥�ڲ��ٲ����������ѧ����λ��Ǯ����ȥʱ���ĵ�˵��һ�䣺����IJ���ס����û����Ҫ������ݡ���
�����ۼ�������Ǯ�£����ʱ�Ѳ�̫�ܳ��ţ�Ҳ��̫�϶ི����ʳ�����������Լ��ˣ���ϣ����Ů��������ǰȥ̨һ�ۡ����첻����Ը���ڶȹ���ʮ������ٵ���Ҳ����Ǩ������¥���������£�1990��8��30�գ�һ����ѧ��ʦǮ�������ں�����·��Ԣ������ȻǮ����ǰ��ξܾ����ع���̽���뽲ѧ�����˺�����ȴ�����������Ǯ�µ���Ը���ô�ʦ�ǻһص����������ϼҰ��ᡣ
�����������ǡ����η���ȴ���ɲ���
����Ǯ�¹�ȥ����ǻ���̨������쵼�����������°�����������9��26����̨�����й�����û�뵽��Ů������ɥȴ�������粨���ܵ�ǰ��Ǯ��̽�������Ȼ��Ӱ�죬Ǯ��������̨��ɥ���ⲻ�ϱ��Ŵ����������ĥ��������̨�嵱��Ҳ�൱������������Ϣ��
Ǯ���¡�����һ��Ϊ�ʹ��лꡱ��ʷѧ��ʦ��8��
ʱ��ȫ����Э�����˸���ϯ��Ǯΰ������Ǯ����ǰ�ͱ����������ѧ�������Ļ��Ḱ̨̽�ף����λ����ȥ���廪��ѧͬѧ�������δ����Ϣһ�������������Ұ����ʿ�������������У�����ֱָǮΰ���ǹ������߸ɣ�Ҫ��̨�嵱�ֽ�ֹǮΰ���뾳��
�������˲����ľ��飬Ǯΰ����Ǯ�¹�ȥ���µ�Ǯ���ˣ���������̨��ԭ����˵����Ϊֶ�ӵ�ȻӦ�ø�̨��ɥ����̨�����������ʱ�˵����ƹ涨���ܷ�̨Ҫ��̨�嵱�ֵľ�����
����Ů��Ǯ�ס�Ǯ�ԺͶ���Ǯ�е�������˸�̨��ɥ��Ը������ϣ�����ϴ�̽��ʱ�ֳ�������Ӱ�������徲��ֻ��˳�����У���Ҫ���и��š�̨�巽���ܵ���Ұ��������ǣ���������ע��ȴ��Ǯ�Һ����Ƿ����̨��ٷ��涨��ǩ�𡰲μ�������֯�����顱�������������빲������̨����Ǯ������Ϊ�ѣ��վ���������Ǯ����ȥ̨��ɥ����������Ǯѷ�ij���Ǯ���Լ��ѹʳ���Ǯ�Ķ���Ǯ��ȥ̨�����ط��ڸ��ʽ�᳡����
����Ǯΰ������̨�����ܵ纯������������ʱʧ�����Ǯ����Я�Ķ��飻Ҳ��Թ��Ͽδͨ������̨��ɥ�ı��ˡ�Ǯ������˵���������������һ�棬�븸�������������Ů�е��൱�ź�����˼�������ȫ��ʵ�ָ�����������Ը��
�������븰̨��ɥδ����Ǯ����Ů�����ܲμ�9��30�������������Ժ��
�����еĹ�����1992��1�£�Ǯ��������Ǯ����ǰ��Ը����Ǯ����ǹ���̫��
����֮��������������̫���е���ɽ����ɽ��Ǯΰ�������¼���Ǯ����ǰ����
���������硶��������ϵ�꡷�����й���������ѧ��ʷ��������ʷ��١��Ⱦ�����Ĺ
������
���������վ���һʱ�ģ���ʷʼ�չ�ƽ��Ѹ�ٵط�����ʱ�����ϡ�Ǯ����̨���Ծ��и߶ȵ�������Ӱ��������Ǯ�±���Ǩ������¥�����в����������д����###����1994�굱ѡ̨���г���Ϊ���������������������Ǹ����������ĮȻ��˵���������ĵ�Ǹ��û�����塣��
��������Ǩ�������õ�����¥����̨������ͼ�����1992��1��6�ձ�Ϊ����ݡ������ڷ������ʧ�ޣ�������г�ʱ�����ɣ�ֱ��2001��12��31�ղžͽ�ί�ж����ѧ��Ӫ������2002��3��29�����¿��ݣ�����ά��Ǯ�¾�סʱ��ò����Ӣ�������µ�̨����������ŵ��Ǯ�¼���ݱض���ȫ�ţ��Է���Ǯ�µķ緶��
������Ӣ�Ŵ���̨����������ΪǮ�����ܵIJ���ƽ������ʽ��Ǹ����ΪǮ��ƽ������ǿ��������¥�����и��Ʋ������Ǽ�Ϊ���ݣ������д�������Ҫ��������壬������������Ǯ�·��ھ�ס����˺���ռ�÷�������⣬����̨���е�Ī����١�����������Ӣ�Ź�ͬΪǮ�¼�������ֿ��ݣ�������һ�á�ϣ��֮�ɡ���ϣ�����º���ʷѧ�ĸ�����2004�̨꣬������������һ���ƻ���Ǯ�¡����ʡ���˹������������
����������ʷ���ػ��й�
����һ��Ǯ�·�������һ�����������������������ս���ȥ������û��������ҵ����ӡ���Ǯ����Ϊһ��˶�壬��ʷѧ����ѧ�ϱ��гɾͣ���֤���й�������������������������룬ȴʼ��δ����������ѧ������Ϊ�ij���һǧ������֡�����ʵ�ǵ����һ�ɶ��л��Ļ�����ͳ��ֵ���Ȱ��������������д����ߣ��Ӵ�Ҳ���Կ���һ��˼��ҵĸ�����ؽ�
���������ڴ�ͳ��ֵ�뾭�䲻���ܵ������Ļ����ѧ�������ս֮�ʣ���ִ�ͳ��Ҫ�ܴ�����������л���������ʷ�Ļ����Ȱ�������������ʹǮ�²��Ϸ�ս��ȥ��ԭ������
������Ǯ�¶��ԣ������ù�����Ŀ�����ǿ�����������롰�����¡��б����ϵIJ��죬���������Ǹij����������й����Ļ����������ˣ�����һ�����½������Ļ��������й�Ҳ���᧿�Σ�ˡ�
����Ǯ������ѧ�ϣ����ź�ѧ���������ż��������ʷͨ�䣬���峣������ӹ�ϵ�����ⷳ����ţ�Ǽ���о����ޣ�ֻ�����ʼ����ʷѧ�ϳ�һ��֮�ԵĿ������������������£����м��ء��������ױ���������֤����ѧ��ʽ��Ҳ��Ϊ�����й���ʷ�о���������Ҫ���ɡ�ͬʱǮ��һ������������ѧ�����ڴ�Ѱ�ҡ����һ�Թ�֮���Ļ�����ֵ�����Գ�����������ѧ���Ը��Լ��ڲ�ͬ��������ɢ�ľ��Ⱦ��Ӱ������
����һ��Ϊ��������������ɹ�Ϊѧ�������ķ糱��Ǯ�µ��ײ�����������째������ס����Կ�֤�粵�˿���Ϊ����ѧα����������Ϊ����ż�������йŸ��Ƶ�����˵���������ԡ���������ϵ�꡷�Ե伮�б��ἰ����������������¼����п�֤�������ɵ���ʷ��Ϊ��ʷ��Ҳ��������ʷ�ع鶨�ۣ���ȴһ��������
�������¾ɵĽǶ�������Ǯ����վ��ά���ɵ��Ļ��۵���������ɵ�������˵���������DZ��أ��������У���������ʷ�ij����й۲죬����������ս֮�ʼ��ױ���������������֤�������������Ը���������ѧ��רҵ����֡���ͳ���������������ȷ��˼���Կ������ǣ�����ֱ�����ɴ�ʦ���ʵġ�ȫ���������۵�������η�������ã������˾�����
����Ǯ����1949���뿪�����½������ѧ���ػ��Ѿ���Ϊ������ԩ��ʷѧ�о����ķ����й���ͳ�Ļ��ĸ����뷢���ϡ�һ�羭ѧ����ѧ��Ǯ�¶����ڴ�����Ѱ��һ�������й��˶��������Ļ�������˼���������Ļ��б�¶����ʷ���������й����������Ļ���λ�������ҵ���������������ԭ����Ǯ����ǰ���һƪδ��ɵ�˼���ĸ壬���⼴�ڡ����˺�һ����ϣ�����й��˵���������˵�����ʷ�ػ���ӭ��δ������������ս��
����20�����Խ���������ν������Ʈʧ����ʱ�̣���ʷ�Ѿ���ΪƯ���ں��ִ���Χ�к�����֪�������ŵĿ��壬��Ϊ��ʥ�̾�ѧ���������������˲���ʵ�ʵĿ�̸�����������˵�Ц����Ǯ�������˵ر�ʾ�������˹�ʷ�İ�����������һ����ҵ֮������Ѱ��Լ�����֮�����Ӽ����߹����ʷ����
����Ǯ�µ�ѧ������ʼ���ߵúܼ�į���ڴ����˶���ʷ�ó����������ȴ����������г���ͬ��ʹ���Ե���ֵġ�����ʱ�ˡ������������ּ�į�����й������������ؾ��Ŀ��飬�������������һ�ǣ���Ϊ�л���ʷ�Ļ��ػ��ߵ�Ǯ�£�������ѧ��������ͻ�ƣ�������֡�Ϊ��ʥ�̾�ѧ���ľ���Ϊ�й�δ�����Ļ���ѧ�������������Ҫ��ʯ��
����
���ס���������ĥ�����Ĺ�â��1��
�����ձ��ڹ��ʺͻ�Ҫ�����ൺ������ɽ��һ��Ȩ������Ҫ�ɹ��ˡ����ǵ��⽻����ʤ���ˣ����ǵ��⽻����ʧ���ˣ�ɽ������һȥ�������ƻ��й����������й��������ƻ����й���Ҫ���ˡ�
������������ѧ�磬�����Ŷӵ�����ʹ��ȥ��Ҫ���������ά�ֹ���������ȫ��ũ���̸��磬һ���������跨�������ᣬ������Ȩ���ڳ��������й��������ڴ�һ�١�����ȫ��ͬ����������������
����һ���й������أ������������������Զ��͡�
���������й���������ɱ¾���������Ե�ͷ��
���������ˣ�ͬ������ѽ��
��������������ѧ������������ɢ���ġ�����ѧ��ȫ�����ԡ���Ψһ�����Ĵ�������ӡ������ݡ�������һ������ѧ���Լ��İ���д�ɡ��պ�����ѧ�����˽���ʯ�IJ�����������ʮ������š��������ԡ��������ۡ��������������ס�
��������������ԡ��Ը�������
�������ף���־ϣ���㽭�����ˣ�������ʮ���꣨1897�꣩12��21���ڽ��������س�����
�����������䣬�����䣬���ν���ʡ�����ꡢ���������µ�����������׳���ʱ���丸Ϊ������֪�ء�������ʫ���ģ������黭����������ѧ������������Ӱ�죻�����������´���������Ļ��ܸ���Ȥ���������˹��鹩�����Ķ�������Ϊ�����¾��������������磬���������Ӵ���������˼��������������ĸ����ϼ��Ҳ�ľ��IJɣ�ʱ���̵���ʶ�֡���ʫ��
��������������˽�ӣ�����ĸ��ȥ����ʮ����������������������š���ʮ����ʼ����������ʿ�߸������졢λ���ϲ���Ӣ��ҹУѧϰ���ġ�1914�꣬����ʮ���꣬�����������Ρ����ಮ�ȸ������˴�����Ϻ�������ѧ����ʱ����ɽ����Ϊ������ѧ���»���ϯ��
���������ڸ�����ѧʱ�ڿ�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