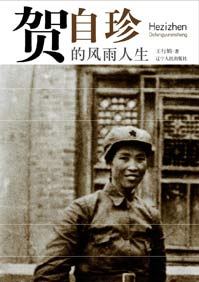军情风雨-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董央忽然在树林外的海岸上还有一台重型武器,他认准这是中国大陆的四联高射机枪。机枪有4个轮轱,4条粗大的枪管平视海岸。树林中站着一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高大肥实,他的军用皮带上挎着一支大号的速射手枪,嘴角上叼着一支雪茄。四周都站着手持M…——16型突击步枪的士兵。海董央腥涩地冷凝,火在燃烧。从树林里传出一声声惨叫,董央更觉着奇怪,便悄悄向草坪走去。这一声声凄厉的叫声在昆仑岛上回荡,惊起夜鸟在岛上盘旋,而那个在草坪中间站着的高大胖子一点不动声色。这个人叫格拉斯、豪森,他的蓝澄澄的眼睛里放射击出阴冷的光芒,这时他走到树林边对着被吊在树上的一个人,回过头来说:“密斯特陈,狠狠地给我打!”董央站在树林边缘,看见一个中国人模样的人手提一支AK47走过来,这个人头上戴着红色的的贝雷帽,又在篝火上多加了几根木柴,然后又用刺刀拨了几下篝火。篝火上吊着一个一个年轻人,他双手被反捆着,两只脚荡在空中,脸上呈现出痛苦的表情。篝火烤着他的脸,头戴红色贝雷帽的人走过去,挥舞起皮鞭,一下下打在他的腿上。
董央看了一会,明白了:这是著名的国际雇佣军,他们就是通过样的方式训练士兵,然后把这些经过严格训练的战士输送到战场上去。在这个蛮荒的岛上,谁也说不清楚有多少人,到处都隐隐约约地看见有人在活动。昆仑岛极少有人到这里来,因此美军利用这个荒岛一直作为训练基地。曾经有一批法国职业军人出现在岛上, 这些人曾无数次转战安哥拉、苏丹、利比利亚等很多非州国家,他们的足迹走遍了世界。台湾、韩国还有东南亚一些美国的盟友,先后派出自已的作战人员到岛上集训,以台湾和韩国最多。他们以哨鹅为训练的前哨,只要听到长长的鹅的叫声,就知道有情况。董央站一旁,听一个同样是台湾来的人给他介绍,这个自称姓陈,他悄悄来到董央的身旁,慢慢地向这个新来的间谍叙说。
“我叫陈文张。”这个陈文张通身迷彩服,腰挎手枪。
董央没有理会,他明白这是台湾特工的离奸计。军统惯用的手法。
到了夜间10点左右,长长的哨鹅的叫声,惊骇地响彻昆仑岛,岛上的武装迅速散开,那个被吊在树上的年轻人,被一把锋利的匕首割断,跳下来,从旁边起一支枪马上投入战斗。
2008年4月,美国福特图书馆公开了一项秘密:当年中央情报局有人协助大陆间谍,在岛上炸毁了数台中国制造成的四联高射机枪,在长达近20 年的越战中美国共有58000人在战斗中丧生,有同盟国的500多人的特工牺牲在各条战线上,其中台湾队派出的特工在大陆失手或丧命的最多,也最不值钱,命如草芥。
三个月后,董央与陈文张共赴大陆。
董央的代号被命名为“兔子”,肩负起在塔利班后方刺探俄罗斯和中国军队的情报工作。董央与陈文张共同走在死亡线上。这时侯台湾军事情报局在阳明山单独接见台湾情报人员,时间是2001年7月13日,当时已听闻到了一些*的叫嚣。董央作为台湾老一代特工,基础是很好的,这话是蒋经国先生在与情报人员时的讲话。当时,正值秋高气爽,台北的季节性海风来到阳明山别墅时,数只天上飞翔的红嘴鸟站在窗前的一棵树枝上,军情七处处长板着脸说了一番鼓厉的话,他说:“0319号同志,这次特别将你请到我的办公室里来,我想是有特别重大任务的……”
董央的真实名字,这时侯才被处长说出来。董央作为国民党的第二代特工,他意识到这次出行将有重大任务,但蒋经国没有说出。不过,从处长的愤慨之情可以看出,这中非同小可,董央听蒋经国说了这么一句:“谁想在台湾搞独立,老子就要搞他的脑袋!”
蒋经国离去后,由台湾情报机关几个人,相继与在坐的三个特工谈话,董央就是其中之一,这给董央极深的印象。台湾机关原本是通过调查了解到:董央特工的儿子还在台湾,1949年随蒋来台后,几个子女都在台湾相继长大成人。
董央的女儿在台湾所谓的“自由中国之声“广播电台”,每天向大陆同胞广播。
“你女儿叫什么?“”情报官员问。
董央回答:“董春志。”
一周后,情报官又问董春志:“现在你们一家都好吧?”
“都好,只是父亲还在大陆,至今没有消息。”
“找过吗”
董春志如实回答说:“我们工作站同志曾深入大陆数次,都没有发现父亲的行踪。”
台湾情报机关对董央说,这次你从昆仑岛回来后,原本是要派你到阿富汗去的,现在情况有了变化,你要伺机在适当的时侯暗弑陈文张,明白吗?”
当天夜晚,台湾第六情报处阿富汗工作站站长来到董央的房间,明确告诉他:“这个陈文张就是暗藏在我们内部的*份子,老蒋几次过问此事,说“这个人几次滑脱,令老蒋极不悦。董央的特别任务就是早日除掉他,完了提陈文张的人头来见我!”
现在老蒋不在了。
当年,非州丛林的枪声,南亚大陆膘悍的特种兵,这对董央来说都是小菜一碟。这帮人沉不住气了乘飞机赶到了阿富汗与苏军。董央在进入阿富汗之后,显得很惶惶,董央化装成一个叫花子,很快又演变成一个韩国军官潜入伏地,一个人拍了一下董央的肩膀,意外地发现董央是一个哑巴,便摇摇头离去。董央在越南南方出入舞厅、车站是很危险的,一旦有人发现他后果不堪设想,他后来在阿富汗的南沙瓦消失在一片寂寥中。在数度出生入死的征战中,董央还是第一次来到阿富汗这个极度贫困的山区,看到一个韩国女人到这里来销售摩托车,感觉不可思议。越战中,董央曾一个人深入北越军队的营地,一个人扛着单兵火箭摧毁北越的一个营地,手提机关枪潜入越南游击的腹地,消灭了美军一个特种部队的一个排,伸出一双手将一个受困的中国军人救出。董一卓对中国大陆军人是陌生的,但一见是中国人,一眼就感觉亲切之至。董央服役到过安哥拉、古巴和索马,他深为战争气氛所感染来到阿富汗。人生的情感是极其细微的董一卓当晚离开了越南的昆仑岛,去向不明。
奇迹出现在这场没有解释的战争期间。
自那天参观过台湾205厂回到台北,董央立即去了一家高级洗脚城。
2007年3月27日,谁也没有想到董央这个出生入死的老军统,已经投奔红军的老董,回到杨家坪准备执行我有关部门的“春晓行动”时,不明不白地冤死在春天的阳光下,在成渝高速路上瘫痪了所有的身体零件,120赶到时早已没有了呼吸。交警将此案列为重大交通事故后又称至我有关部门,据悉仍不了了之。因为肇事司机和司机的一个副总也在这次重大交交通事故中魂飞魄散,哪里还找得到全尸,其膘肥体壮的将军肚及其肚皮也肝胆破裂。
台湾特工原本是想在成渝高速上撞死*份子陈文张的,没有料到另一个老董成了替死鬼。当然陈文张之后的结局早在预料之中,台湾间谍机关原本是给已经赴大陆重庆的董央发去电报,瞩他加快行动,跟一个叫周渝生的人衔接。
现在,“老董”先生牺牲了,台湾所谓参谋本部国际处全体员工无话可说。
他们很快把目标锁定到了一个叫周渝生的人身上。20的前,台湾就有人把周渝生锁定到了眼里,20年后周渝生不知去向。
奇迹发生在董央停在殡仪馆的第二天,老董竟然从棺材里爬了出来,一个人不仅到处游走,还捉住了附近法院一个翻墙的小偷。是这样的,原来董央是被另外一人替代成了死人。一句话,死的人酷似老董,但绝不是老董。
复活的死人与活人的死去,然后又奇迹般搬上所谓荧屏就像牛皮匝,匝牛皮出现在今天的中国,并不是一件稀奇有事,就像某大夫把左腿的钢板上到右腿上,而右腿完好无损。
董央正在跟重庆丫丫摩托老总周渝生衔接,准备在摩托车和汽车的经销上大干一场,却是不争的事实。
十
郁雪红工作的某企业是前苏的一个重要部门。
在中国还没有进入小康之前,全国各地的厂矿企业都是大锅饭,领导者必须一碗水端平,否则但有砸锅之虐。同时,当时的上海人特别喜欢跟比四川,说四川地区的工资晋级特别是 重庆的企业,工人之间是互相谦让,很有一点雷锋精神,尤其应值得上海的工人同志学习。四川的又跟上海的比,说法同出一辙。不过,就郁书记工作的重庆一大型企业来讲,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是大锅饭,晋不晋得到工资有很多变数,首先是你所在的单位的所谓人员构成情况,你是年轻人,如果老师傅多那你就得等下一班车,甚至末班车看有没有你的戏。上世纪70年代有一次大面积的涨工资,即所谓的百分之四十对人们有很深的印象。百分之四十,很显然,那么除了这百分之四十之外,还有百分之六十是没有希望的。正因为还有百之六十的人涨不到工资,工厂就来了个考工晋级,理论实作各占百分之五十,这下该没有问题了吧,正是这个时侯其实再不然。
在中苏交恶期间,这个单位门口24小时还有解放军持枪站岗,以守卫我们中国人来之不易的重要成果。人不多,不到二百人,但肝胆俱全,机床设备是一流的,制造的产品是保密的。车间门口挂着一个小木牌:谢绝参观。因此,在这个车间工作的人都保持着一份神秘感和自豪。苏联专家走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国人可以随便进出,来找人谈事的来找人耍朋友的隔三差五不断。于是这就给后来发生事埋下了定时炸弹。
考工晋级首先是考理论,复习资料事先发到车间班组,让每一个人吃透,摸熟,然后反反复复地背。郁书记是在建设一小黄家院子的教室里考的理论;郁书记看见好些抗战时期的老工人很是为难,首先一点这些身怀绝技的前辈能够识字的寥寥无几,写不起自已名字的占百之八十以上,绝非大有人在。考实作,考官便是车间书记、主任组成的所谓考评组,站在你操作的机床边观看,不时拿着笔在本子上记,这实际上就是在给你打分了。
最后的战斗才是最关键的,这期间大伙议论纷纷,很多民间不平非的事都在此刻化干 为玉帛,互相问长问短,其实都在探听虚实。时间在一分一秒的逝去,这个时刻终于到来了。公布晋级名单的时侯,真正是革命熔炉火最红。车间一个调度在得知自已无望的情况下,一声不吭,他开始了作最后一搏的准备。早上上班是8点钟,这个调度员同志一个人就在砂轮上磨默默地磨锉刀。最初是一个人发现,很快就有了议论声,大家各自站在自已的工作岗位上望着正在磨刀的那个调度。这时侯是机电组的一位解放前进厂的老师傅,在众人的支持下从板凳上站了起来,悄悄地向砂轮机走去。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不到二百人的车间,这时再不没有发出所谓机器的欢唱,相反整个车间只听到一台砂轮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