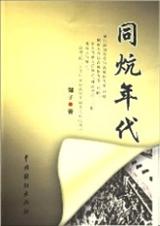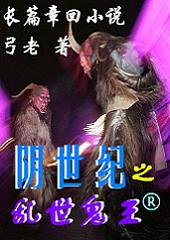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第68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地理学家则站在地质变迁的角度解释说:在数千年的沧桑演变中,是黄河以自己巨大的水力,在此冲出了三路山口。不管是大禹用斧劈开岩石,还是黄河的水力冲开了山口,三门既开,从此,黄河顺峡谷滚滚东流,百姓得以免受水涝之苦。
但那滚滚东去的泥河却在不断把隐患埋在母亲河中——每年淤积在下游河床中的泥沙达4亿吨之多,使黄河成为高出地面十余米的“悬河”。一有风吹草动,“悬河”便面目狰狞地扑向河下的生灵,一次次把灭顶之灾降临给“黄河儿女”。
黄河上的航行者在三门峡这样的河段也常遭厄运。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在奔腾咆啸的三门峡里,船毁人亡,埋尸鱼腹者无数。
顽强不屈的黄河儿女从来就不甘命运的摆布。早在汉代,就有人想在三门峡另辟一条河道,避开天险。唐初,一条长300余米,宽6米左右被民间称为娘娘河,史书上载为“开元新河”的人工运河终于在“人门”以北处开出雏形。可惜这条石质运河,水浅时不能通航,水大时湍急又有毁船之险。娘娘河的开凿者便又在山崖上开凿了一条长9公里的砥柱槽道……
当地人说,唐朝人当年在“人门”开凿运河之所以不能成功,主要是因为?三门峡的岩石——整个峡区差不多全是质地坚硬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
此后,频频向黄河挑战并想制服黄河的后来人看中的恰恰是三门峡理想的库容和质地坚硬的岩石。
1934 年,一群背负着标杆、罗盘、测尺的外国人在野兽出没,涛声如雷的三门峡岸边跑前跑后地忙活着。领头的是荷兰水利专家尼佐夫和英国水利专家柯德,他们受国际联盟派遣来华考查,其目的是要针对黄河的汛期泛滥,以水库蓄洪的办法来削减洪水下泄量,以此减少黄河下游的灾难。在他们考查的众多坝址中,两位外国友人都一致认为三门峡是“最理想的坝址”之一。同年,黄委会挪威籍主任工程师安立森在与中国工程师共同勘察了陕县至孟津干流河段之后,他们惊喜地向中国政府报告:“三门峡实在为一优良库址”,在此修建每秒泄量为12000立方米的高坝大库绝无问题。
四年后,三门峡地区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一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黄河下游大部份地区沦陷。高嚷“大东亚共荣圈”大举军事进攻的日本侵略者为收买人心,得到战争迫切需要的能源,也把“治黄”定为了自己的“大业”之一。他们抽调专业人员近300人,沿黄河像模像样地开展研究与规划,编成了73万字的《黄河治理规划的综合调查报告书》,提出了“黄河中游梯级开发”方案。拟将在从清水河至小浪底共500公里处建11座水库,总库容为800多亿立方米,并伴以庞大的造林和发电计划。在这众多的水库中,三门峡是其中最大的一座。考虑到淹没耕地和迁移人口太多,工程可分两期进行。若以潼关洪水位325米为限,第一期坝高61米,总库容60亿立米,发电能力63·2万千瓦;最终坝高86米,总库容400亿立米,发电112·3万千瓦……
《黄河治理规划的综合调查报告书》的计划刚刚形成,计划的编纂者们却在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楚歌声中黯然回到了他们的那个弹丸之地。那份倾注了计划者不少心血且的确颇有见地的《报告书》,大多销毁散失。
战争的硝烟还未散尽,1946年夏天,国民政府水利委员会组成以张含英为团长的考察团,分水利、水文、地质、河道对黄河中上游作了考查。一篇《三门峡水库是这样上马的》的文章中对随后的考察作了这样的记述:
这年冬天,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聘请美国专家,组成黄河顾问团:豪爽的美军工程师兵团总工程师雷巴德中将,他的助手葛罗顿中校,再就是著名的与中国两条大河有着不解之缘的著名高坝专家萨凡奇博士和他的助手柯登。那年,中将七十多岁,博士也已六十出头。美国人仔细研究了那残存的、由日文译成中文,再由中文译成英文的文件,先沿黄河考查,然后,以美国佬一贯的风格,在开封大吃酒肉的同时对每个问题都激烈争论,最后给中国政府写了一份三人签字的文件:《治理黄河规划初步报告》。在肯定了日本人“研究精详,若干建议颇足称道”之后,他们主要给出三条意见:
1。凡拟在黄河中下游兴修水库,都应当以防洪为首要任务——一句话就把日本人在干流建发电站的设计否定了。这水库若修在包头至龙门间,存量均小,寿命必短。
2。在三门峡建库发电,潼关以上农田淹没损失太大,是日后无法弥补的。故建议建坝地点改移到三门峡以下100公里的八里胡同。此时建坝回水到潼关,形成峡谷水库,避免潼关以上的农田损失。
3。在八里胡同建库,不是为发电,而是作为防洪的滞洪水库。坝下安设巨型闸门,控制流速,使泄水的含沙量保持某一定值,数年之后泥沙冲淤平衡。 美国人的意见都是原则性的,而且主要是否定性的。可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修建三门峡水库时,决策者们怀着民族与阶级偏见而未对它加以足够的注意,为此,刚“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付出了昂贵的“学费”。
“圣人出,黄河清”
黄河洪水这道难题,历朝统治者们都未能将它做好。所以,新中国的旗帜刚刚升起,西方学者就大胆断言,共产党能够夺取政权,但没有能力治好黄河。这咒语一样的预言一直像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困扰着新中国的领袖们,几年后,初期治黄的三门峡工程果真失败,西方人一语成谶。
有人说,面对桀骜不逊的黄河,新中国领袖毛泽东矛盾的心情中表现出的半是敬畏半是无奈——“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这种底气不足的吩咐,有点不像当年以一首气吞山河的《沁园春。雪》而震撼中国,震慑他的敌人的那位毛泽东。
此话的确有些道理。不管是以古代还是用今人的评判标准,毛泽东战争年代在马背上吟成的那首古体词《沁园春。雪》的确当算古今咏雪诗词之绝唱。其词移情入景、力诱纸背。尤其“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等句,有“横绝六合,扫空万古”之势,历代帝王、英雄人物统统在毛泽东笔下席卷而去,一代伟人超凡脱俗的豪情壮志和雄伟壮阔的胸襟气魄跃然纸上。
1945 年8月,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同国民党谈判期间,这首词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后,轰动一时,从词中大气磅礴、气象雄浑的王者风范中,蒋介石感觉出了一种无法容忍的轻蔑,便令手下的文人墨客纷纷唱和——他想以更有气势的诗词压倒毛,结果,43天的谈判结束时,也没有一句能超过毛的词句,气得蒋介石大骂:娘希匹!
不过,历来都藐视一切的毛泽东对黄河却充满了敬重之情。据载,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东渡黄河进行作战转移时,面对滚滚东去的黄河,毛主席对身边的人说: “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藐视,就是不可以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啊!”此后,在多次对黄河的考察时,他都重提了这样的话题。
对敬畏有加的黄河,毛泽东一直想进行详细、深入的考察。他曾说,他很想骑马跑跑两条大江(长江、黄河)。后来,他还真的要去实现自己的这一愿望——准备组建一个智囊团,吸收天文、地理、地质、历史等方面的科学家参加,骑马沿黄河而上,直到黄河源头,对黄河两岸做一次系统的社会调查和自然考察。
不过,毛主席的黄河之行终究不是骑马去的,也不是在他预定的那个时间去的——五星红旗升起之后,他第一次离京巡视的就是黄河——当时,他急需去的地方很多:毗邻朝鲜战场的东北,与台湾蒋军对峙的福建,经济斗争复杂的上海……
但他却选择了黄河。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应该到黄河看看了——早在1949年8月,后来成为新中国黄河水利委员会一把手的王化云起草了一份建议《治理黄河初步意见》。该文件主张在三门峡建蓄水水位350米的大坝,“以发电、灌溉、防洪为开发目的”。但当时的水利部在复勘之后,认为从当时国家政治、经济、技术条件来考虑,不适宜在黄河干流上大动干戈。
当时兼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对于中国的农民、农业特别是并不富余的耕地有着深刻的认知和关怀。1953年5月31日,邓写信给毛泽东:“关于当前防洪临时措施,我意亦可大体定夺,第一个五年,先修芝川、邙山两个水库……度过五年十年,我们国家即将有办法来解决更大工程与更多的移民问题。”
此后,修三门峡水库的事搁置了下来。但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治理黄河之事。1952年10月最后的几天,毛泽东主席利用党中央给他的休假时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黄敬等人陪同,乘专列南下徐州,然后溯河而上,分别在徐州、兰考、开封、郑州、新乡等地对黄河进行考察。他想通过自己的实地考察为三门峡水库的修建提供一些直观的依据。
对于毛泽东主席的这次黄河之行,后来出现了大量不同版本的回忆录等史料,这些丰富的史料都同时记录了这样一些情节:
1952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山东省负责人的陪同下,从济南市乘轿车来到黄河之畔的洛口镇,下车后,登上黄河大堤。毛泽东边走边问陪同的地方干部:“早就听说黄河水灾很频繁,危害很大,你们能不能说说具体情况?”
地方干部告诉毛泽东:自古以来,黄河下游以善淤、善决、善徙著称。据有记载的2000多年里,黄河下游河道以郑州为扇轴,在黄淮海大平原上,北起津沽,南至江淮,南滚北移,共迁徒26次,平均每隔百年改道一次。最近一次改道是在咸丰5年,黄河在兰考县改道后,夺大清河入渤海。改道后的河道,就是现在的河道。如今,这一河段已淤成地上悬河,河床高出济南市区5米,高出开封10米,高出新乡市竟达25米。
“高出这么多?”毛泽东惊讶地说,“真是悬河,悬在人民头上的河,不可掉以轻心哪!”
地方干部说:“黄河自公元前602年,到1938年蒋介石下令扒开花园口的2540年中,总计决溢1590次。若分段来看,西汉时期,平均14年发一次大洪灾;唐代前期平均10年一次,后期7年一次;唐末至五代,平均三年多一次;北宋和元代是一、二年一次;明代二年一次;清朝平均二、三年一次;民国前十几年水灾相对较少,后十余年天灾人祸、水灾不断。”
毛泽东沉思片刻,指着黄河:“按你刚才所说,黄河水灾的次数是越来越频繁啰?”
“过去是这样,不过,自黄河1947年回归故道后,经过解放区人民的努力,加上解放后开展了大量的治黄工作,黄河虽然发过几次大水,但都没酿成灾害。”
“那就是说,黄河五年没有侵害老百姓了,”毛泽东扳着指头算了算,笑了起来,“五年太少了,要保证黄河年年安澜,岁岁太平。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