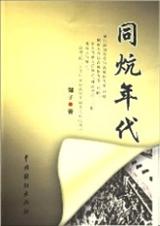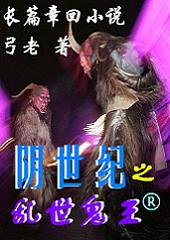大迁徙(长篇纪实文学)完整版-第3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环⒌亩鳎庵荒苁且桓鲂榛我磺沟那蒙秸鸹⒑痛虿菥叩恼绞醵鳎谙疑隙荒苷嬲鸭涑鋈ィ鞒觥扒蒙健焙汀按虿荨闭庋亩鳎康闹皇窍抛呃匣⒑蜕撸皇钦娴囊搿袄匣ⅰ焙汀吧摺倍犯瞿闼牢一睢O朊靼渍庑┖螅匙ㄔ奔僮懊挥锌醇粜《酒鹄词蹦歉鼍哂刑粜菩缘亩鳎宦渡胤畔虏璞绦郧坑驳目谖撬档溃骸按送猓ǜ娓魑灰泼翊恚悼馐敲つ康模彩谴砦蟮模鹗ё愿骸1鸶姨旨刍辜郏换岣质碌娜烁魏魏么Γ』匾驳没兀换匾驳没兀∶挥惺裁唇驳牧耍飨刈橹致邸�
讨论的目的仍然只是“震慑”。但此时的震慑力显然大不如某专员在会上的“动员”了,移民代表纷纷“发作”,把在会上挨专员骂的怒气一齐撒向主持讨论会的书记、县长们,他们指责行署领导不认真落实中央文件精神,埋怨地区领导太武断,太欺负移民,大家好不容易在库区种了一季庄稼,眼看就能收麦子和油菜了,却硬要把移民往回赶。那么大的损失谁来给移民补偿?聂小二等人甚至当着库区县委书记、县长的面高声嚷道:不赔损失我们坚决不撤走。并且,几天时间,一下撤走这么多人,怎么来得及,不走!……
移民中,也有非常合作的。一直相信移民问题最终还必须由政府解决的蒲城县移民返库司令王福义在会上被“震慑”了,他当即表示,“移民的事情,非共产党、政府解决不可,我和党保持一致。”
行署领导乘机用诱人的利益冲开了移民的最后一道防线:返库期间移民所种小麦和油菜每亩补偿40元。
这种经济上的补偿满足了部分移民心理上的需求,王福义和他的蒲城旧部怀揣补偿款撤离了库区。怀着对移民的负疚心理和甘愿为民请命而闹返库的温和派陈文山也带着人马离开了已是麦浪翻滚的库区。
送走了王福义和陈文山,政府腾出足够的力量去对付不肯参加“农机学校会议”的苗福群和刘怀荣。手法仍然是先礼后兵:让公安局给其送去“警告书”:限三日内回去,不回去,采取强硬措施。
这一招果然再次不战而屈人之兵。刘怀荣对记者说:收到那玩意儿后,我便在一百多移民的保护下撤离了库区。当时之所以要撤,一是因为王福义和陈文山撤走后,库区移民的犄角之势已失,无法相互支援,当时的正确选择是走为上计,寡不敌众的我们只有撤退。二是中央当时已着手解决移民遗留了二十多年的历史旧账,我们再对抗下去就没有道理了。加之他们直接冲我的总指挥部而来,所以,我们当时撤得有些仓促。
在仓惶而撤的刘怀荣离开库区的同时,苗福群也在夜幕的掩护下,由麾下的骨干李孝玉用摩托拉着潜回了澄城县安置区。刘、苗二部的残部被政府的优势兵力连打带骂地强行架上车拉走。
被库区人刻骨铭心并引以自豪的第十七次返库大潮又退落了。不过,这次大潮退落时的最后一排浪花,却冲毁了移民返库的最后障碍,为历尽劫难的关中移民迎来了回家的福音。
在17次返库风波中叱咤风云的四大移民“司令”除刘怀荣之外,王福义等人先后以其凄凉的结局向故土,向几十年来与自己同甘共苦的移民及自己的人生作出了悲壮的谢幕——
陈文山未能活着回到家乡雨林乡。政府批准返库时,他已病入膏肓,那页薄薄的返库的通知虽像一剂救世良药,但终究没能使这位为移民获得一个公道而终身殚精竭虑的农民司令起死回生,而只是在他危弱的生命体征中激起了一丝绝望的回光返照……
苗福群、王福义回到库区后,在他们夺回的土地还没有恢复往昔的富庶前,便相继默默地死于贫困之中……
唯独刘怀荣在多灾多难中无病无痛地“寿比南山”,并再次成为库区维护移民权利的领军人物。
第五章 劫后“伊甸园”
26、故土已荒芜
到移民返库工作宣布结束的1988年底,7。3万多名移民回到了三十多年来一直魂牵梦绕的那个“伊甸园”。
还乡者重归故土的情景凄凉得令人心酸:没有敲锣打鼓的欢迎,没有谁理会他们归后的食宿,甚至没有人给他们递上一杯茶水。“公路上蠕动着一支几乎可称作难民的队伍,一户又一户的移民自己拉着架子车,肩挑手提着破烂的家当,人们默默地走着,没有欢笑也没有生气……”
源于甘南的渭河自从有了三门峡电站后便在流水不畅的河床里疲惫无力地缓缓流经关中平原,这条黄河最大的支流,陕西人的母亲河只能拖着她羸弱的躯体,平淡而冷清地迎接她的儿女回归到自己身旁。
回到黄河滩上,关中人心目中的那个“伊甸园”如海市蜃楼一样消失得无踪无影,映入“难民”眼中的故土已荒芜衰败,满目疮痍——昔日的房屋早在三十年前就被拆成一堆残垣断壁掩没在杂草丛中。炊烟袅袅,鸡鸣犬吠,牛欢羊叫的情景已成了所有移民久远的梦中记忆。鸟语花香的家园不见了,原来人们引以自豪的绿洲不见了,被农场砍成一片白花花的树桩怒目苍天,向旧时主人诉说那场疯狂的砍伐给这片土地带来的灾难。
迎接移民们的土地也是那样的贫瘠瘦弱。陕西省的全国人大代表马百党曾愤怒地指出:“返库移民只是得到了少量的贫瘠土地,库区过去原本属于移民的肥沃土地,大部份仍然被部队和国营农场经营着。”
事实上,移民得到的土地不仅仅只是贫瘠,1986年,移民返库安置时,国营农场和部队农场所移交安置移民的土地大都分布在库区的沿河与堤外地带。三门峡水库引起的黄河回水垫高了黄河及渭河的河床,使黄、渭、洛(河)三角洲的地下水位普遍升高了2至3米,原来的平原地带变成了低洼地。土地大面积盐碱化、水涝化已成为难以遏制的现象。而移民接收的盐碱地和涝洼地达12万亩,占划拨给移民使用土地的40%以上。
这40%以上的土地在作家冷梦的笔下“像是一个失散了二十多年的女儿,二十多年后,骨肉团聚,女儿却不再认识他们。她变得暴戾无情,变得刻薄悭吝,仿佛她曾被恶魔掠去过阴曹地府一遭,心肝肺脏全被换过……”
“换过了心肝肺脏”的土地也改变了它原来令人羡慕的“容颜”。在库区采访期间,记者不时看见大片大片如雪似霜的白色物覆盖在土地上。移民们告诉记者,这是盐碱地,这种盐碱土是无法耕种的,若要对其改良和利用,必须经过排盐、洗盐、降低土壤盐分含量;再种植耐盐碱的植物,培肥土壤;最后种植作物。具体的改良措施是:排水,灌溉洗盐,放淤改良,种植水稻,培肥改良,平整土地和化学改良。
衣食无着的移民要以这样的程序改造这样的盐碱地谈何容易。一老移民告诉记者:当时,我们吃水都成问题,哪里还有水灌溉洗盐,放淤改良?
即使是这样的盐碱地和涝洼地,还埋下了因破坏生态而使其进一步恶化的灾难隐患。第一批难民回归之时,库内的那场疯狂的砍伐还未结束。苗福群“司令”的“秘书”聂小二对那场极其疯狂的砍伐至今仍记忆犹新:国有、部队农场在交出土地前夕,像发疯的“屠夫”一样对库区那些郁郁葱葱的林木进行了毁灭性砍伐。返库的移民老远就看见拉树的汽车不断来来往往,咚咚咚的砍伐声和哗哗哗的拉锯声不绝于耳,倒下的大小树木挡住了道路,公路两旁、村道渠边,房前屋后,全是白碴碴的树桩……
聂小二也加入了苗福群组织的阻止砍伐的拦车护林队伍。但对峙了一阵,移民被闻讯赶来的政府干部连拉带劝地弄走了。看着拉满树木的卡车远去,拦车护林的移民心中充满悲愤与怆然。他们深知,失去林木护卫的黄河滩将大难临头,报复的黄河水将漫上滩来吞噬这片土地,夺走这里的富庶,把饥饿、贫穷留给它原先的主人。
这种可以预料的结局果然很快来到,数年间,大自然能够给予人类造成伤害的旱、涝、洪、碱和塌岸等等灾害在曾被人们羡慕不已的那块叫“关中白菜心”的地方粉墨登场,轮番肆虐。
三门峡水库建成后,黄河主流逼渭河倒流,使位于黄河西岸的陕西大片大片的土地塌进黄河。渭南市移民局原主任郑博(化名)告诉给了记者这样一组令人吃惊的数据:移民返库后到他退休的2005年,库区因塌库而损失的土地就有三万多亩。他说:这三万多亩都“长”到与陕西隔河相望的的山西省永济县去了。这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如今仍留在白水县尧禾镇的移民姜宏哲至今还记得:“农场那些并不懂得土地,更不热爱土地的的农工们多年掠夺式经营使土地变得贫瘠不堪,我们回到库区时,田里荒草长得老高,人在地里劳动看不到人的影子。原来那些肥得流油,一季能产七八百斤小麦,五六百斤花生的地都板结了荒芜了,根本无法种庄稼,所以,我们回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荒。”
荒地还未开完,灾难降临了——1987年到1990年连续四年大旱。从白水县移回华阴市的姜宏哲回忆说:那四年,种植的花生、豆类全部受旱减产,玉米不结
玉米芯,棉花不结桃,一亩地只能收一百来斤花生,一亩棉花产量也就三五十斤。这样的产量都只有我们离库前的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左右。特别是1988年七八
月份,五十多天没有下过雨,晒裂的地里可伸进拳头,花生苗拔起来可以点着,半人高的玉米全是一片焦黄……
“土地被糟蹋得无法耕种,我们伤心透了。”满怀希望回到库区的姜宏哲又带着对故土的绝望和悲伤回到了安置区。
“闹”着回库区又黯然神伤地离开库区的绝非姜宏哲一人。1987年6月,白水县尧禾、西固等镇的800多移民兴高采烈地离开“种地靠天,煮饭无水”高山旱塬,回到了华阴孙庄村。孙庄村的那片被农工“换过了心肝肺脏”的土地也毫不客气地对800白水移民当头一棒:荒芜、沙化、盐碱化、旱灾、水灾接二连三地坑害这片土地旧时的主人,使得这个已被折腾得一穷二白的群体瓦上加霜,深陷绝境。
煎熬返库移民的不仅仅是连年旱灾造成的衣食无着,恶劣的居住条件更是严重地威胁着他们生存。初回库区的7万多移民几乎没有一人建过瓦房,全是清一色的的庵棚。华阴县西阳乡原分管移民工作的副乡长郭中举至今还记得:1987年后,华阴的华西村,大荔的平民乡等移民安置点一排排、一片片全是星罗棋布的庵棚。这些庵棚里没有自来水,一般要一两百户人家共同筹钱才打得起一口井,移民们吃水都要到很远的井里挑;庵棚区域里没有电灯,家家户都只有用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或者用破碗、灯草做一个“桐油灯”;偌大的庵棚区大多没有厕所,人们大多是在庵棚旁挖个坑,再牵上一块遮羞的破布,那便是厕所了。有位乡干部说,哪里若臭气熏天,那一定就是移民的庵棚区。庵棚区没有排水系统,移民们常常是将用过的污水随地乱泼,所以,庵棚周围永远是污水横流。偶遇下雨,雨水会将“厕所”里的屎尿漫出,溢向庵棚区的每个角落。
庵棚内的情况更遭。不到两米高的庵棚矮小黑暗阴湿,四壁透风,居住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