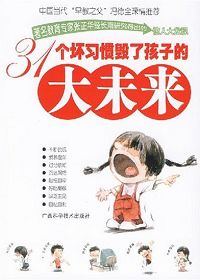31天穿越罗布泊-第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下午,我们进入了雅丹地貌群。据地质专家说,这里曾是古罗布泊的湖底,面积相当大。
雅丹,是维吾尔语“雅尔当”的音译,意思是“险峻的土丘”,是风婆、雷公、电母、雨神们锲而不舍的杰作。从第四纪开始,连绵不断的风剥雨蚀一层层地搬走了第四纪沉积物中疏松的土层,把这些坚硬的泥岩或石膏胶结层暴露出来,经过几百万年,这些坚硬的部分越“长”越高,形成了今天凹凸相间、奇形怪状的土丘,这种地貌就是“雅丹”。
“雅丹”是怎样成为地理学专业名词的呢?这要追溯到上世纪初。当时一些赴罗布泊考察的西方学者在罗布荒原中意外地发现了这些土丘,他们感到很惊奇,于是询问当地维吾尔族向导这是什么,向导说:“雅尔当。”于是,西方学者们就鹦鹉学舌地将这个称呼介绍给了世界,成为地理学的专业名词。我国学者再由英文直译回来,出口转内销的“雅尔当”就变成了“雅丹”。
因天热,我们在雅丹的阴凉处稍事休息,胡乱地吃了几口饼干,继续西行。此后,风景变得丰富多彩,让人目不暇接。大小不等的沙阜土丘,鳞次栉比,它们各显身姿,争奇斗怪,有的如擎天一柱,有的如青松茂竹,有的如亭亭华盖,有的如灵芝蘑菇;有的像雄狮怒吼,有的像猛虎下山,有的像孔雀开屏,有的像群鱼出海;有的似神怪魔鬼,有的似魑魅魍魉,有的似天龙八部,有的似外星来人;也有状如西欧中世纪城堡、古刹宝塔、马帮、舰队的……一切皆有形,一切皆幻然,看花是花,看蟾是蟾,全在于观者的心生心灭。
第三章 第3天——断乳的母亲河(2)
亿万年的地质变迁,不分昼夜的水流风蚀,把地表塑造出千奇百怪、形态迥异的地貌,如河谷地貌、岩溶地貌(喀斯特)、冰碛地貌、风蚀地貌等等。也因此造就了许多天然的地质公园,如举世闻名的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中国云南的石林、贵州的地下溶洞等等。雅丹地貌很少为世人所知,我觉得它的魅力丝毫不亚于其他同为世界名胜的地质公园。
魔鬼城的幽灵
不知不觉地渐入佳境,我们走进了著名的“魔鬼城”。“城区”东西长约二十五公里,南北宽约四五公里。这里的雅丹雄浑伟岸,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雄姿英发。若登临“城堡”的最高处向下俯瞰,“城”便幻化为海面,雅丹变幻为岛屿。风和日丽时,波澜不惊,可赏蓬莱仙境;沙暴骤起时,飞沙走石,可闻铜琶鼙鼓。我一直在仰视,仰视这鬼斧神工,仰视这奇崛的地貌,它们确实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走在这里面,天高十丈,地阔九尺,那种感受真是难以言表。
看雅丹也如看庐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我认真地观察,发现这片雅丹地貌群远远超出了书中介绍的规模和形态,其个体和整体规模之大,形态之奇异,实属罕见。由于千万年的风吹日晒,地表平坦的砂岩层形成了风蚀蘑菇、风蚀柱、风蚀垄槽和风蚀洼地等各种形态,风的艺术天分,令我叹为观止。
这里雅丹的高度,低的四五米,高的二三十米,长宽在十几米到几百米不等。整体像一座西方中世纪的城堡,有壁垒森严的城墙,有曲径通幽的街道,有高耸的大楼,还有宽阔的广场。教堂风格迥异,雕塑流派纷呈,所有的形象无不栩栩如生,无不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我在魔鬼城里,找到了许多世界著名建筑的缩影,宛若进入了建筑艺术博物馆。
城里也有许多“花园”,点缀着惟妙惟肖的“蘑菇石”、摇摇欲坠的“摇摆石”、随风摇曳的“风动石”。我一路赞叹,一路惋惜,敦煌雅丹太值得开发了,这是一块难得的特色旅游宝地。
尽管我对雅丹地貌万分的好奇和惊喜,但看着看着,也渐渐地产生了审美疲劳。为了给自己找点事干,我开始边走边研究雅丹地貌内部的区别。
突然,无端生成的几个大旋风在雅丹群中窜来窜去,显得十分怪异,让人觉得惊心动魄。我的朋友调侃说,这一定是戈壁迷路死亡者的幽灵,虽死了无数年,其心不甘,化作旋风,在魔鬼城里寻找求生的路径呢!听了这话,我为之动容,想起了陶渊明的一句诗:“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削发明志
傍晚,我们按时赶到了位于敦煌西北约180公里处、玉门关西北约100公里处的会师地点——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公园里主要是风蚀作用形成的雅丹地貌景观,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全球规模最大、地质形态发育最成熟、最具观赏价值的雅丹地貌群。
提前从敦煌开车来到这里的黑龙江电视台记者、工作人员,以及向导和各地的朋友们,冲着我一阵欢呼。
明天,我将进入罗布荒原无人区,开始独自徒步。为表示自己坚决完成这次徒步探险活动的决心和信心,我决定剪去留了十年的长发。十年前的1998年10月20日,我从哈尔滨出发,开始了一个人走遍中国的长征。那天,我蓄发明志,发誓“不走遍中国不理发”。今天,我要把留了十年的头发剪掉,心里还真不舍。我想轻松地进去,因前方道路险恶,如果我不能活着出来,头发留下来也是一种纪念。负责给我理发的刘少义拿着剪刀也在犹豫,拿起来放下,有点下不了手。我说:“剪吧!”一剪子下来,三下五除二,剪成了一个光头。因没有剃头推子,剪出的效果很“农村”——满脑袋的垄沟、垄台。熟悉我的人觉得不顺眼,有点怪。我也觉得不自在,空落落的像少点什么。当初蓄发时,有人说我怪,今天剪掉了,又有人说我怪。
我算是和“怪”纠缠在一起了。
前些时候,当我最终决定徒步穿越罗布荒原时,许多人觉着我奇怪,已经在路上行走了将近十年,按说该歇歇了,怎么又闹腾起来了?前天,路过二墩村,村里人也觉得我特别怪异,问我:“你去那里干什么?那里都是荒漠、沙丘,别说人啦,连一丝生命迹象都没有。真是个怪人!”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话虽落俗套,却是我人生的写照。
不想这些了,我要为明天准备食物和水。我与给黑龙江电视台做向导的刘和平老师商量了一下,让他给我预埋一些食物和水。关于埋放的地点与方式,也取得了一致。同时,还要考虑随身携带的水和食物的重量。背包在行走中会越来越重,因为我必须保留捡到的石头、野生动物骨骼等,所以我一直在琢磨怎么能把背包的分量减轻。
至于食物,主要是压缩饼干。选择它是因为它有四点好处:一是重量轻;二是便于保存;三是容易补给;四是可以有效地补充能量。
有朋自远方来
黑龙江电视台的董主任、邢喆、李黎、苗壮等几个人一直在为明天的直播报道调试设备、研究地图。
而我也要忙着接待今天远道赶来的好朋友们。如今,网络上把户外旅行爱好者叫做“驴子”,把“驴子”之间的关系叫做“驴友”,这种称呼很诙谐幽默,也很贴切。
我的朋友马遥是从北京赶过来的,她给我带来了解放军总装备部为我准备的压缩饼干。从北京来的还有袁动力大姐和王道远大哥。南京的郭小文也赶来为我壮行。中国科学探险协会的王方辰先生亲自给我组装了一套太阳能充电板。我看着他们关切的眼神,鼓励的微笑,还有这些实实在在的帮助,感到无限温暖。我对他们说:“请放心,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成功徒步穿越罗布荒原,回报一直关心和支持我的人们。”
在未来的一个月,我要独自完成每一段路程。但有了这些朋友的关注和支持,有了他们的真情实意,我的内心格外充实。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人的探险。
第四章 第4天——睡在魔鬼的怀里(1)
时间地点
2008年10月12日上午9点,欢送仪式;中午,进入罗布荒原;晚7点,抵达三垄沙。
天气状况
晴,微风。
饮食情况
压缩饼干,矿泉水。
夜宿情况
在三垄沙露营。
踽踽独行,是什么滋味?日复一日地独行,又是什么滋味?我排遣孤独的方式很多:跟自然对话,跟历史对话,跟前面的目的地对话……要想获得成功,必须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冷嘲热讽,耐得住孤独,忘却自我,忘却比对,忘却世间的种种诱惑。吹着口哨,唱着歌曲,一直走下去。这,就是我的生存状态。
隆重的壮行
早晨起来,来自黑龙江、甘肃的记者们一片忙碌:调试设备,准备现场,他们为我安排了一个“为雷殿生徒步穿越罗布泊壮行”的出征仪式。过去,总以为记者很潇洒,没想到他们终日为新闻节目的“看点”呕心沥血,奔波劳碌。那些转瞬即逝的电视画面,蕴含着常人不知道的辛苦。
9点,出征仪式开始了。来为我壮行的当地媒体有《兰州日报》,敦煌的电台、电视台、报社。
在出征仪式上,彪悍的蒙古族男歌手唱起了吉祥的送行歌曲,高昂的蒙古长调和龙吟般的马头琴让我心旷神怡。我喜欢蒙古族歌曲,如苍狼长啸,如战马嘶鸣……尤其喜欢在草原大漠上倾听蒙古族同胞的演唱。戴上洁白的哈达,喝了三碗壮行酒,此时豪情万丈,心已飞向远方。
美丽大方的哈萨克族姑娘们,为我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旋转飘逸,皆有来自天然、来自远古的风情。唐朝诗人白居易的古风《胡旋女》中盛赞的大概就是这种舞蹈:
胡旋女,胡旋女,
心应旋,手应鼓。
旋鼓一声双袖举,
回雪飘摇转蓬舞。
左旋右旋不知疲,
千匝万周无已时。
人间物类无可比,
奔车轮缓旋风迟。
曲终再拜谢天子,
天子为之微启齿。
我的那些来自山东、北京、南京、四川、浙江等地的朋友们,也在欢送的人群中。他们千里迢迢来相送,这份情谊不是语言可以表达的。
新疆方面的协作团队负责向导和后勤保障工作,带队和向导是大名鼎鼎的“罗布泊三剑客”中的刘和平老师及彭戈侠先生。刘和平最后一次给我检查了装备,特别是GPS和海事卫星电话,这两件宝贝能确保他们随时得知我的具体方位。
夏训诚教授是我国权威的沙漠专家,在西北工作51年,曾先后28次进出罗布泊考察。他不停地叮嘱,我即将进入的库鲁克塔格山脉边缘的雅丹和沙包地貌是我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心里也明白,看似平坦的戈壁滩走起来并不轻松,尤其是在负重的情况下,脚踩下去,能把沙子踩出来,就像踩在雪地上一样软绵绵的,但很吃力。在戈壁滩上走三十到三十五公里,相当于在公路上走七八十公里。
简短而热烈的仪式结束了。我向刘少义和罗红斌道别。这三天他们的陪伴,为我的旅途增添了几分色彩和快乐。我们天南海北地侃大山,但很真实,也很轻松。这种人与人的交往方式是我喜欢的:不要求对方什么,不刻意营造什么,自然随意,像溪水一样流淌。能在一起的时候,就要珍惜。分别的时候,也没有太多




![[HP]编号07315封面](http://www.sntxt2.com/cover/21/21855.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