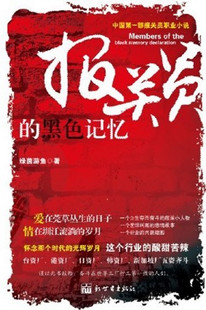茕茕筠竹,一岁宦花-第19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徐多身上的伤不轻,先前忙着赶路没办法好好疗伤。顾岸出了宫不把他当下人看待,好不容易暂时安定下来,徐多也不需要伺候别人,打了桶水,收拾好自己,坐在床上运转内力。
习惯了一年多功力稳定增强,此时经脉被伤势堵塞,徐多急于冲破阻碍,腥甜蓦地涌上喉咙。冷汗爬上额间,徐多稳下情绪,找了块布巾吐出鲜红,颓然地放弃。
他心思烦乱,强行运功,险些加重伤势。背上都是伤,走起路来有点佝偻。他很厌恶自己这副样子,显得脆弱无能。徐多不甘心地长吐口气,下床,摸上茶壶,倒了杯冷茶压住烦闷。
回到床上渐渐冷静下来,徐多开始计划今后的打算。
这次不同于几年前的出征,他只留了张纸条给小太子,还没得到回应便匆匆离开了。他这回没向小太子讨一个“绝不亲近其他人”的承诺,徐多十分清楚小太子早已不是那时候的小豆丁,身上散发着令他迷恋的气质,有了自己的想法,很多事情不再需要他的引导。
他要先养好自己的伤,算好尚武帝恢复记忆的日子,再……徐多合被而眠,闭上眼,脑中的计划运转了不到半柱香时间,迷迷糊糊做起光怪陆离的绮梦。
那个冷清的小屋里,桌上的蜡烛忽明忽暗。他躺在床上痛得辗转反侧,突然感觉到熟悉的气息。
小太子推门而入,唤了一声徐多,神情似乎比平日生动、柔和了些许,投向徐多的视线直白又留恋。
徐多痴痴地看向他,目光黏在他一个人身上,他走近一步,痴迷就更添一分。直至他近在咫尺,徐多仰望着他,傻傻地笑起来,道:“殿下,不要再当奴才的白月光了。”
小太子似懂非懂,又好像并不意外,反而更凑近了些,凝视着徐多。
徐多有点揣揣,轻声道:“殿下生气了?别生奴才的气,可好?”
小太子摇摇头,用前所未有的温柔声音道:“徐多,你疼不疼?”
徐多不大明白小太子的意思,只是将自己的话说得更明白了点:“竹竹,奴才喜欢你。”
小太子没出声,眼里没有怒意,探出一只手握住徐多的,细细寻到他的指缝,十指相扣。
徐多心跳声大到耳鸣,整个身子不由自主地颤抖:“竹竹,你亲亲奴才就不疼了。”
小太子微笑地看着他,黑沉的眼底有点无奈和纵容。小太子俯下|身,微凉的唇瓣先是触碰到他的嘴角,柔柔地亲了下后,覆上他的嘴。徐多先是浑身一软,随即难以抗拒地亢奋起来,他大着胆子先伸出舌试探小太子,发觉他轻启牙关,似是有意无意的邀请。热油噼里啪啦浇在火上,简直被烧断了最后一丝理智,他蓦地用手揽住小太子的后颈,疯狂又如痴如醉地吻他。
“嗯!……”徐多不小心咬到舌头,把自己疼醒了。他懊恼地猛捶一下床板,随后小心翼翼伸出舌尖舔了舔唇角,绯红缓缓爬上脸颊。
===
顾岸不能无所事事地呆在刘春来这儿,找了份工,领了十几个人替别人建房子。
徐多不愿意闲着,顾岸念及他有伤在身,说什么也不准他一同做苦力,于是徐多领了个置办材料和记账的差事。
刘春来专门为顾岸开了家铺子,徐多坐在里头,远远地就看见一个健壮的身影。秦谦是顾岸那边的副手,名字起得文绉绉的,长得一点不含蓄,和刘春来一挂,走的都是糙汉风格。
“徐兄弟,好啊!”秦谦隔着老远冲他打招呼。
“早,缺了什么材料?”
秦谦走进铺子:“顾头儿说明天需要二十根圆木,麻烦你跟陈老板打声招呼。”
徐多不穿奴才的衣服,不做出卑躬屈膝的姿态,很难有人发现他是个太监。他个子不高,身着朴素布衫,声音平和好听,笑起来又亲切,干活的弟兄们都把他当无害的弟弟。
“好,我下午去陈老板那儿一趟,明早就能领到木头。”
“好嘞,麻烦了。”秦谦摸了摸下巴上的胡茬,笑出雪白的牙。
“对了,”徐多叫住他,“顾公子说你们要挖池塘,需要什么你现在给我写张清单,免得到时候再跑一趟。”
徐多有点好处,做起事来有条不紊,不出差错。这在宫中是太监的基本素质,但放在个性普遍粗犷的男人镇平民中,就显得独特起来。
秦谦大咧咧地拍了两下他的肩:“行,纸笔递我。”
秦谦边写,嘴也没闲着:“徐兄弟,我就喜欢你这点,省了我们好多事儿。你伤好些了吗?阿光他们都挂念着,上回你帮他垫了媳妇儿的药钱,他一直念叨着请你吃饭,要不就今晚吧,今晚烤只全羊,羊腿、肋排都归你。你这伤要好吃好喝养着,哪能天天操劳。”
徐多跟着笑了笑,男人镇民风热情,顾岸的几个手下没把他当外人。以为他是受了伤沦落至此,平时大事小事喜欢帮他一把。
徐多不是不喜欢有人对他好,但这只是个临时的栖息之地,他总不愿意牵扯出太多感情。
“我哪吃得了那么多。”他避重就轻地略过伤势,“今天冬至,恐怕不能赴约。”
秦谦才想起来,拍了下脑袋,清单也写好了,把纸笔重重往台面上一放,埋怨了句:“下回!下回再推就太不给面子了……”
徐多重新摆好纸笔,细细检查那张清单:“行,那下回吧。”
作者有话要说:
☆、贰拾叁
小太子推开小屋的门,先是发现放在桌上的油纸包,随后看到压在松子糖下面的纸。小太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头也不回地走出小屋。
他去了御书房,父皇白日一向都在那儿。守在外面的太监换了人,小太子等他通报完,进门,见到几乎变了一个人的父皇。
尚武帝一人坐在偌大的御书房,旁边没有一个下人。尚武帝面容憔悴,看见他,叫了声景儿,露出一个无力的苦笑,招了招手,示意他过去。
小太子走近了些,尚武帝又招了招,直至他走到眼前,尚武帝抓起他一只手,往他手里塞了一个酒杯。
===
东宫一片宁静,皇宫内接连出了几件大事,外面越是热闹,东宫里就越显清净。
小太子很少喝酒,酒量只能算一般。陪父皇喝了一晚上,早就醉了七八分。他踩着月光往回走,远处仿佛有抹等待的人影,再走近些,才看清只是虚影。
他虽说是个太子,每日的生活却很单调。除了念书和练武,再无多余的活动。如今师傅走了,练武的时间也缩短了。他以前从来不觉得这样的日子有何无趣,时不时一转身,就能看到徐多微微躬着的身影,有时在他刚刚收起剑时,有时在他合上书时。发现徐多的时候,徐多往往已经在那伫立良久。
这是徐多第一次主动离开,一声不吭的,毫无预兆的。
小太子脑袋发沉,不是很喜欢这种气闷的感觉,像是被什么约束住,扰乱他的心绪。
刘元走后东宫一直缺了个掌事的太监,小太子已经脱好了鞋袜才想起殿内还灯火通明。他下了床,没有唤其他奴才,光着脚一盏一盏吹灭烛火。
酒意上涌,小太子歪歪斜斜地走了两步,定了定,再往前走。
还有最后一个烛火。它被放在榻边的桌面上,上面有不少玩意儿,摆得十分整齐,但小太子现在看来,每个东西的边缘都已经模糊重叠。
小太子朝前伸出手想撑住台面,不经意扫落了桌上一样东西,那暗紫的物体在地上“咚咚”滚了两圈,停下来。
这个小暖炉是第二次见徐多时得到的,他当时十分喜爱,整整一个冬天都捧着它度日。后来日子久了,又有一个又一个寒冬,他没有换过另一个暖炉,却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日日抱着它。
他把摔落的小暖炉拾起,里头没添火炭,外壁坚硬冰冷。小太子把它放在腿上,蓦地接触到冷硬的外壁,激得他清醒了两分。
小太子回了回神,有点卖力地回忆今日和父皇的对话。
“父皇,师傅走了吗?”
“景儿,朕还是想不起来……”
“儿臣能做什么?”
“朕不知该如何是好……景儿,你还小……朕反悔了……朕怎么能放他走……”尚武帝喝得神志不清,忘却了面前是他年仅十二的儿子。只知眼前是最亲近安全的人,一味发泄痛苦。
尚武帝在小太子心中高大可靠、无所不能,这么近看到父皇的悲痛,令他简直愕然。他可以做一点什么?想得脑袋昏昏的,突然浑身一激灵,嗅到一丝怪味,倏地扭头,才发现方才撞落小暖炉时竟然同时将一旁的烛台推倒在地。
星点的火光快速地扩大,不给小太子缓冲的时间,火势已然蔓延到床角,散发呛人的烟味,似要吞噬了整张床。小太子飞快从榻上跳起来,抱着怀里的小暖炉快步走到外面。
“青儿!”小太子朗声。
隔了一会儿,一个小丫鬟揉着惺忪的眼过来,没来得及请安,陡然瞟到寝宫内异样的火光,顿时大惊失色。
“殿,殿下……”
“叫人救火。”他冷声命令,面色罕见的难看。
“是……是……奴婢这就去唤人……”青儿乱了阵脚,在原地转了几圈后才撒腿跑去寻帮手,跑了几步转头慌忙道:“此地危险,殿下快些离开……”
小太子赤足站在殿外的空地,衣着凌乱,亵衣滑落一边肩膀,露出光洁的肤色。凑上去仔细嗅嗅,还能闻到酒和烟混杂的气味。
他从未如此狼狈,不复以往镇定淡然。
紧蹙的眉宇间又增了一分懊恼。实际上,他有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徐多不在,他如同失去了庇护的外罩,再也难以维持住那副与世无争、云淡风轻的模样。
===
东宫走水不是一件小事,好在当时小太子清醒着,没令火势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但终究是损坏了一部分,寝宫内重新修缮,小太子只得挪去其他宫殿就寝。
尚武帝还处于失忆中,小太子接到这道旨意,点了点头,表示接旨。
他没有去东宫其他偏殿,反而抱着“失而复得”小暖炉走向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方向。
回到最初的太子宫,小太子站在宫门口,不禁呼吸一滞。这里的气息太过亲切,他有五年没回来,却还能闻到空气中母妃栽花时的泥土香。
这里一直有人在清扫,他推开内殿的门,那个放着他许多“宝物”的箱子还在角落里,小太子恍然,这里种着他的童年。那时候没有松子糖,也没有华贵的布置,只有他的小皮球,和几个冷淡的下人。
那些奴才们的面孔小太子早已忘却,似乎徐多出现后,那些人就一个一个地消失了。他以前小,不懂,如今到了这个年纪,便也清楚其中谁在作祟。他知道东宫内有很多徐多的人,却不甚在意,不远不近地也与那些人相处了好几年。不是他对徐多怀有戒心,而是除去徐多外,他谁都不信。
他的淡漠是与生俱来的,若不是徐多这么多年仔细呵护、处处用心,绝不会融化那层冰冷的外壳。
小太子躺在久违的床上,翻了个身,突然感觉到怪异,掀开身下一层绒毡,露出里面一把青色的剑。
小太子把它拿出来,握到剑柄的一刹那,回忆便接踵而至。这把小铜剑是徐多给他的,他还想得起徐多带来剑时的表情,羞愧且自责。具体徐多是因为什么愧疚,小太子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获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