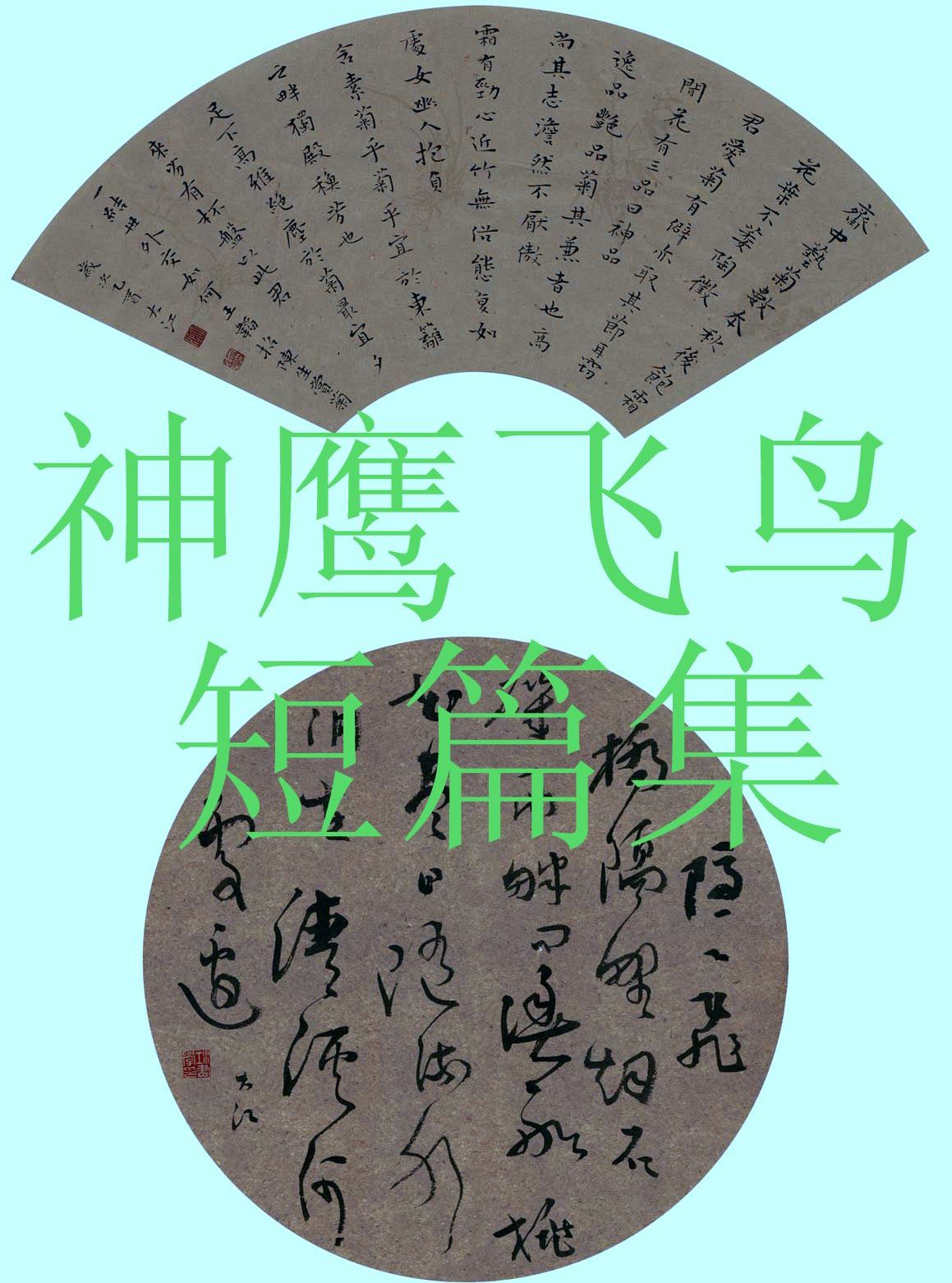九月鹰飞-第5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你要嫁给我?”葛病在笑,笑容中带着三分辛酸,三分感激,还有三分是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也分不清,他不是个十分清楚的人。
丁灵琳跳起来,她忽然发现这里唯一亮着的灯火,就是那对龙凤花烛。这本是为她和郭定而准备的,就在这对龙凤花烛前,郭定穿着一身新郎的吉服,倒了下去。
现在,这对花烛还没有燃尽,她却已要嫁给另外一个人。
若是别人要做这种事,无论谁都会认为这个人是个荒唐无情的疯子。可是丁灵琳不是别人,无论谁对她都只有怜悯和同情,因为她这么做,不是无情,而是有情,不是报复,而是牺牲,她不惜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为的只要报答别人对她的恩情,除此之外,她实在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法子能救葛病。
这法子当然并不一定有效,这种想法也很荒谬幼稚。可是一个人若是肯牺牲自己,去救别人,那么她做的事无论多荒唐,多幼稚,都值得尊敬。
因为这种牺牲才是真正的牺牲,才是别人既不肯做、也做不到的。
正文 第二四章 悲欢离合
花烛已将燃尽,烛泪还未干。
烛泪一定要等到蜡烛己成灰时才会干,蜡烛宁愿自己被烧成灰。
也只为了照亮别人。
这种做法岂非也很愚蠢?
但人们若是肯多做几件这种愚蠢的事,这世界岂非更辉煌灿烂?
丁灵琳扶起葛病,站在花烛前,柔声道:“现在我就要嫁给你,做你的妻子,终生依靠你,所以你一定要活下去。”
葛病看着她,一双灰黯的眼睛,忽然又有了光采,脸上的笑容,也已变得安详恬静。
丁灵琳泪痕未干的脸上,也已露出了微笑。
她知道他已能活下去。
现在他已有了家,有了亲人,他已不能死。
她寒着泪笑道:“这里虽然没有喜官,但我们却一样还是可以拜天地,只要我们两个人愿意,有没有别人做见证都一样。”
这并不是儿戏,更不算荒唐,因为她的确是真心诚意的。
葛病慢漫地点了点头,目中带着种异样的光采看着她,看着面前的花烛。
能和自己喜爱的女子结合,岂非正是每个男人最大的愿望。
他微笑着:“我这一生中,一直都在盼望能有这么样一天我本来以为我永远不会有这么样一天了,可是现在”
现在他终于达成了他的愿望。
他的语声也变得安详而恬静,可是他并没有说完这句话,他忽然倒了下去。
死亡下得比闪电还快,忽然就击倒了他。
他完全不能抵抗。
没有人能抵抗。
黎明前总是一大最黑暗的时候。
丁灵琳己跪下,跪在葛病,的尸体前,眼泪就像是泉水般涌出来。
就在这同一个地方,同一对花烛前,就在同一天晚上,已有两个准备跟他结合的男人倒了下去。
这打击实在太大。
也许他们本就要死的,因为她,他们也许反而死得更快。
可是她自己却己不能不这么想。她忽然觉得自己是个不样的女人,只能为别人带来灾祸和死亡。
郭定死了,葛病死了,叶开也几乎死在她的刀下。
她自己却偏偏还活着。 ——
我为什么还要活着?为什么还要活在这世界上?
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每个她认得的人,竟都可能是魔教中的人,从铁姑开始,到玉箫道人,葛病,还有那冷酷如恶魔的孤峰天王,每个人都是她想不到的。
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她可信赖的?
只有叶开!可是叶开又在何处?
酒还在她身旁,烈酒喝下去时,就像是喝下了一团火。
她喝了一口,又一口。
“叶开你说过,只要等一切事解决,你就会来找我,现在什么事都完了,你为什么还不来?为什么?”
她放声大叫,忽然将手里的酒坛子用力砸出去,砸得粉碎,烈酒鲜血般流在地上。
桌上已将燃尽的龙凤花烛也被震倒了,落在地上,立刻将地上的烈酒燃烧了起来。
火也是无情的,甚至比死亡更无情,甚至比死亡来得更快。
这种猛烈的火势,又有谁能抵抗。
没有人能抵抗!
但丁灵琳却还是痴痴地跪在那里,连动都没有动。
看着火焰燃烧,她心里忽然泛起种残酷的快意。
她要看着这种火焰燃烧,把所有的一切全都烧光,她己不再有什么留恋。
毁灭岂非也是种发泄?
她需要发泄。她想毁灭。
木板隔成的厅堂,转眼问就已被火焰吞没,所有的一切事,现在真的已全都解决了。
可是叶开呢?
叶开。你为什么还不来?
烈火照红了大地苍穹时,黎明终于来了。
叶开却还是没有来。
叶开醉了。
他一向很少醉,从来也没有人能灌醉他,唯一能灌醉他的人,就是他自己。
他很想灌醉自己。
喝醉酒并不是件很愉快的事,尤其第二天早上更不愉快——这一点他比谁都知道得清楚。
可是昨天晚上,他却硬是把自己灌醉,醉得人事不省。
因为他毕竟不是圣人。
知道自己的情人正在拜天地,新郎官却不是自己,又有谁还能保持清清醒醒,高高兴兴地在街上逛来逛去?
所以他逛到第一个卖酒的地方时,就停了下来,停了一个多时辰。
可是出来的时候还没有醉。
一一这地方的酒好像太淡了,好像兑了水。
所以他又逛到第二个卖酒的地方,用一种不稳定的脚步逛了进去。
这次他是怎么出来的,他已记不清了,以后是不是到过第三个地方?他更记不清了。
他唯一记得的事,是把一个带着婊子去喝酒的上流氓头上打了个洞。
那个洞究竟有多大?他也已完全不记得。
他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竟睡在一条死弄中的垃圾堆里。
又脏又臭的垃圾堆,连野狗都绝不肯在这种地方睡一下子。
他可以保证这绝不是他自己愿意的,他一向没有睡在垃圾堆里的习惯。 ——
定是那个头上有洞的上流氓,找了人来报仇,先揍了他一顿,再把他抛到这里来。
他不久就证实了这件事。
因为他站起来的时候不但头痛欲裂,而且全身都发疼。
那一定要很重的拳头才能把他打成这样子,他还没有学会打人前就已先学会挨打的。
然后他又发现头疼并不是完全因为酒醉,他头上也多了个洞。
无论谁若是发现自己被人抛在垃圾堆里,被整得一塌糊涂,都兔不了要很生气,很难受的。 ——
偶而能被人痛揍,岂非也是件蛮有趣的事。
何况,他相信揍他的那些家伙们,现在一定也很痛。
走出巷子,是条斜街,就像长安城里大多数街道一样,古老而陈旧。
街对面有家小酒馆,门口挂着个很大的酒葫芦,是铁铸的。
叶开忽然想起,昨天晚上他打架喝酒,都是在这小酒铺里。
酒铺后面,好像就是个“暗门子”,那上流氓带出来的,就是这暗门子里的女人。
从这里往左转,再转过两条街,就是鸿宾客栈。
叶开这一辈子,大概是再也不会到鸿宾客栈去了,那里的伤心事实在大多。
现在应该到哪里去?应该做些什么事?叶开连想都没有想。
他决定暂时什么都不去想,现在他脑子里还是昏沉沉的。
他只知道绝不能往左边走。
今天居然又是晴天,太阳照在人身上,暖暖和和的,很舒服。
街上的人都穿着新衣服,脸上都带着喜气,一见面就作揖,不停他说:“恭喜”,叶开这才想起来,今天还是大年初二。
别的人在大年初二这一天,应该做些什么事呢? ——
带着孩子到亲戚朋友家去拜年,收些压岁钱,然后再回家,准备些金果元宝,等着别人来拜年,把压岁钱再还给别人的孩子。
这一天大家都不许说不吉利的话,更不许吵架、生气。
可是既没有家、又没有朋友的异乡浪子,在这一天又该干什么?
叶开在街上逛来逛去,东张西望,其实眼睛里什么都没有看到,心里什么都没有去想,也许只在想一件事。
丁灵琳现在正干什么?
他本来已决定,永远再也不想她了,但却不知为了什么,他这昏沉沉的脑袋里,想来想去,偏偏都只有她一个人。
他刚才还决定,绝不再到鸿宾客栈去,可是现在一拾起头,就发现自己还是又走到这条路上来了。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看见鸿宾客栈那块高高挂着的金字招牌,只看见一大堆人,围在那里,有的在窃窃私议,有的在摇头叹息,甚至还有些人正在那里抱着头放声大哭着。
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
叶开忍不住逛了过去,挤进人丛,然后他整个人就忽然变得冷冷冰冰,就像是一下子掉进了深不见底的冷水潭里。
长安城里气派最大的鸿宾客栈,现在竞已变成了一片瓦砾。
鸿宾客栈昨夜的惨案:直到天亮才有人知道,因为昨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是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的晚上,大家通常都是在呆在家里的,谁也不会到街上来闲逛,就算有人,也是些已赌得头昏脑胀的人,谁也不会逛到客栈里去。
呆在家里的人,也大多都在喝酒,赌钱,更不会关心到外面的事。
老掌柜请去喝喜酒的,大都是些无家可归的光棍,没有人关心的光棍。
就因为这是个特别的日子,所以才会发生那些特别的事。
这并不是巧合。
每件事的发生和存在,都一定有它的原因。
“这里是什么则。候走水的?”
“不知道。”
“昨天夜里我在赌叶子牌,就算天塌下来,我也不会知道。”
“听说昨天晚上有人在这里做喜事?”
“好像是的。”
“那些来喝喜酒的人,怎么连一个都不在?”
“不知道。”
“那对新人呢?”
“不知道。”
这地方虽然已被烧成了瓦砾,却连一个人的骸骨都没有。
“这里的老掌柜呢?”
“不知道。”
昨天晚上这里究竟出了什么事,简直连一个知道的人都没有。
“我别的事都不奇怪,只奇怪那对新人居然也不在这洞房里,连老掌柜都不见了。”
大家议论纷纷,越说越奇:“难道这里昨天晚上出了狐仙?出了鬼?”
若不是有鬼,客栈被烧光,那老